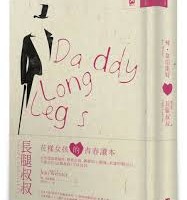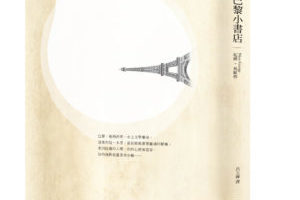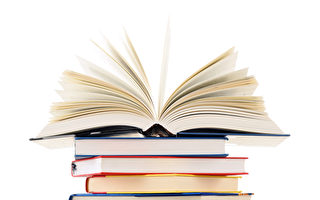書摘:今晚,我們用人生調味(1)

《今晚,我們用人生調味》(平安文化出版社 提供)
耶誕晚餐
我在和愛德華見面之前,就聽說了他在太太臨終前所作的承諾。
薇樂莉是愛德華的女兒,也是我認識非常久的一位老朋友,她在母親過世後不久就跟我說了這個故事。
她的母親寶拉臥病多年,在九十五歲生日的前幾天裡,時而清醒時而昏迷,有一天卻突然在床上坐起來,特別指明要跟她親愛的先生說話。
「聽我說,愛迪。」寶拉的語氣堅定有力。
「你現在不能跟我一起走,否則我們的小家庭就到此結束了。」
寶拉知道愛德華已經作了決定,他寧可跟她一塊死,也不願獨活。
那樣不對,她說,而且極力勸他要活下去。等他好不容易同意了之後,她就對著這位結髮六十九年的男人唱小夜曲。
開口的第一首是〈我風趣的情人〉,然後一口氣唱了1940年代與1950年代排行榜上有名的百老匯音樂劇歌曲和民謠。歌詞有一搭沒一搭的。
當年他們還年輕,仍然懷抱著雄心壯志,相信自己能在演藝界闖出一片天空。
寶拉的歌聲清亮,絲毫聽不出她幾天來飽受胸腔感染之苦,連說話都很困難。她最後以〈全部的你〉作結,唱得七零八落:
「我愛你的北方,東方,西方,你的南方,但我最愛的是全部的你。」
二十四小時後她就過世了,在2009年十月。她死後的幾週內,愛德華哀慟逾恆,覺得幾乎不可能守住他對寶拉的承諾。他獨自坐在安靜的公寓裡,坐在餐桌前,他們一家人曾在這張餐桌上吃過許許多多活潑愉快的晚餐。
最後,愛德華住進了雷諾克斯山醫院,醫師們做了一連串的檢驗,卻找不出他的身體有什麼毛病,打算隔天就讓他出院。
「恐怕他是不想活了。」薇樂莉說。在醫院的等候室裡坐在我旁邊的位子上。
那天是耶誕夜,我們說好了一塊吃晚餐。薇樂莉推薦了一家醫院轉角的餐廳,她都陪她父親在這裡用餐。
這是一家沒什麼特色的第三街小館子,我們入座後,戳著乏善可陳的紅鯛魚,我們兩個都哭了。
這天原本是寶拉的生日前夕,而薇樂莉還沒有走出喪母之慟。現在她又非常擔心她父親,怕他會活不下去。
我也不確定在聽薇樂莉述說寶拉唱歌的那一段時,為什麼會淚崩。
我沒見過愛德華,而雖然那是非常催淚的一幕,我還是忍不住覺得部分原因是:我自己的不快樂,也被赤裸裸地揭穿了。
我剛搬到紐約不久,在報社當記者,耶誕節我得出差。我的婚姻眼看也快解體了,儘管我盡了最大的努力假裝一切都好。而且我非常擔心離婚對我年幼的女兒會有太大的衝擊。
我含糊其詞地提出了自己的困境──我不想害薇樂莉在她父親生病時還替我的問題擔心──她建議我和愛德華一塊吃飯。
「他很會做菜。」
薇樂莉邊哭邊說,或許是希望這句話會勾起我的好奇心,等她回加拿大後,我會自願去探望愛德華(她的姊姊蘿拉是藝術家,跟先生住在希臘)。
我不知道我是因為美味大餐太誘人,或者是我只是太寂寞了,連跟一個抑鬱沮喪的九十歲老翁消磨時光都變得具有吸引力。可能是想為薇樂莉這個朋友兩肋插刀,也可能是對她父親感到好奇,讓我在兩個月後來到愛德華的大門前。
反正無論是什麼原因,我壓根就沒想到和愛德華見面竟然會改變我的人生。
為了我們第一次的兩人晚餐,我穿了一件黑色亞麻質地的寬鬆直筒連衣裙和涼鞋。我輕輕敲門,然後又按電鈴,幾分鐘之後,一名高個子年長紳士突然打開了門,兩眼帶笑,握住了我的手,吻了我的兩頰。
「達令!」他說:「我一直在等妳。」
***
九十三歲的愛德華是一位風度翩翩的紳士,而且「很會做菜」。無論是在口中融化的杏子舒芙蕾、香氣彌漫的蘋果派,還是紙包香草烤雞、里斯本風鑲小烏賊、法式葡萄酒醬牛排 ……
伊莎貝兒每週與愛德華共進一次晚餐,不僅品嘗到愛德華精心烹調的各種美味佳餚,也分享了愛德華豐富的人生閱歷與智慧。
剛開始我總是帶著一瓶酒到愛德華的公寓。
「什麼都不需要帶,寶貝。」他說。
儘管我常常會忽略這個建議,我覺得兩手空空去吃飯很不習慣。
而且也不需要敲門或是按門鈴,愛德華這麼跟我說。他一定會知道我來了沒,因為我一走進這棟公寓的大門,門房就會打電話上來通知他。況且,他的門也都不上鎖。
不過在我們見面後不久,他就堅持要給我一把鑰匙,怕的是他在早上或下午在沙發上打盹時,我想過來看看他,門卻鎖住了。
他給我的鑰匙套在紫色塑膠鍊上,鑰匙環上的小卡片用黑色粗體字寫著愛德華以及他的電話號碼。我們兩人都知道我不會真的用這支鑰匙打開他的公寓門,可是我很有禮貌地收下了──表示友誼,也每天提醒我愛德華現在是我人生中的一分子了。
每次我帶酒去,愛德華都會把我的名字寫在標籤上,然後塞進門廳衣櫃裡的臨時酒窖裡。衣櫃是他掛冬天厚外套的地方。
每次都是在我抵達之前,他就選好了佐餐的酒了,而我帶去的酒會留待下一次更合適的餐點。
在一次早期的晚餐,我犯了個錯,我帶了醃鱈魚炸丸子,這是我根據我母親的食譜做的。我根本就不該以為他會把炸魚丸連同他的菜一起放上餐桌。
我毫無預警就把這道菜塞給他。在我們相識的早期,我從來就沒想過愛德華準備每一餐花了多少心思。我才剛把那一包用錫箔紙包著的炸魚丸遞過去,就知道我失禮了,我也看出了愛德華有片刻的疑惑。
但他優雅地收下了我的禮物,邀我這個星期再找一天來晚餐,好讓我們一起分享炸魚丸。
愛德華不是勢利鬼,也不是讓人受不了的吃貨。他只是喜歡做事情照著規矩來。
他對自己創造的東西都十分關注──無論是客廳裡的家具或是他的文章。他親手打造了所有的家具,連椅子的布面也一手包辦。而且他寫詩和短篇故事,一筆一畫都規規矩矩,再很有耐心地把草稿重謄在白紙上,寫到他滿意了才會交給他的一個女兒打字。
他對待烹飪也是差不多的態度,雖然他是在晚年,在他七十幾歲時才開始掌廚的。
「寶拉做了五十二年的飯,有一天我跟她說她夠辛苦了,也該輪到我了。」他說。
愛德華年輕的時候就學會了要珍惜美好的食物。十四歲時他留級了,他的父母把他送離納什維爾,到紐奧良去跟他富有的叔叔、嬸嬸過暑假。
他的嬸嬸愛蓮諾是老師,決定要教會他什麼叫紀律,讓他回到正軌上來。同時她也決定要指導他做法國料理。
「我被帶進了一個我根本不知道的世界。」他說。
回憶起1934年在赫赫有名的安東尼餐廳吃的一餐:「我永遠也忘不了第一次吃軟殼蟹。裹上薄薄的麵糊油炸,配上融化的熱奶油。真是太美味了。」
他開始烹飪時,借用了安東尼餐廳的法式克里奧菜單,不過他也開心地跟我說,他也能欣賞簡單的東西。
他仍能記得小時候吃水煮包心菜:「加上一大塊奶油,那種滋味就只有天堂才有!」
而且他到處找靈感:他自稱他的炒蛋技術是從聖若翰那兒學到的。◇(待續)
——節錄自《今晚,我們用人生調味》/ 平安文化出版社
【作者簡介】
伊莎貝兒·文森(Isabel Vincent)
1965年生於加拿大多倫多,多倫多大學畢業,目前她定居於紐約。
伊莎貝兒·文森是知名調查記者,除為《紐約郵報》撰稿外,報導也出現在《TIME》、《紐約客》等全球各大報章雜誌上。她並曾贏得多個獎項,包括加拿大記者協會「卓越調查新聞獎」。其著作《身體與靈魂》獲加拿大「國家猶太圖書獎」,《希特勒的沉默夥伴》則獲頒「猶太大屠殺紀念獎」。
責任編輯:李昀
點閱【今晚,我們用人生調味】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