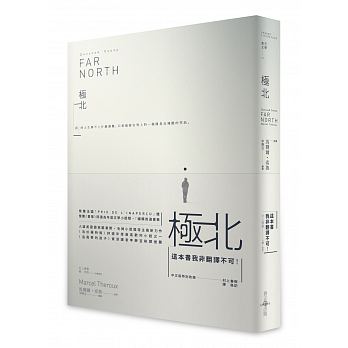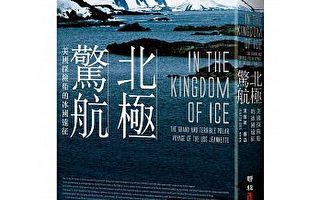我用托盤端給他一壺熱水、鑷子、紗布,和大蒜肥皂,讓他自己去搞。而且我把他的門鎖起來,以策安全。
我把麻布袋裡的書擺在客廳的書架上。這些書全都是奇奇怪怪的尺寸,所以沒辦法像爸媽的書那樣擺得整整齊齊的。有幾本是圖文書。我很納悶男孩是要拿這些書去看,還是去燒。我確信自己知道答案。
燒掉的書總是會讓我有點心情沉重。
□
我每用掉一顆子彈,就逼自己立刻再做五顆。我遵守這個規則,已經有好一陣子了。我的子彈成本極高,不管是花的時間,或是為了熔煉而耗費的燃料。花了這麼高的代價去做出品質這麼差的東西,實在很不划算。
但我的想法是這樣的:如果燃料用罄了,總還是可以找得到,我可以劈開一些硬木,做成木炭甚至可以燒掉自動鋼琴——老天垂憐,如果非這樣做不可的話。但你絕對不該任憑事態惡化,掉以輕心,讓子彈供給不足。
如果你能找到一個願意和你做買賣的人,子彈當然會有個市場的公定價格。但是萬一有人找你碴,招來一群狐群狗黨不放你甘休,這時一顆子彈又值多少?為了不聽見你的槍上膛時半顆子彈都沒有的聲音,你願意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此外,我也喜歡自己動手做。我喜歡金屬熔化的過程。我喜歡蹲在熔爐旁邊,透過我父親那副煙灰色眼鏡的鏡片看著火燄,看著鉛像水銀那樣流動。我喜歡物質轉化的過程,喜歡早上從模子的沙土裡剝下那冰冷醜陋的金屬塊。
問題是,理所當然,我的子彈一點都不精良。如果要再次開槍射擊,我會希望用的是純精鋼打造,閃閃發亮的精良子彈,而不是像我做的這種醜不拉嘰的東西,活像有人丟在馬蹄鐵匠鋪裡的地板上,沾滿天曉得是什麼的泥土和細菌。
做好五顆子彈之後,我帶了一些食物和水,以及一盞酒精燈到男孩床邊。他在發燒,眼睛閉著,但在眼皮底下微微翻動。短而粗密的睫毛。披散在枕頭上的藍黑色頭髮,讓我想起烏鴉的翅膀。他嘴裡唸唸有詞,用的是他自己的語言。
便盆是空的,但我拿走男孩那件發臭的藍色連身袍。他可以穿查洛的衣服,如果他活下來的話。
□
天剛破曉,我端了早餐給他。
他的皮膚連一絲黃色都沒有,白得像骸骨。兩鬢有淡黑色的頭髮,但唇上與兩頰都沒有鬍子。
我留給他的食物,他全吃光光,但我轉身去拿便盆的時候,他卻生氣了。他很害羞。這時我知道自己喜歡他:我差點殺了他,但他卻羞於讓我看見他的大便。真是個孩子。
我想盡辦法用手勢表達,要他躺在床上休息。他看起來情況還不太好。但是我才開始打掃馬廄,他就出現在院子裡。穿著查洛的格紋外套和他的拖鞋,他看起來年紀更輕,個頭更小。傷口的包紮讓他腳步不穩,但他還是走過來,坐在凳子上看我餵母馬吃東西。看見馬,他似乎很開心。
「Ma。」他指著她說。
我開始解釋我從不給動物取名字,我只叫牠們「母馬」、「花馬」或「灰馬」,對於你終有一天要宰來吃的動物,哪有必要取名字。而且把牠們看成一塊馬肉,總比當成是亞當斯基或黛西美兒的身體來得容易應付吧。
但是我沒辦法讓男孩理解我的意思,所以從此後,母馬就變成「瑪」了。
這時他指著自己,說出一個發音近似「平」的字。沒錯,平。就像商店門口的鈴鐺輕響。就像繃開的襯衫釦子。或是撥動的斑鳩琴弦。我很想知道這是哪一種異教徒的名字,還是說有個我沒聽說過的「聖徒平」存在。
但他就是平。就是這個名字。所以我也自我介紹。我指著自己,說出我的名字:「梅克皮斯」。
他一臉迷惑,皺起臉,彷彿沒聽清楚似的,不確定自己是不是敢唸出這個名字。所以我又說了一遍:「梅克皮斯」。
他的臉露出一個大大的咧嘴笑。「沒可屁事?」
我仔細地瞧著他,但他並不是要取笑我,只認為那是我的名字。而且既然我唸他名字的時候笑了,他怪裡怪氣的唸我的名字也沒什麼不對嘛。
□
讓平住在我家,卻又不信任他,顯然一點道理都沒有。我這人脾氣很壞,孤僻獨居,疑神疑鬼,而這也是我能活這麼多年的原因。除了我之外,最後一個住在這屋簷下的是查洛,但那也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了。
不過當時我想,其實現在也還是這麼認為,一旦你讓其他人進屋來,你就得完全接納他。每回騎馬離開家門,我就會認為碰見的任何人都打算殺我或搶劫我。但是在自己家裡,我可不能這樣過日子。
我決定信任平,不是因為我對他有某種直覺,我對他根本一無所知──而是因為這是我能過下去的唯一方法。
然而,午餐時分騎馬回來,發現門鎖完好無缺,柴薪依舊疊得整整齊齊,小雞到處啄食,儲藏窖裡的甘藍菜和蘋果沒人動過,我還是有點意外。但是平不見蹤影,坦白說,當時想到他可能已經離開了,我心裡竟然有點難過。
我匆匆爬上二樓,腳上的靴子踩在樓梯上乒乒乓乓。沒有他的影跡。我衝進查洛房間,被眼前的景象嚇了一大跳。
平在那裡,面前擺了一個鏡子,我媽的舊針線盒,以及一盞酒精燈。他一根一根拿起舊鐵針,在火燄裡穿梭,然後戳進耳朵的肉裡。
看見我,他露出微笑,而我的驚駭讓他笑了起來。他整隻耳朵像豪豬身上的刺那樣豎起來。針刺進去想必讓他痛得要命,但是他沒有因為這樣而放棄。事實上,他繼續把針戳進耳朵裡。然後,他小心翼翼地在鼻子上插了一兩根針,接著又在肩膀上插了一兩根。
我忍耐力很強。我必須如此。但是看見這個畫面,還是讓我有種怪怪的感覺。
平讓我了解他腦筋沒有問題,拿針戳身體是為了讓肩膀的傷口癒合。但這到底是什麼路數的魔法,恐怕我就沒辦法告訴你了。◇(節錄完)
——節錄自《極北》/春天出版公司
責任編輯:李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