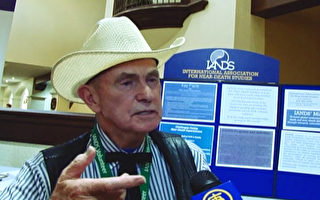想见慈颜空有泪,哀思常随仙鹤飞;
欲聆庭训遝无声,难将寸草报春晖。
缠小脚的母亲首缘早寡,木匠父亲常年在外奔波,战乱动荡中两人携手流亡他乡以求生,相濡以沫展开新的人生。父母亲离开我们二十余年了,2014年(黄历甲午年)正值父亲诞辰110周年和母亲诞辰105周年,特为文纪念。
母生世家 德高品清 首缘四年即从寡
1910年3月4日(黄历庚戌年正月二十三),母亲钱英出生在苏北滨海县城一个家境富裕的耕读之家。
小时候,常听母亲讲她幼年时的事。外公是个读书人,知书达理、为人厚道、远近闻名。曾做过多年的私塾先生,所以对子女家教甚严。在那个时代,读书识字、外出干事、养家糊口、闯荡天下是男人的事。即使是富裕人家,女孩子一般也是不能进学堂念书的。
所以,母亲从没上过一天学。但是,富裕的家境毕竟给了母亲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她不必像穷苦人家的孩子那样,因缺衣少食而忙于生计受劳苦困顿。她有大量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去私塾学堂偷听兄长们读书、念诗。而外公也乐得清闲,懒得管她,非但不予阻止,还时常给她讲点野史逸闻,戏文掌故什么的。
母亲从6岁开始,直到出嫁,经常被外公带去镇上小戏院子看古戏,听说书。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孔孟之道,忠、孝、礼、义、仁,在她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可以说:母亲的人生哲学、处世准则,基本上都是从中国传统戏曲及文史典故中得到的。忠厚、诚实、善良、仁慈,遇事先为他人着想,从不与人为恶,是母亲最宝贵的品德。
不过即便是有着这般悠游的环境,依旧藏着最让母亲刻骨铭心的记忆,那就是缠足。母亲8岁时,便被家里逼着缠足,年幼的足骨被长长的布条包缠,白日里不能作稍长距离的行走,只能慢慢移动脚步,走上几十步之遥就要痛得浑身冷汗直冒。夜晚时疼痛难忍不能入眠,常常整夜啼哭不止。外婆在世时,偶尔偷偷在夜深人静时,让母亲把缠足布放掉,息上半夜,第2天重新缠上。这当然得瞒住外公,因为一旦让他发觉,必定大发雷霆,轻则痛斥指责,重则家法侍候。经过3年缠缠放放痛苦残忍的折磨。母亲终于完成了缠足。从此便用她那一双令人可怜的小脚,颤颤巍巍地走完了她艰苦辛劳的一生。
如果说,外公逼着母亲缠足是一个残酷的行为,那么他让母亲自幼便操习女红,为母亲增添日后令人羡慕并赖以维生甚而另结良缘的绝技,则是外公给予母亲最大的恩赐。外婆去世不久,外公便续弦再娶。新进门的小外婆比外公小十来岁,是个管家理财的行家能手,还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女裁缝。外公便让母亲向新外婆学习女红。几年下来,母亲的手艺竟超过了新外婆,名声远播,村里乡外妇孺皆知。
及至母亲渐渐长大,到了谈婚论嫁之时,慕名前来提亲的媒人接踵而至,令外公应接不暇。凭心而论,尽管新外婆对母亲是严多于爱,但外公对自己的亲生骨肉,总还是怜爱的。他想让母亲能嫁到一个好人家,挑挑捡捡,最终选定了离家60里开外的一俞(余)姓青年。家道虽不太富,难能可贵的是,这是一个书香门第,先前曾出过举人。俞父也是教书匠,膝下唯一男儿,只可惜自幼多病,体质虚弱。俞家希望借婚嫁冲冲喜,说不定能消除病灾,带来好运。于是择定吉日,完成大礼,母亲便从女孩儿家匆匆成为人妇。这一年,她才18岁。
母亲常跟我们说:她的第一次婚姻是不幸的。
这并不是说俞家人不好,也并非丈夫不爱她,而是指婚后仅仅过了4年,她丈夫便仓促走完了人生。母亲22岁便守节从寡,陪伴公婆凄楚度日。
日子过得了无情趣,但也还算平安无事。
转眼6年过去了,年近30的母亲不幸又遭到战争的祸害。日本侵略者把战火从华北经华中烧到了华东。1937年底国都南京沦陷,苏北、苏南相继陷入日寇铁蹄蹂躏之下。
父系舜帝之后 习木艺操持一生
与母亲不同,父亲出生在贫困家庭。父亲姚武之,字白兰,1905年3月21日出生于贫瘠的苏北阜甯县,喻口乡。据《学宏堂姚氏宗谱》载:“姚氏一族,相传上五帝之一舜,因出生在姚墟,他的后世子孙即以出生地的姚为姓氏。据传舜帝名字就叫姚重华。”
祖父姚廷㭴是教书先生,家境贫寒,加之子女众多,生活是相当拮据的。但是作为读书人,他还是省吃俭用坚持让几个儿子去念书、识字。所以我的两个伯父都能学有所长,后来继承了祖父的衣钵,当了教书匠。唯有轮到我父亲时,家境实在难以支撑。启蒙时期,勉强念了5年完小,13岁便因家境窘迫,辍学回家了。祖父四处求人,终于让父亲拜当地一位颇有名气的木匠为师。从此斧、锤、锯、凿便伴随父亲走完他勤劳、朴质、艰辛而漫长的一生。
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再度“合作”,“结成统一战线”。随即江淮平原、苏南﹑苏北都出现了一些“抗日武装”。他们挖公路、炸桥梁、埋地雷、割电线,倒也颇令日本鬼子头痛不已。说实在的,这种“抗日武装”从来没跟鬼子正面硬碰硬交过手。但在组织民众,扩大武装上,他们却干得有声有色。
据相关记载,新四军于1937年10月由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组建而成,叶挺、项英为正副军长。组建时仅8千多人,7千条枪。在陈毅“积极拓展人、枪、款”的做法下,至1941年底42年初,新四军在苏、皖、鄂、豫上已建立了8块根据地,主力部队从不足1万发展到近20万,地方武装近10万。可奇怪的是这么多的人和枪,在抗战的8年之中都没见过有史料记载可圈可点的大战,即使不能像台儿庄大捷那般轰轰烈烈,类似于平型关的战斗也该有那么几次吧,然而确实是史无记载。是遗漏?还是⋯⋯?
反正不管怎么说,新四军、八路军在抗日战争8年里,武装力量却在迅速扩展是不争的事实。
父亲满16岁时当上木匠,跟随师父背着工具走南闯北,经风雨,见世面。有过风餐露宿、饥寒交迫的困顿,也有上梁盖瓦、大宴酒席的风光。随着技艺不断精湛,远乡近邻请他们做工的越来越多。近20年工匠生涯,既丰富了父亲的人生阅历,也增长了他待人处事的才干。尤其是结识了不少乡绅大户,知名人士。
当时的中共地下组织,想要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自然要争取像父亲这样阅历丰富、交际广泛的人加入。于是在父亲的本家兄弟姚俅的动员下,于1938年加入县大队。不久被提为大队长,那是1940年,父亲刚刚36岁。
战乱后勤孔急 军需女红撮缘分
1940年,不事抗日,专注扩充的新四军,在黄桥战役中,打败了参加过徐州会战的抗日将领韩德勤(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苏省主席)所属的抗日主力部队,地盘得到迅速扩充,导致被服一时不够用。姚俅便带着父亲来到滨海县的天场乡,找“妇救会”(当时的妇女抗日救国组织)赶制军需被服。
碰巧母亲为躲战乱,已在1938年底躲到天场她哥哥钱亚民(我三舅)家。在这里,母亲因她的女红手艺而被妇救会相中,经劝说参加了被服缝制组织,并为佼佼者。
41年过年后的一天,父亲来到缝制组,就此初次见到了我的母亲。母亲年轻守寡,将近10年,几乎从来没有接触过什么外人。她后来告诉我们,在妇救会里第一次见到陌生的挎盒子枪的父亲时,脸一下子红到脖根,一扭头就跑回了舅舅家。当时父亲不明就里愣住了,姚俅以为母亲出了什么事,不由分说拉着父亲追到了我舅舅家,劝说母亲回去商量赶制军需。母亲死活不肯迈出房门,最后是姚俅央求舅舅陪着母亲,才解决了问题。
据父亲后来回忆,当时他对母亲根本没有任何儿女私情,一心想的只是赶制被服。此后的3个多月里,父亲多次赶到天场催促军需,也没有和母亲有什么接触,只是在验收大会上着重地表扬了母亲的精湛手艺,这恐怕算是父亲第一次注意到了母亲。
1941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把战线延伸扩展到了南太平洋地区。为了维持战争,它迫切须要建立稳定的“大东亚后方基地”。
从1941年底至1942年春、夏,日本侵略者东拼西凑集中优势兵力对中国的苏北、苏南进行“拉网式扫荡”。作为“主力”的苏北、苏南新四军部队“战略撤退”,分散进入皖、赣山区打游击。县大队这种小型地方武装,决定化整为零,埋藏枪支,分散到民众中,等待时机再图发展。
躲日寇徐图发展 连袂潜沪讨生计
父亲自幼离家学艺,随师父四处闯荡。20岁那年遵从祖父心愿,娶王氏为妻。婚后不久,又为养家而走乡串镇四处揽活。就这样时而在家,时而外出,10多年里,共有5男2女7个孩子(其中两个夭折)。当上大队长,官虽不大,但毕竟名声在外,身份暴露,回家藏身是万万不可能的,投亲靠友,又恐连累他人。前思后想,最后听从了姚俅的建议,渡江南下,潜入上海,隐身于都会的茫茫人海。
计划有了,要实行起来真不容易。首先要从穷乡僻壤的苏北农村奔向千里之遥的大都市,这笔盘缠就不是个小数目。父亲不可能回家去讨取,因为一方面担心一旦回到家,就会被妻儿老小拖住而不得脱身,另一方面恐怕即使回到家,家里也拿不出这笔盘缠,连年战乱父亲长期揽不到大活计,哪有工钱寄回家?而战前打工攒下的钱,也差不多被人口众多的一家老小花费得所剩无几了,父亲只能另想他法。
而此时的母亲也正为无处躲避鬼子的扫荡而发愁。母亲找到妇救会讨计策,无奈妇救会干部个个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正巧姚俅也到天场妇救会找妻子商量一起撤到上海躲藏起来,他看到母亲焦急的神情,就对她说:“不要着急,我让姚白兰(父亲的字)来找你吧,他恐怕也不能在苏北待下去了。”过了几天,父亲便和姚俅再次找到了母亲,并决定让母亲回滨海说服公婆,将乡下土地变卖,所得钱款大部分留作二老养老,剩下的作为盘缠,随父亲隐藏到上海再说。
正苦于无计逃生的母亲要想活命,恐怕也只有这条路可走了。更何况,她所依赖的人是个堂堂县大队大队长,这对她来说,无疑是擎天之柱。他们悄悄地回到了滨海,说服了年迈的公公婆婆,仅仅3天时间,便匆匆卖掉土地,给二老留下足够的养老钱,买了一条小船,又买了一些草席装上船,便跟着父亲驾船渡江南下了。
他们沿长江北岸上行向西,直到江阴附近才横渡长江,然后再沿长江南岸东行。几经周折,终于在1942年4月把船摇进了上海苏州河,并靠近长寿路桥的北岸抛锚停泊下来。
“八一三事变”的中日松沪战役早以让这里成为一片废墟。当时日寇大举进攻上海,对闸北地区进行了狂轰滥炸。从宝山路、铁路上海站向西,沿线一片火海,广肇路、(现天目路)秣陵路(当时上海的货车站,曾经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的指挥部所在地)恒丰路一带几乎被夷为平地。但出人意料奇迹般的留下了一片三层楼房。从恒丰路口起,沿裕通路向西、座南面北一连70多间,尽管墙头屋顶到处都是弹痕累累,留有炸弹爆炸后的残迹,但它却巍巍然屹立在一片断垣残壁之中。事变后,几经修葺,重新入住人口,渐渐变成闸北一个人口密集的居住地。而“三层楼”这一称呼,也就成了上海苏州河以北,长寿路、广肇路以南,恒丰路以西这一大片三角地带的代名,远近闻名。就连祸害中国长达10年之久的“文革”,在全国一片“改地名,换牌号”的浊浪之下,都没能废除它。可惜,在九十年代“引进外资,改造旧城”的浪潮中,被夷为平地(至此,上海所留存的抗日战争时期建筑纪念物恐都已荡然无存了)。当时紧挨着“三层楼”的是一大片难民居住的茅棚。在一排棚户旁,父亲敲敲打打拆掉了小船,用船板搭建了一个仅能容下一张床铺和一张饭桌的小木屋,算是栖身之地了。
母亲曾告诉我,落脚安身之后,父亲并以卖掉草席的钱款为本,跟随同乡曾宝元先生做贩卖布匹的小生意。但是由于经营无方,连连亏本。母亲劝他赶紧收手,并直言相劝道,“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商赚钱的,一个工匠手艺人应该凭本事讨生活。”父亲从此不敢轻言经商,于是就用那剩余的钱添置了一些木匠工具,重操旧业。但是连年战祸很少有人请木匠干活,偶尔帮人修个桌椅板凳,是断难维持生计的。
无奈之中,母亲便开始帮人缝穷。在穷人集中居住的地方,这倒不失是个糊口良策。破衣烂衫的人买不起新衣,缝缝补补就必不可缺了。加上母亲的手艺高超,针脚之细密,缝口之熨贴莫不让人夸赞。渐渐这一大片棚户区内,便人人皆知有这么一位缝纫好手的小脚大妈。活计越来越多,有时不得不连夜赶工,因为有人傍晚送来衣服,第二天必须穿着缝补好的衣衫出门打工。碰到这种情况,母亲总是通宵不眠,赶紧将衣衫缝补妥贴,再将衣服洗净,烘干,褶好,坐在门口等人家上门来取。父亲劝她抓紧时间睡会儿,可母亲总是说:“人家要赶时间,我睡下了,人家来了再叫门,就太花时间了。打一份工也不容易,不能耽误人家上班。”就这样,他们俩一个外出揽活打工,一个在家替人缝补,也就这么勉强地凑活着度过了日寇侵华的尾声。(待续)◇#
──转自《新纪元》周刊
责任编辑:林芳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