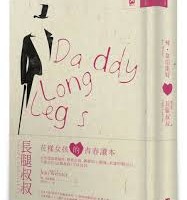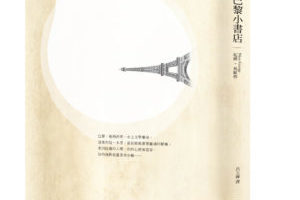童年
1
莉拉出现在我生命里是一年级的时候。我马上对她印象深刻,因为她很坏。
在班上,我们每个人都有点不乖,但只有在导师奥丽维洛没看见的时候才耍花招。可是莉拉不同,她随时随地都很坏。
有一次,她把吸墨纸撕成一小片一小片,泡进墨水里,然后用笔捞起来,丢到同学身上。我的头发被砸中两次,白色的衣领也被丢中一次。老师一如既往扯开喉咙,用我们很害怕的那种像针般又尖又长的声音叫她去黑板后面罚站。
莉拉理都不理,甚至一点也不怕,还是不停丢着浸满墨水的纸片。
奥丽维洛老师在我们眼中是个很老的胖女人,虽然她当年顶多四十出头。她从桌子后面走过来,想狠狠修理一下莉拉,却不知道绊到什么东西,一个踉跄,失去平衡然后跌倒,脸撞上桌角,躺在地板上,像是死了。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我并不记得。我只记得老师那一团黑黑的,一动也不动的身体,以及莉拉盯着她看的严肃表情。
我记得太多这类的意外了。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大人小孩都经常受伤,伤口会流血,化脓,有时候还会死掉。
卖蔬菜水果的阿珊塔太太有个女儿踩到钉子,得破伤风死了。
斯帕努罗太太的么儿因为格鲁布性喉头炎而死掉。
我的一个表哥二十岁的时候死了,因为那天早上出门搬瓦砾的时候被砸了,当天晚上就耳朵嘴巴冒血而死。
我外公是从建筑工地的鹰架上跌下来摔死的。
佩卢索先生的父亲少了一条胳臂,因为一不小心被车床给轧到了。佩卢索先生的太太姬塞琵娜,她姐姐得了结核病,二十二岁就死了。
阿基里阁下的大儿子——我从没见过他,却好像记得他——上战场打仗,死了两次;先是在太平洋淹死,然后又被鲨鱼给吃了。
梅契欧瑞全家人在大轰炸的时候惊恐尖叫,抱在一起死掉了。
老葛罗琳达太太死掉,因为吸进瓦斯而不是空气。
我们上一年级的时候,四年级的吉安尼诺有天看见一颗炸弹,伸手去摸,就被炸死了。
和我们一起在院子里玩的卢吉娜(也不算是玩伴啦,我们只知道她的名字而已)得斑疹性伤寒死了。
我们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充满会要人命的辞汇:格鲁布性喉头炎、斑疹性伤寒、瓦斯、战争、瓦砾、工作、轰炸、炸弹、结核病、感染。就因为这些辞汇和那些年的经验,让我终此一生都怀着许多的恐惧。
你也可能因为那看似正常的东西而死掉。
比方说,如果你浑身是汗,没先将手洗干净,就从水龙头捧凉水喝,很可能会死掉:你身上会起红疹,开始咳嗽,无法呼吸。
你可能因为吃黑莓没吐籽而死掉。
你可能因为嚼美国口香糖,不小心吞下肚而死掉。
你可能因为撞到太阳穴而死掉。太阳穴是格外脆弱的地方,我们向来都很小心的,被石头丢中就可能死掉,但是丢石头又是司空见惯的事。
放学的时候,卖蔬菜水果的阿珊塔那个不知是叫恩佐还是恩祖席欧的儿子,总会领着院子里的一帮男生,朝我们丢石头。他们很不高兴,因为我们比他们聪明。
石头飞来的时候,我们都快快跑开,但是莉拉不这么做,她还是保持正常的步伐,有时候甚至停下来。
莉拉很厉害,超会观察石头飞来的轨道,那种轻松闪避的姿态,如果是在今天,我就知道要形容为“优雅”。她有个哥哥,说不定她是从他那里学来的,我不知道,我没有哥哥,只有弟弟,从他们身上我什么也学不到。
但是,只要一发现她落后了,我就会停下来等她,尽管我很害怕。
即便是在当时,我就已经不知为什么,无法抛下她了。我和她不太熟,我们从没讲过话,虽然我们不管在课堂或课外,都不时较劲。很难以解释的,我总觉得如果抛下她,和其他人一起跑掉,我身上的某个东西就会留她身边,而她永远不会还给我。
起先我躲在墙角后面,探头看看莉拉来了没。然后,既然她不肯让步,我也只好勉强自己加入她的阵营。
我递石头给她,自己也丢几个。但我其实没什么把握,我这辈子做很多事都没什么把握。我总是觉得,我的行为好像和我自己有点脱节。
但是莉拉不同,她从年龄还很小的时候——我没办法精确地说是在六、七岁,或是我们一起爬上阿基里阁下家楼梯的八岁快九岁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绝对坚定的个性。
不管手里握着的是三色笔的笔杆还是石头,或漆黑楼梯的栏杆,接下来要做什么——把笔精准地戳进课桌木头里,丢墨水弹,把那些男生赶出院子,爬上阿基里阁下家的楼梯——她都半点也不犹豫。
那帮男生从铁道的路堤发动攻击,武器就是铁轨路基的石头。带头的恩佐是个很可怕的小孩,一头金发剪得短短的,眼睛颜色很淡。他起码比我们大三岁,但是留级一年。
他丢的是个头小,但边缘尖利的石头,而且丢得非常之准。但是莉拉总是等着他的石头飞过来,再好好表现她的闪躲技术,这让他更生气,丢石头丢得更凶狠。
有一次我们击中他的右小腿,我之所以说“我们”,因为是我把一块边缘尖锐的扁平石块交给莉拉的。这块石头像刀片一样划过恩佐的皮肤,留下一道红色伤口,立刻冒出血来。
恩佐看着自己受伤的腿。我清清楚楚看见:他用拇指和食指夹住一块石头,准备要丢,他的手臂已经举了起来,却停住了,非常迷惑似的。他麾下的那些男生也不可置信地看着他腿上的血。
然而莉拉没对自己的战果表现出丝毫的满意之情,弯腰捡起另一块石头。我拉着她的手肘,这是我们第一次的肢体接触,猝不及防,胆颤心惊的接触。我觉得那帮人会更火大,所以想要彻退。
但是来不及了。恩佐虽然小腿流血,却从恍惚的状态醒过来,丢出手中的石头。那块石头击中她的头,打得她从我身边晃开。一秒钟之后,她倒在人行道上,额头有一道伤口。
2
奥丽维洛老师从课桌跌下来撞到头那天,如同我之前说的,我以为她死掉了,在工作的时候死掉,就像我祖父和玫利娜的丈夫一样。在我看来,莉拉也会因为自己招来的严厉惩罚而难逃一死。
结果呢?经过一段我也说不上来多久的时间——不知是短是长——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她们就只是消失了,老师和学生,两人消失了好几天,从我们的记忆里消失了。
接着,一切都出人意表。奥丽维洛老师回到学校来,活得好好的,开始关心莉拉。我们以为她会惩罚莉拉,因为这是很自然的事。但她没有,反而表扬莉拉。
这个新的阶段是从莉拉的妈妈,瑟鲁罗太太被叫到学校来的那天开始的。
有天早上,工友敲敲门,说瑟鲁罗太太来了。伦吉雅.瑟鲁罗走了进来,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让人认不出来。
她就像我们街坊大部分的妇人一样,平日里总是邋邋遢遢,穿着拖鞋和寒酸的旧衣服,但这天却穿上正式的黑色洋装,提着闪亮的黑色皮包,踩着让她肿胀的双脚饱受折磨的低跟皮鞋。
她把两个纸袋交给老师,一个装着香肠,一个装着咖啡。
老师高高兴兴收下礼物,看着低头瞪课桌的莉拉,对她,也对全班说出了让我极为不解的话。当时我们才刚开始学字母和1到10的数字。我是班上最聪明的学生,认得所有的字母,也知道怎么数1、2、3、4到10,而且我写的字常常得到赞美,甚至还得到老师亲手缝的三色帽花。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尽管莉拉害老师跌倒送医,但是奥丽维洛老师却说她是我们班上最优秀的学生。
没错,她是调皮捣蛋。
没错,她老是往我们身上丢浸满墨水的吸墨纸。
没错,若不是这女生这么搞怪,身为老师的她就不会跌倒,伤到脸颊。
没错,她是常常不得不处罚莉拉,拿木头教鞭打她,或罚她跪在黑板后面的硬地板上。
但是,身为老师,身为一个人,有个让她喜悦万分的事实,她几天前不小心发现的惊人事实。
说到这里她停了一下,仿佛言语还不足以形容,或者是她希望让莉拉的母亲和我们知道,这伟大的功迹永远难以用言语道尽。她拿起粉笔,在黑板写了一个字(我其实不记得是什么字,因为当时我还不识字,所以现在这字是我随便乱掰的):“日”。然后她问莉拉:
“瑟鲁罗,黑板上是什么字?”
全班好奇地陷入沉默。莉拉要笑不笑,露出一脸怪相,身体往旁边一歪,靠到显然很火大的同桌同学身上。然后,郁郁念道:
“日。”
伦吉雅.瑟鲁罗看着老师,表情很迟疑,近乎恐惧。
老师起初不懂,为什么她自己的热情没有映照在这位妈妈眼睛里。
接着,她揣测,说不定伦吉雅自己并不识字,或者并不确定写在黑板上的字就是“日”。
老师皱起眉头,半是为厘清瑟鲁罗太太的情况,半是为表扬我们的这位同学,所以对莉拉说:
“很好,黑板上这个字的确是‘日’。”
接着,她要求莉拉:
“过来,瑟鲁罗,到黑板这边来。”
莉拉很不情愿地走到黑板前面,老师把粉笔交给她。
“写,”她对莉拉说:“‘粉笔’。”
莉拉用颤抖的手,非常专心地写,一个个字母高高低低的,写出:“chak”。
奥丽维洛老师添上一个“l”,瑟鲁罗太太看见老师修正这个字,很绝望地对女儿说:
“你写错了。”
“不,不,不,莉拉是需要练习没错,但是她已经会认字了。她已经会写字了。是谁教她的?”
瑟鲁罗太太垂下眼睛,说:“不是我。”
“但是在你家,或你家的那栋楼里,有没有人可能教她?”
伦吉雅不太肯定地摇摇头。
于是老师转头看莉拉,用非常真心赞赏的语气,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问她:“谁教你认字和写字的,瑟鲁罗?”
瑟鲁罗,这个黑发黑眼,黑罩衫领口有条红缎带,年仅六岁的小女生回答说:“我自己。”◇(节录完)
——节录自《那不勒斯故事》/大块文化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