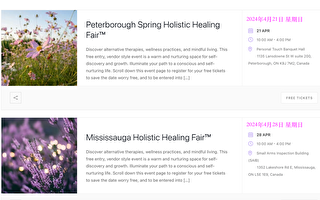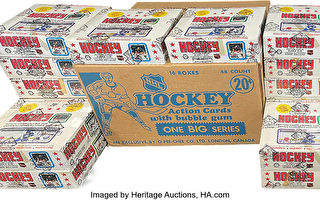【大纪元2017年08月16日讯】看到吧,王子草都要长到人头那么高了。
好几次,我回老家,在爷爷的墓前,母亲都这样说。
在我们湖北老家,有这样一种说法:坟头上的王子草(茅草)长势越好,后人就越新旺发达。
生活无止无休的动荡。多年来,我的生活被卷进了季节的淤滞之中,在同一个地方来回地打着转,爷爷坟头上王子草的庇荫,仿佛是刻意绕过了我。反正,在我身上,丝毫看不到发达的迹象。
母亲嘴上说王子草长的旺盛,实则是在宽慰我不要灰心。
和亲人们拉家常,唯有把话题转到童年时光,我才会变得活泛和健谈,一起经历过的事情,都还记得清楚,尽管前后脉络和情节全是空白,但是一个个场景的色彩却鲜明地浮现在当事人的脑海里。
“记得妹妹一个人躲在廊檐下吃柑子,躲着我和弟弟。”
大我五岁的姐姐揭露我小时候吃独食。“还记得不———抬猪,你每天睡觉前都要玩抬猪。有一次,我和姐姐故意把你抛到地上,你扯着嗓子嚎,害得我们挨一顿打。”
我头上的小哥也参与对我这个淘气妹妹的控诉。抬猪,姐姐和小哥独创的游戏。睡觉前,姐姐和小哥各自站在床头床尾,各自拎着被子的两角,我则躺在被子上,任由他们两个往上抛,接住,再抛,再接住。我高兴的咯咯笑,他们累的胳膊酸疼。那晚,大概是我赖着不下来,惹恼了他们,姐弟俩联手把我给抛到了地上。
“妹妹小时候真的很霸道。横。六一儿童节,我和同学有一个舞蹈节目,同学借穿了她的紫红灯芯绒上衣,正在台上表演,妹妹在台下瞧见了,不干,爬上戏台,非得让人家当场脱下来。”姐姐说到这里,笑。听的人也都笑。
我们就这样确认着彼此共有的各种场景。他们说的,有的我还记得,有一些,我想不起来了。
记忆中我有偷吃过南瓜子。那是来年做种子的。怕我和小哥偷吃,母亲把南瓜子装在布袋里,悬挂在在天花板的正中央。我仰头观察了几次,终于想出了办法,用细竹竿去戳那个布袋子,功夫不负有心人,那布袋子被我戳了一个小洞,想吃的时候只需用棍子扒拉那个布袋,南瓜子就一颗一颗的往下落。
第二年春天,母亲把布袋解下来准备去播种,发现没剩下几颗,她以为是老鼠,于是,家里那只老黄猫遭了殃,被冠以失职罪,遭到饿饭一天的惩罚。
长路漫漫。在我缺席的这二十多年里,家乡的变化是惊人的。首先是没有了人。八十年代出生的第一批独生子女均已长大成人,或求学或外出打工,一个一个离开了故园,到处可见铁将军把门无人居住的空房。若不是间或有车辆疾驰而过,你会怀疑这里是否还有人烟。
老的人大都走了,一个个走进了土里。偶尔看见路边新耸起的一个坟堆,上面插着白色的清明吊子,凭着记忆,想着这是谁的地界,估摸着里面埋着的又会是谁。有的是不该走的人,还很年轻,疾病或是车祸什么的,听人说起,说的人和听的人都唏嘘。这个世界,很多时候不按规矩出牌。
半老不老的人还留守着,像一片片枯黄的落叶,天气晴好时,他们各自要忙自家的营生,雨天就聚在一起打牌,佝偻的背影,仿佛记忆或梦境里的人物。偶尔也会谈谈在外谋生的儿女。年轻人在外谋着生,他们的父母在家等着死,这是当今社会的普遍真实写照。
其次是没有了水。家门口的小河,过去,一到夏天,男孩子们三三两两,结伴下河游泳扎猛子。而现在差不多彻底干枯了,河滩边满满的,全是淤沙,除了白茫茫一片沙灰,细细的流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唯一没变的,是赌风依旧盛行。在中国,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有人的地方就有麻将,就有赌场。这真的很悲哀!可我们却无力去批判———醒目的贫富差别,东西部地域的差别,从上到下,大小官员鱼肉欺诈百姓的事件屡出不穷,被压在最底层的民众,麻木是他们生存状态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这世上,有太多十字路口,有的通往光明,有的通往黑暗,而在极权国家,民众根本没有选择的自由。民众集体的麻木,成了社会稳定的大法码。换言之,我们所谓的社会稳定,所依赖的,正是底层百姓无意识的集体麻木。远的不说,就说现在,社会分裂如此严重,可有些人不仅看不到,反倒还觉得眼前一片歌舞升平。
一旦民众从麻木中醒来将是如何的天翻地覆!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很多很多……
由此,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意识形态(奴化)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一切,都是统治阶级为了统治的需要。
除此,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了。
责任编辑:岳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