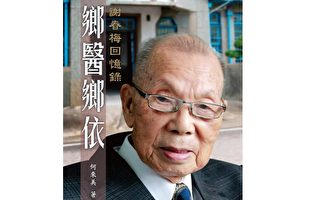(续前文)
*母亲发挥惊人的好运气
照护机构的入住申请,并不是依“申请顺序”入住。
申请入住的文件中,会写明当事人是什么状况而希望入住。各机构如果有空额,就会比较申请人的状况,从“认为最有需要的人”开始接纳。就像前面写的,特别养护老人院和团体家屋都大排长龙,感觉需要很久才能轮到。参观的时候我们得到的说明是“如果运气好,立刻就可以住进来,但也可能要等很久,无法一概而论”。
特别养护老人院因为二○一五年四月的制度修正,原本“需支援二”的人就可以入住,但现在原则上变成“需照护三”以上才可以入住了。因此据说等待时间缩短了一些,不过在二○一七年一月当时,各家机构的第一线,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敢说“变得更容易入住了”。
年节前后,母亲在妹妹的照护下度过。比起我粗枝大叶的照护方式,同为女性的妹妹似乎更能体贴入微地照护,母亲看起来很高兴。也应该说多亏了妹妹吧,十月的时候令我头痛不已的暴食症状也完全停止了。
妹妹照护的期间,我可以去鹿儿岛出差。一月半妹妹返回德国后,母亲又去短期住宿。这时遇上了一个问题,就是短期寄宿最多只能占“需照护”有效期间(母亲是一年)的一半。这项规定是为了防止家属利用“短期住宿”把老人丢在机构,实质上当成安养院使用的状况。如果母亲排队超过半年,就必须另觅其他的方法。
但这些担心是多余的。没想到母亲在这时候发挥了强大的好运气。
一月十八日,我们兄妹一致同意“这个地方最好”的团体家屋,透过T先生连络“有空额了”。我大吃一惊,连络团体家屋,K院长说她提前去短期住宿的机构见母亲,甚至已经面试结束了。
“我们努力以家庭的方式经营,觉得令堂很适合我们,可以在我们这里一起生活。”
没想到居然这么快就能入住,运气好到不敢相信母亲两年前因为跌倒而错失了难得的新药临床试验机会。
*二○一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四十一年又十个月
入住的时候,我们必须和K院长一起确认一大堆合约内容,捺下许多印章。但想想先前的种种辛苦,这根本不算什么。入住费用除了母亲每个月的年金全额以外,只要我们三兄妹每个月各出一万五千圆,就可以持续支付下去。
如果直接说“要送你去安养院”,母亲一定会惊讶、生气、彻底反抗。我和照顾管理专员T先生多方研究之后,决定在入住的一月三十一日,直接从短期住宿机构转移过去,并向母亲说明:“要把你送去住起来更舒服的地方。”
一月二十日星期五到二十三日星期一,成了母亲在自家生活的最后一段日子。搬进团体家屋后,主治医生也会换成机构的家庭医师。二十一日星期六,是H医生最后一次诊察。照顾管理专员T先生已经向H医生说明状况,医生说:“考虑到现况,我认为搬进团体家屋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由亲人照护,无论如何都有极限,不管再怎么努力,到最后还是会无法保持和颜悦色。放心吧,只要拉开距离,你又可以继续对令堂温柔了。”
就像T先生说的“你够努力了”一样,H医生的话,或许也是对家暴者的制式安慰。即使如此,两年半以来必须一肩扛起照护责任的我听到这话,还是忍不住感激得流下泪来。
我心想这是最后了,准备了特别丰盛的晚餐。
星期六做了寿喜烧。母亲说“好好吃”。
但隔天的星期日一早却不好了。
一早起床,母亲正把被大便弄脏的被子放在膝上,呆呆地看着电视。厕所、床铺和地板,到处沾满了粪便。洗衣机里,被大便弄脏的被单塞进了一半。应该是想要自己收拾善后,拿到洗衣机,记忆却就此中断了。
我脱掉母亲全身的衣物,在浴室用莲蓬头冲掉沾在身上的粪便。然后清扫地板,喷上杀菌剂。脏衣物先浸泡氧系漂白剂,接着用流水冲掉全部的粪便,然后丢进洗衣机。
连我自己都觉得经过这两年半的训练,动作变得相当干净俐落。母亲不停地说“对不起、对不起,让你做这些事”,但说到一半就停住了。没办法,她的记忆无法维持。
都到了这个节骨眼,我还是对于把母亲送进安养院感到十分罪恶。都已经精神承受不了而殴打母亲,实在没资格说这种话,但既然母亲还想继续住在这个家,我还是想要成全她的心愿。但是这样的心情也在清理粪便的过程中消失得一干二净了。
二○一五年七月,母亲肩膀脱臼时,我就决定“母亲还能自行排泄的时候,就在这个家照护她”。而这天早上的排泄失败,让我的心情变得坚定:我能够做的,都已经做了。
虽然有点担心母亲的肠胃,但再怎么说,今晚都是母亲在家的最后一个晚上。不在这时候让母亲享受,更待何时?所以晚上我不惜重本买了高级牛肉,煎了牛排。因为是多脂的霜降肉,量并不多。母亲一样说着“好好吃”,全部吃完了。事实上,我认为母亲肠胃健康,真的是很宝贵的资本。
隔天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一,母亲没有排便失败,清爽地起床了。她在居服员的协助下收拾准备好,浑然不知再也不会回到这个家,以为是要去平常的短期住宿,出门去了。
看着她的背影,我的脑中浮现的是——如果要笑我是动画宅就笑吧——电视动画《红发安妮》(一九七九年)接近尾声的一集〈马修离开我家〉。没错,是前年七月离职的居服员K女士年轻时曾经在同一个职场共事的高畑勋负责演出的一集。在那一集,领养孤儿安妮的马修与玛丽拉兄妹中的哥哥马修离世,描写了他的葬礼。
母亲在亡父兴建的这个家中,度过了一半以上的人生,总共四十一年又十个月。下次可以回家,应该是今年的年底,但从母亲老化的速度来看,也不知道她能否再次归来。
一个家庭的一个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看到地毯的痕迹,涌出真实感
其实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沉浸在这样的感伤之中。接下来的几天忙碌得可怕。
照顾管理专员T先生从事务所借来专门接送轮椅使用者的厢型车,附有升降机,我和T先生用那台车把母亲的东西载到团体家屋去。电视机、边柜、衣柜、换洗的衣物和内衣裤。不够的东西以后再送去就行了。床铺因为上一名入住者(据说过世了)的家人留下来说“请给后面的人使用”,因此我们感激地收下了。
直到最后,我真的受到T先生莫大的关照。T先生说:“这是我份内的工作,不用谢。”但如果没有他的专门知识和切中需求的照护计划,我应该没办法照顾母亲直到今天。
我也连络K院长,讨论送母亲过去的步骤。我说母亲一定又会抗拒到底,但K院长可靠地说:“放心,我们是专家。”
租赁业者到家里来,回收租用的照护床和厕所辅具。由于照护的主体转移到团体家屋,如果下次母亲暂时回家,需要床铺时,就不会有政府补助了。到时候必须全额自费租借。
一月三十一日入住当天,我叫了照护计程车,从短期住宿机构把母亲送去团体家屋。这是专门接送需要照护的老人的计程车,连轮椅或卧床失能的人都可以载。我先去团体家屋等待,不久后母亲坐着照护计程车过来了。
不出所料,她戒心十足地质问我:“不是要回家吗?你到底把我带到哪里了?”
“短期住宿要延长一些,所以我帮你找了个住起来更舒服的地方。”
我搬出预先准备好的“不算谎言的说明”。但母亲听不进去。
“这里是哪里?”
“你要把我怎么样?”
她不停地问,赖在玄关不肯移动。
“接下来由我们接手吧!”
K院长不让母亲听见地小声对我说。
“以前我们也遇过几次这样的情形,令堂很快就会平静下来了。如果看到你在这里,她也会很激动,所以你暂时回去一下比较好。”
母亲还是一样闹脾气不听话。但我认为似乎已经没有我能做的事了,趁着母亲没留神的时候,悄悄回家了。
家里的老狗迎接我回家。
它也已经十五岁了。或许照顾完母亲,接下来就得照顾老狗了。它身为我们家的一分子,陪伴母亲一起生活了十五年。我必须好好地照顾完它这辈子才行。
母亲当成房间使用的起居间地毯,一清二楚地留下照护床的脚的压痕。地毯上也有黄色的污渍。是母亲尿失禁的痕迹。不管怎么清都清不干净。由于母亲有可能暂时回家,所以还不能更换地毯。如果要换新,就是母亲离世以后的事了。
冷不防地,心底涌出“终于告一段落”的真实感来。◇(节录完)
【作者简介】
松浦晋也(Matsuura Shinya)
一九六二年出生于日本东京。庆应义塾大学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毕业,庆应义垫研究所政策传媒研究科修毕。以日经BP社记者身份,于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二年从事太空探索相关采访工作。并经历机械、工程、电脑、广播通讯等领域的采访经验,后来成为独立记者。
——节录自《妈妈,对不起》/ 圆神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余心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