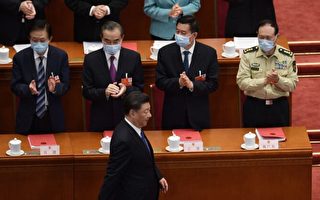【大紀元2021年09月09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Theodore Dalrymple撰文/吳約翰編譯)奧運會已經夠糟糕了!尤其當中共認為奧運會很重要時,你就可以藉此判斷它有多糟糕。
過去的納粹、蘇聯、獨裁者尼古拉‧齊奧塞斯庫所領導下的羅馬尼亞人都認為,獲得數量多的獎牌,就足以證明他們的獨裁是合理的,或者至少有助於他們的國際聲譽。
中國人現在也這麼認為,即使是頭腦更聰明的民主政客,也重視這種空洞又容易被迅速遺忘的勝利。
很難想像對一群人所遭受到的暴政或苦難,僅藉由在奧運會上贏得獎牌,可獲得最微薄的補償。誰會說這樣的話:「我們不敢發聲,如果我們說出來,我們將會被逮捕和折磨,但至少欣慰的是我們的三級跳遠冠軍選手表現得最好」?
殘奧會同樣糟糕,只是表現方式不同。殘疾人士之間共同競爭的想法其實非常複雜,因為他們所面臨的障礙是如此的不同,以下是有資格參加比賽的殘疾相關列表:
肌肉力量受損(即腿部、下半身或所有四肢癱瘓);被動關節活動範圍受損;四肢缺陷(無論是先天性,還是後天由於疾病或外傷所致);腿長差異(長短腿);身材矮小(低於平均);肌肉僵直(中樞神經系統受損引起的肌肉張力增加);共濟失調(中樞神經系統受損導致運動不協調);手足徐動症(中樞神經系統受損引起的緩慢、不自主的動作);視力障礙;智能障礙。
我們被告知,每項運動的等級,由損傷及其影響運動員的程度作決定,每個等級分配有不同的字母和數字。但是,如何平衡脊椎側彎與失明,或一條腿與低智商之間的差異?更不用說可能且確實經常發生的多種變化和組合了。
根據殘疾的嚴重程度,對人們進行分類,以便他們可以在公共場合相互競爭,這在我看來,本質上是令人反感的。
確實,在一兩個世紀之後,我們的後代可能會像我們在今日回顧當時羅馬奧運會上的野蠻一樣;或回顧維多利亞時期,在遊樂場上展示畸形人的猥褻那般,去看待現今的殘奧會。也就是說,我們正表現出一種缺乏考量和殘酷的感受。
但這不是我要強調的觀點,在我看來,殘奧會最重要的是,要喚起普通民眾的熱情;然而,這儼然已經受到大量有利於他們的宣傳活動的影響了。
這種宣傳是相對較新的手段,並且有一種近乎集權中央化的感覺,好像有人在某個地方判定人們的靈魂需要改變,因為他們在道德上有缺陷。
其實這種宣傳是陰險及邪惡的,因為它顯然意味著,如果反對殘奧,將被視為對殘奧會的冷漠,甚至是敵視殘疾人士的困境:要麼你必須完全接受殘奧會;要麼你認為不應該為殘疾人士做任何努力,去讓他們的生活盡可能正常或豐富,並只是想將他們隱藏在機構中,因為他們的存在使你感到不安。
於是就用當前習以為常的方式,建立一種錯誤的二分法:要麼接受當前對某事的佯裝熱絡;要麼扮演中世紀反派角色。這是許多現代運動,用來推進其議程的手段。例如,如果你覺得女性拳擊令人反感,那麼你就必須選擇不支持女性在她們的職業類別中獲得進展,並只將她們侷限在和兒童、廚房及教堂相關的職業中(正如德國人過去常說的那樣)。
這也是反種族主義者使用的一種技倆(必須承認,非常有效)。如果你不同意他們所說的一切,你就相當於三K黨的活躍成員,不允許有中間立場存在。單純是非種族主義者的可能性也不存在。
你要麼是信徒,要麼是異教徒,而異教徒將被處以火刑(比喻性的)。目前,只要把你從正義的圈子裡(例如,學術界)踢出去就足夠矣。
我將殘奧會與馬德里普拉多博物館裡的維拉斯奎茲(Velasquez)名畫《宮女》作了番比較,它描繪出西班牙菲利普四世宮廷的矮人,以及可能患有先天性甲狀腺功能低下症的弱智男孩。
這些畫作傳遞出真正的道德教育,任何經過仔細思考的人,應該都不會忘記,即使是這樣的(殘疾)人,也是人類成員之一,但令我們感到羞恥的是,我們之中也有很多人容易忘記這部分。
所以,這些畫作提醒了人們,人類道德的一致性(所有人都被創造為擁有平等的權利,即視為目標而非手段的平等權利)。但殘奧會恰恰相反:它永遠不會讓我們忘記參賽者(指:殘疾人士)和我們之間的差異。
如果殘疾人士有機會參加體育運動,這是一件極好的事,但絕不能變為向他人提供窺視奇觀的一種手段。運動,應該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娛樂,或是請容許我這麼說,是為了他們的靈魂。
媒體對於殘奧會的廣泛報導,有一種欺凌的成分,因為它對觀眾或讀者在心理層面上所要求的,其實不太可能做到。
媒體應該同時將這些比賽,視為與其它比賽無異,而不是去關注它們的高度異常性質,並且絕不會去評論,例如選手以單腿奔跑的非凡速度(儘管藉助現代科技),同時以社會包容的名義,來讚賞或認同比賽是仁慈的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運作(註)。
註:社會工程,是社會科學中的一門學科,是指透過政府、媒體或私人團體大規模影響特定的態度和社會行為,以便在目標人群中產生所需的特性。社會工程也可以從哲學上理解為一種實現新的社會建構的意圖和目標的確定性現象。
要同時記住這兩件事是不太可能的,即要求觀眾或讀者既要「注意」,又要「不注意」。就像心理學家最愛的一幅心理測驗圖(點擊這裡可看),在花瓶和兩位女士臉部輪廓之間:一次只能看到一種圖像。
這會導致一種不舒服的心理狀態,在這種狀態下,觀眾或讀者會因為注意到他不應該注意到的東西而感到罪惡,卻反而沒有注意到他應該注意到的東西。
就我自己而言,我懷疑我的想法和感受被殘奧會所操縱。某些人或一群人有權讓我們覺得可以成為比自己更好的人,他們就是斯大林所說的作家: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作者簡介:
西奧多‧達倫波(Theodore Dalrymple)是一位退休醫生。他是《紐約城市季刊》(City Journal of New York)的特約編輯及三十多本書籍的作者,作品包括《底層生活》(Life at the Bottom),最新著作是《禁運和其它故事》(Embargo and Other Stories)。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原文:The Impossible Dual Focus of the Paralympic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責任編輯:高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