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番騰似轉輪,眼前凶吉未為真;
請看久久分明應,天道何曾負善人?
聞得老郎們相傳的說話,不記得何州甚縣,單說有一人,姓金,名孝,年長未娶,家中只有個老母,自家賣油為生。一日挑了油擔出門,中途因裏急,走上茅廁大解,拾得一個市裹肚,內有一包銀子,約莫有三十兩。
金孝不勝歡喜,便轉擔回家,對老娘說道:「我今日造化,拾得許多銀子。」老娘看見,到吃了一驚,道:「你莫非做下歹事偷來的麼?」金孝道:「我幾曾偷慣了別人的東西?卻恁般說!早是鄰舍不曾聽得哩。這裹肚其實不知什麼人遺失在茅坑旁邊,喜得我先看見了,拾取回來。我們做窮經紀的人,容易得這主大財?明日燒個利市,把來做販油的本錢,不強似賒別人的油賣?」老娘道:「我兒,常言道:『貧富皆由命』,你若命該享用,不生在挑油擔的人家來了。依我看來,這銀子雖非是你設心謀得來的,也不是你辛苦掙來的,只怕無功受祿,反受其殃。這銀子不知是本地人的?遠方客人的?又不知是自家的?或是借貸來的?一時間失脫了,抓尋不見,這一場煩惱非小,連性命都失圖了也不可知。曾聞古人裴度還帶積德,你今日原到拾銀之處,看有甚人來尋,便引來還他原物,也是一番陰德,皇天必不負你。」
金孝是個本分的人,被老娘教訓了一場,連聲應道:「說得是,說得是!」放下銀包裹肚,跑到那茅廁邊去。只見鬧嚷嚷的一叢人圍著一個漢子,那漢子氣忿忿的叫天叫地。金孝上前問其緣故。原來那漢子是他方客人,因登東,解脫了裹肚,失了銀子,找尋不見。只道卸下茅坑,喚幾個潑皮來,正要下去淘摸,街上人都擁著閑看。
金孝便問客人道:「你銀子有多少?」客人胡亂應道:「有四五十兩。」金孝老實,便道:「可有個白布裹肚麼?」客人一把扯住金孝,道:「正是,正是!是你拾著?!還了我,情願出賞錢。」眾人中有快嘴的便道:「依著道理,平半分也是該的。」金孝道:「真個是我拾得,放在家裏,你只隨我去便有。」眾人都想道:「拾得錢財,巴不得瞞過了人。那曾見這個人到去尋主兒還他?也是異事。」金孝和客人動身時,這夥人一哄都跟了去。
金孝到了家中,雙手兒捧出裹肚,交還客人。客人撿出銀包看時,曉得原物不動。只怕金孝要他出賞錢,又怕眾人喬主張他平分,反使欺心,賴著金孝,道:「我的銀子,原說有四五十兩,如今只剩得這些,你匿過一半了,可將來還我!」金孝道:「我才拾得回來,就被老娘逼我出門,尋訪原主還他,何曾動你分毫?」那客人賴定短少了他的銀兩。金孝負屈忿恨,一個頭肘子撞去,那客人力大,把金孝一把頭髮提起,像隻小雞一般放番在地,捻著拳頭便要打。引得金孝七十歲的老娘,也奔出門前叫屈。眾人都有些不平,似殺陣般嚷將起來。恰好縣尹相公在這街上過去,聽得喧嚷,歇了轎,分付做公的拿來審問。眾人怕事的,四散走開去了;也有幾個大膽的,站在旁邊看縣尹相公怎生斷這公事。
卻說做公的將客人和金孝母子拿到縣尹面前,當街跪下,各訴其情。一邊道:「他拾了小人的銀子,藏過一半不還。」一邊道:「小人聽了母親言語,好意還他,他反來圖賴小人。」縣尹問眾人:「誰做證見?」眾人都上前稟道:「那客人脫了銀子,正在茅廁邊抓尋不著,卻是金孝自走來承認了,引他回去還他。這是小人們眾目共睹。只銀子數目多少,小人不知。」縣令道:「你兩下不須爭嚷,我自有道理。」教做公的帶那一干人到縣來。
縣尹升堂,眾人跪在下面。縣尹教取裹肚和銀子上來,分付庫吏,把銀子兌准回覆。庫吏覆道:「有三十兩。」縣主又問客人道:「你銀子是許多?」客人道:「五十兩。」縣主道:「你看見他拾取的,還是他自家承認的?」客人道:「實是他親口承認的。」縣主道:「他若是要賴你的銀子,何不全包都拿了?卻止藏一半,又自家招認出來?他不招認,你如何曉得?可見他沒有賴銀之情了。你失的銀子是五十兩,他拾的是三十兩,這銀子不是你的,必然另是一個人失落的。」客人道:「這銀子實是小人的,小人情願只領這三十兩去罷。」縣尹道:「數目不同,如何冒認得去?這銀兩合斷與金孝領去,奉養母親;你的五十兩,自去抓尋。」
金孝得了銀子,千恩萬謝的扶著老娘去了。那客人已經官斷,如何敢爭?只得含羞噙淚而去。眾人無不稱快。這叫做:欲圖他人,翻失自己。自己羞慚,他人歡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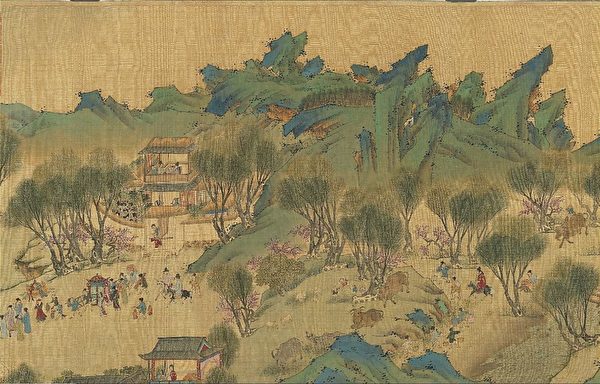
看官,今日聽我說「金釵鈿」這樁奇事。有老婆的翻沒了老婆,沒老婆的翻得了老婆。只如金孝和客人兩個,圖銀子的翻失了銀子,不要銀子的翻得了銀子。事跡雖異,天理則同。
卻說江西贛州府石城縣有個魯廉憲,一生為官清介,並不要錢,人都稱為「魯白水」。那魯廉憲與同縣顧僉事累世通家,魯家一子,雙名學曾;顧家一女,小名阿秀,兩下面約為婚,來往間親家相呼,非止一日。
因魯奶奶病故,廉憲攜著孩兒在於任所,一向遷延,不曾行得大禮。誰知廉憲在任一病身亡。學曾扶柩回家,守制三年,家事愈加消乏,止存下幾間破房子,連口食都不周了。顧僉事見女婿窮得不像樣,遂有悔親之意,與夫人孟氏商議道:「魯家一貧如洗,眼見得六禮難備,婚娶無期。不若別求良姻,庶不誤女兒終身之托。」孟夫人道:「魯家雖然窮了,從幼許下的親事,將何辭以絕之?」顧僉事道:「如今只差人去說男長女大,催他行禮。兩邊都是宦家,各有體面,說不得『沒有』兩個字,也要出得他的門,入的我的戶。那窮鬼自知無力,必然情願退親。我就要了他休書,卻不一刀兩斷?」孟夫人道:「我家阿秀性子有些古怪,只怕他到不肯。」顧僉事道:「在家從父,這也由不得他,你只慢慢的勸他便了。」
當下孟夫人走到女兒房中,說知此情。阿秀道:「婦人之義,從一而終;婚姻論財,夷虜之道。爹爹如此欺貧重富,全沒人倫,決難從命。」孟夫人道:「如今爹去催魯家行禮,他若行不起禮,倒願退親,你只索罷休。」阿秀道:「說那裏話!若魯家貧不能聘,孩兒情願守志終身,決不改適。當初錢玉蓮投江全節,留名萬古。爹爹若是見逼,孩兒就拚卻一命,亦有何難!」
孟夫人見女執性,又苦他,又憐他,心生一計:除非瞞過僉事,密地喚魯公子來,助他些東西,教他作速行聘,方成其美。
忽一日,顧僉事往東莊收租,有好幾日擔閣。孟夫人與女兒商量停當了,喚園公老歐到來。夫人當面分付,教他去請魯公子後門相會,如此如此,「不可洩漏,我自有重賞。」
老園公領命,來到魯家。但見門如敗寺,屋似破窯,窗槅離披,一任風聲開閉;廚房冷落,絕無煙氣蒸騰。頹牆漏瓦權棲足,只怕雨來;舊椅破床便當柴,也少火力。
盡說宦家門戶倒,誰憐清吏子孫貧?說不盡魯家窮處。卻說魯學曾有個姑娘,嫁在梁家,離城將有十里之地。姑夫已死,止存一子梁尚賓,新娶得一房好娘子,三口兒一處過活,家道粗足。
這一日,魯公子恰好到他家借米去了,只有個燒火的白髮婆婆在家。老管家只得傳了夫人之命,教他作速寄信去請公子回來:「此是夫人美情,趁這幾日老爺不在家中,專等專等,不可失信。」囑罷自去了。
這裏老婆子想道:「此事不可遲緩,也不好轉托他人傳話。當初奶奶存日,曾跟到姑娘家去,有些影像在肚裏。」當下囑付鄰人看門,一步一跌的問到梁家。梁媽媽正留著侄兒在房中吃飯。婆子向前相見,把老園公言語細細述了。姑娘道:「此是美事!」攛掇侄兒快去。
魯公子心中不勝歡喜,只是身上藍縷,不好見得岳母,要與表兄梁尚賓借件衣服遮醜。原來梁尚賓是個不守本分的歹人,早打下欺心草稿,便答應道:「衣服自有,只是今日進城,天色已晚了。宦家門牆,不知深淺,令岳母夫人雖然有話,眾人未必盡知,去時也須仔細。憑著愚見,還屈賢弟在此草榻,明日只可早往,不可晚行。」魯公子道:「哥哥說得是。」梁尚賓道:「愚兄還要到東村一個人家,商量一件小事,回來再得奉陪。」又囑付梁媽媽道:「婆子走路辛苦,一發留他過宿,明日去罷。」
媽媽也只道孩兒是個好意,真個把兩人都留住了。誰知他是個奸計:只怕婆子回去時,那邊老園公又來相請,露出魯公子不曾回家的消息,自己不好去打脫冒了。正是:欺天行當人難識,立地機關鬼不知。

梁尚賓背卻公子,換了一套新裝,悄地出門,徑投城中顧僉事家來。
卻說孟夫人是晚教老園公開了園門伺候。看看日落西山,黑影裏只見一個後生,身上穿得齊齊整整,腳兒走得慌慌張張,望著園門欲進不進的。老園公問道:「郎君可是魯公子麼?」梁尚賓連忙鞠個躬,應道:「在下正是。因老夫人見召,特地到此,望乞通報。」老園公慌忙請到亭子中暫住,急急的進去報與夫人。孟夫人就差個管家婆出來傳話:「請公子到內室相見。」
才下得亭子,又有兩個丫環提著兩碗紗燈來接。彎彎曲曲行過多少房子,忽見朱樓畫閣方是內室。孟夫人揭起朱簾,秉燭而待。
那梁尚賓一來是個小家出身,不曾見恁般富貴樣子;二來是個村郎,不通文墨;三來自知假貨,終是懷著個鬼胎,意氣不甚舒展。上前相見時,跪拜應答,眼見得禮貌粗疏,語言澀滯。
孟夫人心下想道:「好怪!全不像宦家子弟。」一念又想道:「常言人貧智短,他恁地貧困,如何怪得他失張失智?」轉了第二個念頭,心下愈加可憐起來。茶罷,夫人分付忙排夜飯,就請小姐出來相見。
阿秀初時不肯,被母親逼了兩三次,想道:「父親有賴婚之意,萬一如此,今宵便是永訣。若得見親夫一面,死亦甘心。」當下離了繡閣,含羞而出。孟夫人道:「我兒過來見了公子,只行小禮罷。」假公子朝上連作兩個揖,阿秀也福了兩福,便要回步。夫人道:「既是夫妻,何妨同坐?」便教他在自己肩下坐了。假公子兩眼只瞧那小姐,見他生得端麗,骨髓裏都發癢起來。這裏阿秀只道見了真丈夫,低頭無語,滿腹恓惶,只饒得哭下一場。正是:真假不同,心腸各別。
少頃,飲饌已到,夫人教排做兩桌,上面一桌請公子坐,打橫一桌娘兒兩個同坐。夫人道:「今日倉卒奉邀,只欲周旋公子姻事,殊不成體,休怪休怪!」假公子剛剛謝得個「打攪」二字,面皮都急得通紅了。
席間,夫人把女兒守志一事,略敘一敘。假公子應了一句,縮了半句。夫人也只認他害羞,全不為怪。那假公子在席上自覺局促,本是能飲的,只推量窄,夫人也不強他。又坐了一回,夫人分付收拾鋪陳在東廂下,留公子過夜。假公子也假意作別要行。夫人道:「彼此至親,何拘形跡?我母子還有至言相告。」假公子心中暗喜。只見丫環來稟:「東廂內鋪設已完,請公子安置。」假公子作揖謝酒,丫環掌燈送到東廂去了。
夫人喚女兒進房,趕去侍婢,開了箱籠,取出私房銀子八十兩,又銀盃二對,金首飾一十六件,約值百金,一手交付女兒,說道:「做娘的手中只有這些,你可親去交與公子,助他行聘完婚之費。」阿秀道:「羞答答如何好去?」夫人道:「我兒,禮有經權,事有緩急。如今尷尬之際,不是你親去囑付,把夫妻之情打動他,他如何肯上緊?窮孩子不知世事,倘或與外人商量,被人哄誘,把東西一時花了,不枉了做娘的一片用心?那時悔之何及!這東西也要你袖裏藏去,不可露人眼目。」
阿秀聽了這一班道理,只得依允,便道:「娘,我怎好自去?」夫人道:「我教管家婆跟你去。」當下喚管家婆來到,分付他只等夜深,密地送小姐到東廂,與公子敘話。又附耳道:「送到時,你只在門外等候,省得兩下礙眼,不好交談。」管家婆已會其意了。
再說假公子獨坐在東廂,明知有個蹊蹺緣故,只是不睡。果然,一更之後,管家婆捱門而進,報道:「小姐自來相會。」假公子慌忙迎接,重新敘禮。有這等事,那假公子在夫人前一個字也講不出,及至見了小姐,偏會溫存絮話!這裏小姐,起初害羞,遮遮掩掩,今番背卻夫人,一般也老落起來。兩個你問我答,敘了半晌。阿秀話出衷腸,不覺兩淚交流。那假公子也裝出捶胸嘆氣,揩眼淚縮鼻涕,許多醜態;又假意解勸小姐,抱持綽趣,盡他受用。
管家婆在房門外聽見兩下悲泣,連累他也恓惶,墮下幾點淚來。誰知一邊是真,一邊是假。阿秀在袖中摸出銀兩首飾遞與假公子,再三囑付,自不必說。假公子收過了,便一手抱住小姐把燈兒吹滅,苦要求歡。阿秀怕聲張起來,被丫環們聽見了,壞了大事,只得勉從。有人作《如夢令》詞云:
可惜名花一朵,繡幕深閨藏護。不遇探花郎,抖被狂峰殘破。錯誤!錯誤!怨殺東風分付。
常言事不三思,終有後悔。孟夫人要私贈公子,玉成親事,這是錦片的一團美意,也是天大的一樁事情,如何不教老園公親見公子一面?及至假公子到來,只合當面囑付一番,把東西贈他,再教老園公送他回去,看個下落,萬無一失。千不合,萬不合,教女兒出來相見,又教女兒自往東廂敘話。這分明放一條方便路,如何不做出事來?莫說是假的,就是真的,也使不得,枉做了一世牽扳的話柄。這也算做姑息之愛,反害了女兒的終身。

閒話休題。且說假公子得了便宜,放鬆那小姐去了。五鼓時,夫人教丫環催促起身梳洗,用些茶湯點心之類。又囑付道:「拙夫不久便回,賢婿早做準備,休得怠慢。」假公子別了夫人,出了後花園門,一頭走一頭想道:「我白白裏騙了一個宦家閨女,又得了許多財帛,不曾露出馬腳,萬分僥倖。只是今日魯家又來,不為全美。聽得說顧僉事不久便回,我如今再擔閣他一日,待明日才放他去;若得顧僉事回來,他便不敢去了,這事就十分乾淨了。」計較已定,走到個酒店上自飲三杯,吃飽了肚裏,直延捱到午後,方才回家。
魯公子正等得不耐煩,只為沒有衣服,轉身不得。姑娘也焦躁起來,教莊家往東村尋取兒子,並無蹤跡。走向媳婦田氏房前問道:「兒子衣服有麼?」田氏道:「他自己撿在箱裏,不曾留得鑰匙。」
原來田氏是東村田貢元的女兒,到有十分顏色,又且通書達禮。田貢元原是石城縣中有名的一個豪傑,只為一個有司官與他做對頭,要下手害他;卻是梁尚賓的父親與他舅子魯廉憲說了,廉憲也素聞其名,替他極口分辨,得免其禍。因感激梁家之恩,把這女兒許他為媳。
那田氏像了父親,也帶三分俠氣,見丈夫是個蠢貨,又且不幹好事,心下每每不悅,開口只叫做「村郎」,從此夫婦兩不和順,連衣服之類,都是那「村郎」自家收拾,老婆不去管他。
卻說姑侄兩個正在心焦,只見梁尚賓滿臉春色回家。老娘便罵道:「兄弟在此專等你的衣服,你卻在那裏噇酒,整夜不歸?又沒尋你去處!」梁尚賓不回娘話,一徑到自己房中,把袖裏東西都藏過了,才出來對魯公子道:「偶為小事纏住身子,擔閣了表弟一日,休怪休怪!今日天色又晚了,明日回宅罷。」老娘罵道:「你只顧把件衣服借與做兄弟的,等他自己幹正務,管他今日明日!」魯公子道:「不但衣服,連鞋襪都要告借。」梁尚賓道:「有一雙青段子鞋在間壁皮匠家納底,今晚催來,明日早奉穿去。」魯公子沒奈何,只得又住了一宿。
到明朝,梁尚賓只推頭疼,又睡個日高三丈,早飯都吃過了,方才起身,把道袍、鞋、襪慢慢的逐件搬將出來,無非要延捱時刻,誤其美事。魯公子不敢就穿,又借個包袱兒包好,付與老婆子拿了。姑娘收拾一包白米和些瓜菜之類,喚個莊客送公子回去,又囑付道:「若親事就緒,可來回覆我一聲,省得我牽掛。」魯公子作揖轉身,梁尚賓相送一步,又說道:「兄弟,你此去須是仔細,不知他意兒好歹?真假何如?依我說,不如只往前門硬挺著身子進去,怕不是他親女婿,趕你出來?又且他家差老園公請你,有憑有據,須不是你自輕自賤。他有好意,自然相請;若是翻轉臉來,你拚得與他訴落一場,也教街坊上人曉得。倘到後園曠野之地,被他暗算,你卻沒有個退步。」魯公子又道:「哥哥說得是。」正是:背後害他當面好,有心人對沒心人。
魯公子回到家裏,將衣服鞋襪裝扮起來。只有頭巾分寸不對,不曾借得。把舊的脫將下來,用清水擺淨,教婆子在鄰舍家借個熨斗,吹些火來熨得直直的,有些磨壞的去處,再把些飯兒粘得硬硬的,墨兒塗得黑黑的。只是這頂巾,也弄了一個多時辰,左帶右帶,只怕不正。教婆子看得件件停當了,方才移步徑投顧僉事家來。
門公認是生客,回道:「老爺東莊去了。」魯公子終是宦家子弟,不慌不忙的說道:「可通報老夫人,說道魯某在此。」門公方知是魯公子,卻不曉得來情,便道:「老爺不在家,小人不敢亂傳。」魯公子道:「老夫人有命,喚我到來,你去通報自知,須不連累你們。」門公傳話進去,稟說:「魯公子在外要見,還是留他進來,還是辭他?」
孟夫人聽說,吃了一驚,想:「他前日去得,如何又來?且請到正廳坐下。」先教管家婆出去,問他有何話說。管家婆出來瞧了一瞧,慌忙轉身進去,對老夫人道:「這公子是假的,不是前夜的臉兒。前夜是胖胖兒的,黑黑兒的;如今是白白兒的,瘦瘦兒的。」夫人不信道:「有這等事!」親到後堂,從簾內張看,果然不是了。
孟夫人心上委決不下,教管家婆出去,細細把家事盤問,他答來一字無差。孟夫人初見假公子之時,心中原有些疑惑;今番的人才清秀,語言文雅,倒像真公子的樣子。再問他今日為何而來,答道:「前蒙老園公傳語呼喚,因魯某羈滯鄉間,今早才回,特來參謁,望恕遲誤之罪。」夫人道:「這是真情無疑了。只不知前夜打脫冒的冤家又是那裏來的?」慌忙轉身進房,與女兒說其緣故,又道:「這都是做爹的不存天理,害你如此,悔之不及!幸而沒人知道,往事不須題了。如今女婿在外,是我特地請來的,無物相贈,如之奈何?」正是:只因一著錯,滿盤都是空。
阿秀聽罷,呆了半晌。那時一肚子情懷,好難描寫:說慌又不是慌,說羞又不是羞,說惱又不是惱,說苦又不是苦;分明似亂針刺體,痛癢難言。喜得他志氣過人,早有了三分主意,便道:「母親且與他相見,我自有道理。」(待續)
——摘自明朝超級暢銷小說《喻世明言》
點閱【經典小說選登】系列文章。
責任編輯:李婧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