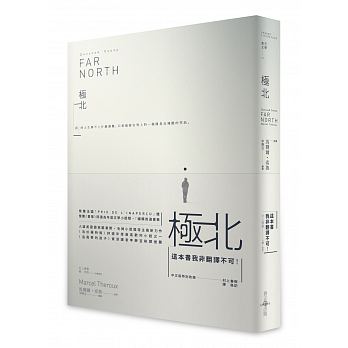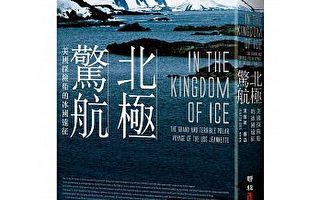我用托盘端给他一壶热水、镊子、纱布,和大蒜肥皂,让他自己去搞。而且我把他的门锁起来,以策安全。
我把麻布袋里的书摆在客厅的书架上。这些书全都是奇奇怪怪的尺寸,所以没办法像爸妈的书那样摆得整整齐齐的。有几本是图文书。我很纳闷男孩是要拿这些书去看,还是去烧。我确信自己知道答案。
烧掉的书总是会让我有点心情沉重。
□
我每用掉一颗子弹,就逼自己立刻再做五颗。我遵守这个规则,已经有好一阵子了。我的子弹成本极高,不管是花的时间,或是为了熔炼而耗费的燃料。花了这么高的代价去做出品质这么差的东西,实在很不划算。
但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燃料用罄了,总还是可以找得到,我可以劈开一些硬木,做成木炭甚至可以烧掉自动钢琴——老天垂怜,如果非这样做不可的话。但你绝对不该任凭事态恶化,掉以轻心,让子弹供给不足。
如果你能找到一个愿意和你做买卖的人,子弹当然会有个市场的公定价格。但是万一有人找你碴,招来一群狐群狗党不放你甘休,这时一颗子弹又值多少?为了不听见你的枪上膛时半颗子弹都没有的声音,你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此外,我也喜欢自己动手做。我喜欢金属熔化的过程。我喜欢蹲在熔炉旁边,透过我父亲那副烟灰色眼镜的镜片看着火焰,看着铅像水银那样流动。我喜欢物质转化的过程,喜欢早上从模子的沙土里剥下那冰冷丑陋的金属块。
问题是,理所当然,我的子弹一点都不精良。如果要再次开枪射击,我会希望用的是纯精钢打造,闪闪发亮的精良子弹,而不是像我做的这种丑不拉叽的东西,活像有人丢在马蹄铁匠铺里的地板上,沾满天晓得是什么的泥土和细菌。
做好五颗子弹之后,我带了一些食物和水,以及一盏酒精灯到男孩床边。他在发烧,眼睛闭着,但在眼皮底下微微翻动。短而粗密的睫毛。披散在枕头上的蓝黑色头发,让我想起乌鸦的翅膀。他嘴里念念有词,用的是他自己的语言。
便盆是空的,但我拿走男孩那件发臭的蓝色连身袍。他可以穿查洛的衣服,如果他活下来的话。
□
天刚破晓,我端了早餐给他。
他的皮肤连一丝黄色都没有,白得像骸骨。两鬓有淡黑色的头发,但唇上与两颊都没有胡子。
我留给他的食物,他全吃光光,但我转身去拿便盆的时候,他却生气了。他很害羞。这时我知道自己喜欢他:我差点杀了他,但他却羞于让我看见他的大便。真是个孩子。
我想尽办法用手势表达,要他躺在床上休息。他看起来情况还不太好。但是我才开始打扫马厩,他就出现在院子里。穿着查洛的格纹外套和他的拖鞋,他看起来年纪更轻,个头更小。伤口的包扎让他脚步不稳,但他还是走过来,坐在凳子上看我喂母马吃东西。看见马,他似乎很开心。
“Ma。”他指着她说。
我开始解释我从不给动物取名字,我只叫它们“母马”、“花马”或“灰马”,对于你终有一天要宰来吃的动物,哪有必要取名字。而且把它们看成一块马肉,总比当成是亚当斯基或黛西美儿的身体来得容易应付吧。
但是我没办法让男孩理解我的意思,所以从此后,母马就变成“玛”了。
这时他指着自己,说出一个发音近似“平”的字。没错,平。就像商店门口的铃铛轻响。就像绷开的衬衫扣子。或是拨动的斑鸠琴弦。我很想知道这是哪一种异教徒的名字,还是说有个我没听说过的“圣徒平”存在。
但他就是平。就是这个名字。所以我也自我介绍。我指着自己,说出我的名字:“梅克皮斯”。
他一脸迷惑,皱起脸,仿佛没听清楚似的,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敢念出这个名字。所以我又说了一遍:“梅克皮斯”。
他的脸露出一个大大的咧嘴笑。“没可屁事?”
我仔细地瞧着他,但他并不是要取笑我,只认为那是我的名字。而且既然我念他名字的时候笑了,他怪里怪气的念我的名字也没什么不对嘛。
□
让平住在我家,却又不信任他,显然一点道理都没有。我这人脾气很坏,孤僻独居,疑神疑鬼,而这也是我能活这么多年的原因。除了我之外,最后一个住在这屋檐下的是查洛,但那也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不过当时我想,其实现在也还是这么认为,一旦你让其他人进屋来,你就得完全接纳他。每回骑马离开家门,我就会认为碰见的任何人都打算杀我或抢劫我。但是在自己家里,我可不能这样过日子。
我决定信任平,不是因为我对他有某种直觉,我对他根本一无所知──而是因为这是我能过下去的唯一方法。
然而,午餐时分骑马回来,发现门锁完好无缺,柴薪依旧叠得整整齐齐,小鸡到处啄食,储藏窖里的甘蓝菜和苹果没人动过,我还是有点意外。但是平不见踪影,坦白说,当时想到他可能已经离开了,我心里竟然有点难过。
我匆匆爬上二楼,脚上的靴子踩在楼梯上乒乒乓乓。没有他的影迹。我冲进查洛房间,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大跳。
平在那里,面前摆了一个镜子,我妈的旧针线盒,以及一盏酒精灯。他一根一根拿起旧铁针,在火焰里穿梭,然后戳进耳朵的肉里。
看见我,他露出微笑,而我的惊骇让他笑了起来。他整只耳朵像豪猪身上的刺那样竖起来。针刺进去想必让他痛得要命,但是他没有因为这样而放弃。事实上,他继续把针戳进耳朵里。然后,他小心翼翼地在鼻子上插了一两根针,接着又在肩膀上插了一两根。
我忍耐力很强。我必须如此。但是看见这个画面,还是让我有种怪怪的感觉。
平让我了解他脑筋没有问题,拿针戳身体是为了让肩膀的伤口愈合。但这到底是什么路数的魔法,恐怕我就没办法告诉你了。◇(节录完)
——节录自《极北》/春天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李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