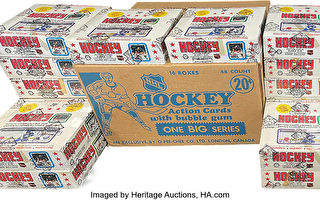【大纪元2023年10月31日讯】文化大革命初期, 人们的道德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人与人友善。我们邻居不出远门一般都不锁门,没听说过谁家丢东西。一栋栋整齐的平房,家家也没有院子;栋与栋之间有铁丝拉的晒衣绳,谁家早晨出门晒了棉被、衣服,不用担心,下雨时,一定会有在家的邻居帮忙收起来。
那个年代物质短缺,买什么都凭票。有一段时间,几乎家家缺灯泡,一到晚上家里黑乎乎的。偶尔来了几张电灯票不够分,就抓阄儿。谁家有特殊困难,大家都会谦让。 那是发自内心的一种习惯行为。我是经常丢钥匙,邻居哥哥姐姐都会帮忙找,感觉就是应该这样的。
邻居李婶,男人死了,自己带着三个孩子。单位照顾给她安排了一份杂工(那时候很多女人是不工作的),到月底经常要借点钱才能过去。我父母属于高工资,她也会找我妈妈借钱,老邻居,钱也不多,有时我妈妈就不要了,但她不管多少一定要还,李婶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她每借一笔钱物,都记在小本子上怕自己忘了。看看现在中国大陆家家都是铁窗铁门,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明抢暗骗,这短短的几十年,人的道德变化太大了。
随着文化大革命深入进行, “文攻武卫” 开始。大批判,大辩论,大字报。我们附近有一个当老师的,邻居陈大娘上中学的儿子立刻响应号召,在那老师家门上贴了一张大字报,陈大娘听说后马上端上一盆清水和抹布,把那老师家的门擦得干干净净,然后再去道歉。 晚上经常听到大人教育孩子的声音, 但社会的力量太大了。
我的“后爸爸”
我上小学了,学校没老师,老师都在外地集中学习改造;课停了,校园里空空荡荡。
我们刚入学的新生都有工宣队、农宣队和几个高年级的小学生代管(叫小老师),天天学毛语录,忆苦思甜,开批斗会,体罚学生等。
我是脖子上挂钥匙的(白天家中大人都上班不在家),中午放学后自己拿饭票去机关食堂吃饭。 每天中午吃饭时,都会看到排着队进食堂的一群人,他们先向毛XX像鞠躬请罪,还要说好多好多请罪的话,才能排队去买饭。不过,轮到他们的时候,也就是些剩饭菜了。我听说他们都是右派分子、是坏人,我觉得这与我没关系。
有一天小老师在班上对我说, 你回家问问你家长,你祖辈是怎样剥削压榨穷人的。从那天起,我就知道我也属于这“一小撮”,我一下就从旁观者变成黑五类崽子。经小老师这一点拨,中午去食堂吃饭的路上,就会有调皮的孩子要打我,吓得我绕道走,有时候都不敢去吃饭。我生性懦弱,特别自卑。
好不容易盼到老师们都改造回来了。我第一任班主任焦老师,她经常在课堂上鼓励学生揭发父母。我知道她先生也是右派。那时讲 “亲不亲阶级分”,要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为了得到老师的表扬,有一段我产生了恶念,想编个故事揭发我爸爸。当然我并没有那样做,如果我真做了,那我必定是家破人亡。
来到海外后,我爸爸让我看一篇报导,讲述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个男孩子由于观点不同揭发她的母亲,导致他当教师的母亲第二天就被活活打死。文章讲述了他如何走过自责、悔恨、凄凉的一生。我听了我爸爸的介绍我没敢看,我知道那是什么。
毛XX讲:“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一天半夜醒来,听到我父母在商量离婚。我妈妈说:“不能让孩子一生受牵连,孩子归我。”我听明白后大哭,我妈妈忙说:“我和你爸爸在说着玩呢。”
不久我父母就带着我去派出所给我改名换姓, 我从此姓朱。
因为我妈妈的大伯抽大烟败光了家产,我姥爷只能是给大财主家扛长工,我妈妈家也因祸得福得了贫雇农成分。那个年代讲血统论,“龙生龙,风生风,老鼠生来会挖洞”。刚刚生下的小婴儿就注定了你的阶级属性,这叫“阶级烙印”。
我改名换姓,搬了家,换了新学校。我参加了学校篮球队,还被选上了军鼓队,好像要开启新的人生。一天我们班转来一个男同学,认识我。他知道我姓朱以后,就在同学中说我父母离婚了,我的后爸爸姓朱等,马上同学们都传播我的新历史。那个年代离婚是件很丢人的事,从此我又成了有后爸爸的可怜娃。
责任编辑: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