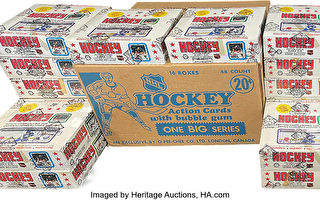【大紀元2023年10月31日訊】文化大革命初期, 人們的道德水平還是比較高的,人與人友善。我們鄰居不出遠門一般都不鎖門,沒聽說過誰家丟東西。一棟棟整齊的平房,家家也沒有院子;棟與棟之間有鐵絲拉的晒衣繩,誰家早晨出門晒了棉被、衣服,不用擔心,下雨時,一定會有在家的鄰居幫忙收起來。
那個年代物質短缺,買什麼都憑票。有一段時間,幾乎家家缺燈泡,一到晚上家裡黑乎乎的。偶爾來了幾張電燈票不夠分,就抓鬮兒。誰家有特殊困難,大家都會謙讓。 那是發自內心的一種習慣行為。我是經常丟鑰匙,鄰居哥哥姐姐都會幫忙找,感覺就是應該這樣的。
鄰居李嬸,男人死了,自己帶著三個孩子。單位照顧給她安排了一份雜工(那時候很多女人是不工作的),到月底經常要借點錢才能過去。我父母屬於高工資,她也會找我媽媽借錢,老鄰居,錢也不多,有時我媽媽就不要了,但她不管多少一定要還,李嬸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好借好還,再借不難」。她每借一筆錢物,都記在小本子上怕自己忘了。看看現在中國大陸家家都是鐵窗鐵門,吃喝嫖賭坑蒙拐騙,明搶暗騙,這短短的幾十年,人的道德變化太大了。
隨著文化大革命深入進行, 「文攻武衛」 開始。大批判,大辯論,大字報。我們附近有一個當老師的,鄰居陳大娘上中學的兒子立刻響應號召,在那老師家門上貼了一張大字報,陳大娘聽說後馬上端上一盆清水和抹布,把那老師家的門擦得乾乾淨淨,然後再去道歉。 晚上經常聽到大人教育孩子的聲音, 但社會的力量太大了。
我的「後爸爸」
我上小學了,學校沒老師,老師都在外地集中學習改造;課停了,校園裡空空蕩蕩。
我們剛入學的新生都有工宣隊、農宣隊和幾個高年級的小學生代管(叫小老師),天天學毛語錄,憶苦思甜,開批鬥會,體罰學生等。
我是脖子上掛鑰匙的(白天家中大人都上班不在家),中午放學後自己拿飯票去機關食堂吃飯。 每天中午吃飯時,都會看到排著隊進食堂的一群人,他們先向毛XX像鞠躬請罪,還要說好多好多請罪的話,才能排隊去買飯。不過,輪到他們的時候,也就是些剩飯菜了。我聽說他們都是右派分子、是壞人,我覺得這與我沒關係。
有一天小老師在班上對我說, 你回家問問你家長,你祖輩是怎樣剝削壓榨窮人的。從那天起,我就知道我也屬於這「一小撮」,我一下就從旁觀者變成黑五類崽子。經小老師這一點撥,中午去食堂吃飯的路上,就會有調皮的孩子要打我,嚇得我繞道走,有時候都不敢去吃飯。我生性懦弱,特別自卑。
好不容易盼到老師們都改造回來了。我第一任班主任焦老師,她經常在課堂上鼓勵學生揭發父母。我知道她先生也是右派。那時講 「親不親階級分」,要和剝削階級家庭劃清界限。為了得到老師的表揚,有一段我產生了惡念,想編個故事揭發我爸爸。當然我並沒有那樣做,如果我真做了,那我必定是家破人亡。
來到海外後,我爸爸讓我看一篇報導,講述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一個男孩子由於觀點不同揭發她的母親,導致他當教師的母親第二天就被活活打死。文章講述了他如何走過自責、悔恨、淒涼的一生。我聽了我爸爸的介紹我沒敢看,我知道那是什麼。
毛XX講:「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一天半夜醒來,聽到我父母在商量離婚。我媽媽說:「不能讓孩子一生受牽連,孩子歸我。」我聽明白後大哭,我媽媽忙說:「我和你爸爸在說著玩呢。」
不久我父母就帶著我去派出所給我改名換姓, 我從此姓朱。
因為我媽媽的大伯抽大煙敗光了家產,我姥爺只能是給大財主家扛長工,我媽媽家也因禍得福得了貧雇農成分。那個年代講血統論,「龍生龍,風生風,老鼠生來會挖洞」。剛剛生下的小嬰兒就註定了你的階級屬性,這叫「階級烙印」。
我改名換姓,搬了家,換了新學校。我參加了學校籃球隊,還被選上了軍鼓隊,好像要開啟新的人生。一天我們班轉來一個男同學,認識我。他知道我姓朱以後,就在同學中說我父母離婚了,我的後爸爸姓朱等,馬上同學們都傳播我的新歷史。那個年代離婚是件很丟人的事,從此我又成了有後爸爸的可憐娃。
責任編輯:文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