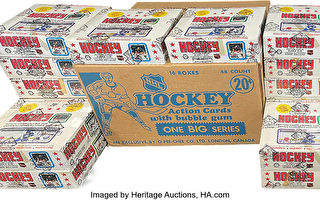【大纪元2023年12月31日讯】文革期间,在学校里天天讲家庭成分,地富反坏右出身的孩子受排挤。贫下中农出身的孩子也不代表安全。那时候发生的很多事情在今天看来真的是啼笑皆非。
比如,写作文中误把“将来”写成“蒋来”,要上纲上线,“你是盼着蒋介石反攻大陆吗?”那可又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了”,人人都有可能成为“一小撮”。区别在于“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管怎样,一旦变成“一小撮”,那就成了仇恨和批判的对象。我们天天唱的样板戏就是:“咬住仇,咬住恨,仇恨入心要发芽”(《红灯记歌词》)。
我们小学校有个音乐老师,偷渡香港被抓,被判无期徒刑。一次拉回学校批斗,我尊敬的一位陶老师,她在批斗会上表现得慷慨激昂,刻骨的仇恨,我那时候也就是约10岁的孩子,感到很奇怪,我知道她家成分也不好,儿子在下乡因此被歧视。她怎么会那么恨哪!长大明白了,她本身成分不好,为了自保,为了划清界限,表现得矫枉过正。
在社会上和学校里都经常有批斗会,从批斗小孩到批斗大人,从批斗身边人到批斗当权派,特别是批判古人孔子、孔圣人,那时称作“孔老二”,砸烂孔家店,到处能看到孔老二歪鼻子斜眼睛的画像。
文革期间戴高帽游街的特别多,一听到敲锣打鼓就知道游街来了,我们小孩儿都跑去看,经常有万人批斗大会。枪毙人、跳井、上吊自杀的,我们也都跑去看。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就是看跳井的,那是在夏天,那个人躺在井边地上,身上盖着一个破席子,只有双脚小腿和头上部分可以看到,头和腿脚都胀得很大很大,紫黑色的,头黑亮,有几个大苍蝇围着嗡嗡飞,记得是没头发,据说是个女的,晒了几天也没人收尸。那年代,听说有时家人怕牵连不敢收尸或不让收尸的。唉,多少冤魂。
我家的新邻居,有对当老师的夫妇被批斗后双双上吊自杀,留下三个很小的孩子;另一邻居约同事在家打桥牌,用英文出牌被告发,定罪是“里通外国的反革命小组”;还有被插上“亡命牌”的,游街示众后拉到刑场陪枪毙,枪声一响,他看到别人都倒下了,他没倒下,接着后面绳子一紧,他又被拽了回来。羞辱人格,林林种种,花样翻新。
那时我妈妈经常给我讲,他们曾经的同事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生活上的艰难,精神上的羞辱,孩子的悲惨遭遇,怕我因不懂世事招惹祸端。
那个年代悲剧多是身边人,我父亲一个大学同学孙叔叔,我们住的也不远。他在大学期间是中共地下党小组成员,反右时相信了中共谎言“向党交心,帮助党进步” 等鬼话,最后被“引蛇出洞”打成右派(我爸爸大学同学很多都是右派),拉架子车二十多年,每月给一点点生活费,一生的青春才华在羞辱中耗尽。
我从小就被教育“言多必失,不要写日记,不要画画,不要留下任何文字的东西”。对敏感问题更是噤若寒蝉,我从小就懂得“惹不起,躲得起”,要“夹着尾巴做人”。
来到海外我真正体会到言论自由就像空气一样珍贵!什么人权啊,生存权啊,在国内从没听说过。我父亲晚年经常说:“共产党的政策就是口袋政策,先骗你进去,等你进去了,口一扎,想怎么整治你就怎么整治你。”让人活得没有一点点尊严,这就是诛心的效果吧。
责任编辑: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