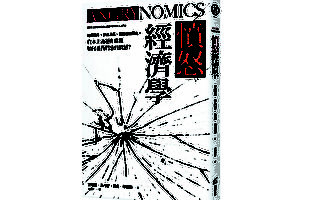【大纪元2023年11月17日讯】
背景说明
本文系蒋硕杰院士去世六周年纪念文,发表于1999年10月。
[写在文前]
一个凡人连自己都难了解了,何况要去了解别人!不过,在瞎子摸象的过程中,若能“听其言,看其文,观其行”,应较能捕捉到其人更近真实的一面,尤其对于一位单纯、无心机且言行如一的“真正知识份子”而言,更是如此。由此角度切入,个人对于蒋硕杰先生“道一以贯之”精神、思想观念的理解,恐怕就具有一些比较利益。就这篇〈蒋硕杰先生经济理念的现实印证与启示—观念力量的诠释〉引言文来说,就是我近十四年对蒋先生所抱持理念的观察、了解之总结。它是由个人在1989年2月所发表的〈其道一以贯之的蒋硕杰教授〉一文扩充而来,当时蒋先生还在人世,他对于这样的称呼也没有表示过异议呢!因而说蒋先生始终如一抱持自由经济理念,应该是不容置疑的。而与蒋先生相知甚深的邢慕寰院士,也对这种说法表示肯定(邢先生于1999年8月27日来函作此表示,两个月后的10月30日即病逝,其来函见附录)。
记得1980年底个人初进中华经济研究院,几乎一开始就接触到蒋先生的文章,除了能先拜读蒋先生送给决策者的建言及发表于媒体的作品外,并将蒋先生的多篇以英文撰写的关于政策性长文译成中文,而且多篇还摘要发表于报端。就这样经过多年的熏陶,个人的“自由经济”思想、理念也从而奠定。对于蒋先生在此期间的各种言论及其行为,也当然近水楼台,相信比大多数国人更为清楚,而对蒋先生终身不渝坚持简单、自由经济原理的观察也应八九不离十。准此,加上个人几年来对自由经济理念的体悟,不免对于黄春兴教授等认为蒋先生有过重大思想转折,实在不敢苟同。黄教授引经据典乍看很有道理,但进一步思考后就会发现他们所说的蒋先生这些思想转折应属手段层次,亦即虽抱持坚定自由经济思想本质,但迫于现实,只能折衷采用渐进方式来实现理念。至于叶日崧所说的蒋先生接受中经院院长、董事长之职,就是受政府供养,就不是抱持自由经济理念者,实在让人不知所云。
综观蒋先生一生,不但对凯因斯有充满野狐禅的比喻,对其有效需求理论、重消费轻储蓄,更是大不以为然,这其实也是基本理念的最大分野。蒋先生回归古典经济学者重视长期成长,藉由市场机能的自由运作,使各项资源使用效率发挥到极致的简单原理,也很自然呈现。其中,要市场机能灵活运作、交易顺利进行,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功能就应坚持,在实际人生里这应是最关键所在。蒋先生站在政府已然控制货币的现实上,尽全力维护流量、狭义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就是力求人类避免受货币这个精灵的役使,但独木难撑巨厦,人类终究还是陷于货币干扰危机的泥淖里,而通货膨胀、泡沫经济这些五鬼搬运、金蝉脱壳现象的孪生兄弟、姊妹,还是三不五时,且愈来愈频繁地发生。这也让我们不得不严肃反省经济学的演化到底是进步或退步,而经济学人所扮演的角色是否不恰当。分析至此,蒋先生的老师海耶克,也才进到蒋先生的世界,因为海耶克的诺贝尔奖受奖词就显现对此事大表忧心的文句,而海耶克本人也对货币始终有着最基本、最深入的研析。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市场经济的顺利进行,众多参与交易的个人需具起码基本伦理道德,至于做人的基本“信用”原则必须要有,否则交易成本就会提高,而人类将货币“误用”,其实已可解释成对信用的破坏,同时对市场里自然长成的秩序也无法遵循,演变成“人造”规矩愈来愈多。不过,这些面向的分析都没出现在蒋先生的文章里,或许在蒋先生的心中,将所有的人都同等视为纯真者,因为他自身就是如此本质的从一而终啊!此外,有关一般人普遍误解的自由经济世界里不需政府,由而排斥政府这个组织一事,实在是极端误解、且有栽赃之嫌。实际上,自由经济的世界,很自然地演化并出现政府这个组织,而且是亟需政府担当“做对事”、“将对的事做好”之角色,但遗憾的是,当前世界呈现的却非如此,严重地说,已明显出现政府该做的事不做或做得极差,不该做的诸种干预、管理情事却做得起劲、过火,实在应做根本性思索、检讨。
附录:邢慕寰院士1999年8月27日来函全文如下:
惠林吾兄:
许久不见,惟时在报纸读到宏论,备见亲切,亦足以快慰耳。我年老多病,所有活动概不参加,本年蒋先生逝世六周年,原应略有表示,其奈力不从心,尚请见谅。所示大文,十分得体,实为精辟之作,可喜可贺。其中提到我所译凯因斯名言,或可自拙著《通俗经济讲话》找到,但我希望此段文字具有“中立”之意义。大作15页“搏”字,似应改为“博”字。
至于黄春兴与干学平两教授最大贡献,似在分析蒋先生政策观念之阶段性演进,我自问受其影响较少,尤其在一九五四年发表〈经济较量与经济政策〉后(蒋先生曾谬加奖饰,见陈慈玉、莫寄屏:《蒋硕杰先生访问记录》)。至于“五院士建言”,只有过来人才能了解,恕不能回答。
第五页:邢慕寰认为“蒋硕杰所没有说的还有可使生产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因而使战时物资供应较为充裕”,明眼人当可看出“战时”实为“战后”之误植,实际上,正与吴文所述“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产业遭盟军摧毁殆尽”,另加许多原因,“战后”亟宜使生产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以充裕物资供应。以上数点,尚请与黄、干二位教授沟通,至以为感。
邢慕寰 八月二十七日
*未在邢先生生前征求同意批露此函,邢先生地下有知,盼能谅解。
一、楔子
1993年10月23日离开尘世的蒋硕杰院士,迄今(1999年9月)已近六个年头,六年虽已使一个新生命达到入学年龄,但在凡人一生岁月中,却并不长。不过,在瞬息万变的当前,在这六年中,年轻一代多已不识蒋先生这个人[1],但“五鬼搬运”这个词却是现时媒体、舆论流行用语,而“自由经济、尊重市场”也是各界人士无时或忘、常挂在嘴上的名词。在台湾,这些名词和主张,就是蒋硕杰提出、播种并奠定的。蒋先生“形体虽已远去,但精神和主张却长在”,可说应是很适当的比喻。
在这短暂六年中,无疑地,亚洲金融风暴是最重要事件,其冲击甚至被认为与1930年代世界经济大恐慌相当。尽管该事件在肆虐世人两年多之后已逐渐平息,然其源起虽被多方探索,而“投资过度、生产过剩”、“债务过多”、“金融乱象”等等都被提出,但“本质”或“最终根源”为何却被严重忽视。我们甚至感受到“反自由化”声音的提高分贝,而歌颂政府管制的言论也所在都有,尤其中共压制人民币币值及严格外汇管制在此次风暴中似乎受到肯定。特别是,在风暴威力正发挥时,呼唤凯因斯,希望凯因斯还魂、再生且一度甚嚣尘上,这样子的情势是否正是本末倒置?虽然可能永远得不到共认的答案,但我们却可经由一生反对、批判凯因斯的蒋硕杰,由其所抱持、终其一生始终如一的理念之回顾以及对应事实当中获得启示,并可寻获明确答案呢!
二、入世的学者、济世的学问
“经济学是什么?”虽被认为是不得体的笨问法[2],但其实已是非常世俗且常用的问法,一般人也都知道问的到底是什么。在俗世里,经济学被认为相对地艰难,尤其充满抽象、难懂的数理表现方式,于是“与世隔绝”、“象牙塔之学”也时有所闻。就是在经济专业领域里,学者应将心力用在学术研究上,或应该走出学术殿堂来关心实务,将理论用于实际生活,也一直争论不休。在蒋硕杰的眼里,毋宁较认同后者,这在他1976年所撰〈刘大中、戢亚昭伉俪逝世周年之追忆〉一文中已清楚表明,而在他1983年为《中央日报》纪念发行两万号而出版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一书所写的序言又更充分显示,而由〈经济学为人类智慧结晶〉题目即可见端倪。蒋先生强调“经济学实在是关系国计民生极其重要的一门科学”,他举出两个实施错误经济政策致生民涂炭的实例:一为共党中国实施马列史毛经济政策,致三十余年的经济一无成就,人民一穷二白。二为拉丁美洲自由世界诸国,尽管地广人稀、物产丰富,因采取错误经济政策,致人民穷困、成长停滞,唯有物价腾涨不已。
共产体制的计划或统制经济之错误实不必多言,举苏联七十年的经验已可供作明显例子,而在1980年代共产世界骨牌式倒台并不约而同走上自由经济之路,其实已足可说明一切[3]。倒是表面上实施私产的自由世界,到底实施什么错误的政策致民穷国困呢?蒋先生在1983年4月于墨西哥首都参加“世界经济成长问题研讨会”,所发表的〈台湾经济发展的启示〉论文中已明白地指出“当时流行的凯因斯学派开发成长学说所导引的政策”,就是错误的政策,至于此政策为何错误,蒋先生如何破解它并说服1950年代后期台湾决策者放弃而采行自由化政策,留待下文详谈。就是有感于由经济学理导引而出的经济政策之影响重大,蒋先生乃对我国青年之优秀者愿意学习经济学的人并不踊跃,以及当时社会风气弥漫着“天分差的才去学经济”感到啼笑皆非,也认为此乃我国好的经济学家远比其他科学家要少得多之因[4]。或许就因为如此,去修习经济学的学子也比较不会慎思明辨,在凯因斯理论当道、教科书及教师大皆凯因斯学派学者的大环境下,脑子里也就根深柢固地装满了凯因斯理论。由凯因斯理论风靡全球的事实观之,或许各国都有同样状况吧!亦即天分较差者才去念经济学。
蒋先生还为此现象曾特地向国内大学执教的朋友请教原因,得到最重要的原因是:学经济学的人无论在国内或国外,就业的机会都比较少,所以乖巧一点的学生都改学工商管理、会计、或电算机程式等就业较易之科目。蒋先生觉得这是“很可伤心”的事,因为一国青年只图一己啖饭温饱之便利,而放弃关系国计民生之大学问的探讨,岂不可叹!有意思的是,蒋先生虽认为此风可叹,但却觉得未必真可惜,因为为谋生而放弃研究学问兴趣的青年,未必是真有天才、能成大器的人物。不过,他为那些真有才能,且很有抱负,但自幼即受传统“聪明的青年应该去学理工”的“熏陶”,因而根本瞧不起经济学,以为经济学不足供他们施展其才能,终而抛弃经济学之青年深感惋惜,也为每年在大学联考中成绩优秀者从来不选读经济学的情况甚感不幸[5]。总之,蒋先生认为经济学是一门非常入世的学问,由其形成的政策影响国计民生,若不幸实施错误政策,恐非“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就能形容的了,因而他期盼一流人才进此领域研读。个人在此忍不住再引申:真正的一流人才应不只会好好研读一门学问,更重要的应还能发现并摒除错误,尤其需具道德勇气与良心,否则恐怕会滥用其聪明才智,甚至于故意利用错误理论所得到的政策来满足私利,但却种下戕害长期的整体生活环境恶果呢!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联想,乃有感于蒋先生在1981年“蒋王(作荣)论战”之际,在当年6月20日于《中国时报》发表的那篇〈货币理论与金融改革〉文章中,以“最后的几句忠言”为标题之结语。这段话的全文是这样的:“王教授颇以文笔之雄肆驰名于当代台湾。听说已故的梁寒操先生曾经在报上读了王教授的大作,大为激赏。立刻自动挥毫写了一幅对联奉送王教授,其中有‘辣手著文章’之类的赞语。我对于王教授的文章也同样的钦佩,但是我不能不提出一句忠告:就是经济学的文章,和其他科学性的文章一样,不是光凭一双手,不管它是‘辣手’也好‘妙手’也好,可以一挥而就的。它也需要用用脑筋将理论与事实搞清楚之后才可以动笔的。在一个销售上百万份的报纸上发表一篇政策性的文章,是要对全国国民与历史有所交代的。
大约两千年前汉朝有一儒生贾让,他的文笔之佳妙至少不亚于王教授。他曾写了一篇〈治河议〉,就文笔而论确是一篇值得传诵至今的好文章。我自己在中学念书时也曾诵读过。可惜他对于水利学及黄河的水文资料都没有研究清楚。因此他所建议的所谓上策,即‘不与河争尺寸之地’,将现有的河堤决开,让黄河舒舒畅畅、从从容容的流入海去的策略,是不可行而有害的。他的文章愈写得动听,流传得愈广愈久,危害也愈大。我希望我们为报纸写文章的人都能各自警惕,不要作当代的贾让才好。”
这段话不可谓不重,但也传神地凸显出蒋先生率直的一面,正如知他甚深的邢慕寰院士所言:“凡是了解蒋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的使命感很高,责任心很重。因此他谈起问题来,总是一板一眼,对任何人都不假以词色。在他看来,朋友归朋友,道理归道理,分得清清楚楚。我亲自看见他在赋税改革会议上对好友刘大中先生严词批评赋革的一些缺失,也亲自看见他当着前行政院长蒋经国先生的面批评政府采行‘指令式’的经济政策。”[6]
因此,蒋先生会讲这样的重话,一定是意识到事态之严重,不得不如此,当然,这些话不是只适用于某一个人,连蒋先生本人都同样适用,尤其影响力大的公众人物更应以之深自警惕,相信蒋先生也有这样的体认。那么,蒋先生敢如此明说,乃对自己的主张有十足的把握和信心,相对地,也深深忧虑错误政策一旦被决策者采用,所将引发的灾难之大、对人民福祉之伤害将很深,可说语重心长。那么,蒋先生为何对自己的主张如此有信心,而对王作荣先生的观点担心到这么深的程度呢?他一定有过刻骨铭心的亲身体验吧?!果不其然,事情得回到1950年代。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
[1] 1999年5月15日在逢甲大学“1999经济思想史与方法论研讨会”,清华大学经济学系黄春兴教授感慨地说,当今年轻学子已不知蒋先生其人,言下不胜唏嘘。而据辅大戴台馨教授表示,其在经济思想史课程中则对大学部高年级生推介蒋先生著作,委实难得,但应属特例吧?!
[2] 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J. M. Buchanan)转述范纳(J. Viner)曾说“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家们做的事务”,奈特(F. Knight)又开玩笑地加上“经济学家们是那些以经济学为业者”,以凸显出此问法不妥当,若改以“经济学是什么知识?”或“经济学者的种种论述,想回答或回答了什么性质的问题?”较正经和得体,请见吴惠林、谢宗林(1997,页5)。
[3] 关于苏联计划经济,1950年代曾有无数的书和论战文章,由于其经济成长曾有一段高档时期,而且科技也极尖端,因而曾被高度肯定,连萨缪尔逊(P. A. Samuelson,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其畅销全球的《经济学》教本,前几版也歌颂过呢!有关苏联经济成长的讨论,较新的著作可参见克鲁曼(P. Krugman)《全球经济预言:克鲁曼观点》(1999,第十一章,页199 – 224)。
[4] 蒋先生以他自己为例,其年青时就时常受到长辈或学长们的“夸奖”说:“你的天资还不坏,为什么不学理工?去学经济学做什么?”而1940、50年代台湾的财经首长也大都是学理工的人,绝少有学经济的。
[5] 十多年来这种现象在台湾社会似乎不但未曾改变,还更恶化呢!其中的道理颇值得深究。
[6]此段话引自邢慕寰〈解读蒋硕杰先生打给我的最后一通电话—纪念蒋先生逝世二周年〉一文,载于《蒋硕杰先生悼念录》,蒋硕杰先生文集(5),页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