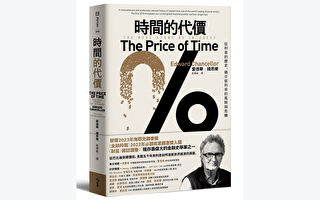【大紀元5月21日訊】在漢語世界,人們一提到英國思想家以賽亞·伯林,首先就會想起他對自由的兩種劃分: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積極自由指的是一個人有權決定他做什麼的自由,消極自由指的是一個人擁有不受他人強制的自由;積極自由是「做……的自由」,消極自由是「免於……的自由」;積極自由涉及的是能力,消極自由涉及的是機會;積極自由自以為掌握了事物的規律,不免會強迫他人跟著自己走,從而滑向暴政和獨裁,消極自由由於懷疑世界有沒有規律,即使有人類能不能認識,得其反倒更少被濫用和歪曲。因而,伯林贊成消極自由,反對積極自由。
如果我們把伯林的這種說法運用到實踐自由的手段——寫作——中去觀察的話,我發現,寫作作為人類捍衛自由的基本手段之一,同樣也可劃分為「積極寫作」和「消極寫作」兩類。積極寫作就是開拓人類文明新局面的寫作,消極寫作就是擺脫他人精神奴役的寫作;積極寫作是要發現歷史的規律,從而改造人類的靈魂,消極寫作只是指出時代的弊病,以期引起療救的注意;積極寫作是探求真理,消極寫作是拒絕謊言;積極寫作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消極寫作只從現實出發,對當下負責,運用良知的力量記錄時代的心聲;積極寫作由於自恃真理在握,代聖人立言,有時倒淪為打擊異己、奴役他人的工具,消極寫作只是有感而發,我手寫我心,捍衛一個獨立的人在生活中的真實目標,反倒會尊重每個人的意願和權利。哈耶克在論述一代人的理想主義迷誤時,曾痛心地說:「在我們竭盡全力自覺地根據一些崇高的理想締造我們的未來時,我們卻在實際上不知不覺地創造出與我們一直為之奮鬥的東西截然相反的結果,人們還想像得出比這更大的悲劇嗎?」二十世紀大半個地球的悲慘經驗告訴人們,比起那些宏大的理論、浮誇的主義、遙不可及的黃金世界,數以萬計的具體的個人,他們的安全、溫飽,他們的自由、幸福,才是真正重要的。試圖在地球上建造天堂的東西,最終卻把人們帶到了地獄;反過來說,把人們帶到地獄裡的東西,恰好是當初人們希望它走向天堂。
「大地總是屬於活著的一代人」,這是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斐遜在給麥迪遜的一封信裡提出的著名思想。這個思想當初只是針對土地和財產權的,但百年以降,當豐饒的大地被形形色色的野心家、暴君和邪教領袖肆意踐踏和預支時,我發現這個論斷至少還應當包含下列兩種含義:1,一個人一旦死了,他與生俱來的一切權利——包括發言權——就自然消失,因而,不能以死人壓活人;2,當「大地屬於活著的人類」時,未出生的人就沒有任何自然權利,因而,一個人,不論他多麼偉大,都不能高懸一個誰也沒見過的人類社會標準來制約、壓迫活著的人類。尤其是對每一個經歷過道德理想國覆滅的知識分子、作家、學者來說,放棄傳統的救世濟民、普度眾生計劃,朝著當下的生活無保留地開放,就成了一種合乎邏輯的自然選擇;尤其是在一個謊言四布,靠獨裁和商品的過量刺激來維持的後極權社會裡,一種關心個人的權利和尊嚴更甚於關心抽象未來的「消極寫作」意義就尤為明顯。
二
與前極權社會一樣,後極權社會的政治、軍事、輿論等一切權力仍然牢牢地掌握在一小撮特權利益者手裡,但與他們的前任相比,這些後繼者在發號施令、宣講謊言時明顯顯得底氣不足。在演講、剪綵、會議、報告以及一切由官方控制的媒體中,極權社會賴以存在的意識形態仍然是唯一合法的交流工具,但在權力的底部,在權力到達個人的一切環節上,這個結構都已經漏洞百出。在制度與生活的目標之間,出現了無數的縫隙乃至斷裂:生活以其一貫的本性,朝著多元化、自組織的方向發展,而制度本身受「超穩定」的力量驅使,不會聽命於任何自然生長的有機力量,它將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資源,將生活拉回封閉、僵死、統一的軌道上來。從表面上看,在所有制度與生活——實際上是權力與人——的拉鋸戰中,總是權力獲勝的次數多些,但在幾乎每一場爭霸賽後,我們都能聽到權勢的喘息聲。實際上,一個靠謊言維持的制度之所以還能維持,僅僅在於人們願意相信謊言。從長遠來看,生活本身的真實目標不會屈從於任何非自然的人為力量。因為極權主義「為了它自己存在它要依賴生活,而生活不以任何方式依賴它」(哈維爾《給胡薩克總統的公開信》)。當導源於人性深處的真實能量匯聚成條條大河衝破由恐懼、謊言和偽善組成的系統堤壩時,人們一定會驚奇,一個巨無霸的倒塌怎麼竟和紙房子散架差不多?
真實地生活當然有多種多樣的表達方式,他可能是演員,當官方指定的曲目不符合他的演唱風格時,他寧願到地下歌廳演出;他可能是教師,當教育部門統一印製的教材不符合一般的學術規範時,他就自編教材講授;他可能是農民,當上級指定的候選人被內定為村長時,他還是堅持在選票上寫下了自己認中的人名;甚至他可能是一個屠夫,當稅吏九次向他索取額外的費用時,他都如數奉上,可到第十次,他終於忍無可忍,拿起了殺豬刀;它可能是一次黨小組會上的沉默,一次「走過場」活動中的不鼓掌,也可能只是對自己不滿意的領導一個鄙夷的眼神……總之,在無數捍衛真實的方式中,消極寫作只是其中之一。換句話說,消極寫作者在真實生活的人群中只是那些對文字,對思想,對精神生活天然痴迷的人。他們從不過高估計自己對推動社會文明做出的貢獻,更不想改造什麼人的靈魂。也就是說,他們並沒有立志要和誰過不去,他們寫作只是「有話要說」,正像狼嚎僅僅因為飢餓,鳥鳴僅僅因為求偶一樣。在生活中他們可能是鞋匠,也可能是股市經紀人、啤酒經銷商,只在白晝將盡,夜晚來臨,他單獨面對自己的上帝時,他才是一個獨立的寫作者。也就是說,在消極寫作和其他生活之間,並沒有嚴格的界限,坐在主席台上念文件的和坐在書桌前凝神思考的可能是一個人。但一個人哪怕一天只有十分鐘這樣的時光,他就是一個消極寫作者。
這樣的寫作是什麼時候開始的?當有一天,你——我們假設她是一個國營企業的普通職工——在單位說了一天的假話,陪了一天的小心,回到家裡仍然不得安寧,你還得為第二天的「踴躍發言」準備材料。當稿紙鋪開,或者坐在電腦螢屏前,你突然覺得,在身體底部升騰起一種無以名狀的恥辱,一種從未有過的厭惡和噁心混合著多少日子積累起來的憤怒從無意識深處湧了上來。你坐在那裡不得起來,因為壓在你身上的是自從你出生以來就有的輕蔑、丟臉和缺乏尊敬。那一刻,你覺得自己異常無助,異常醜陋,甚至連厭惡也感到厭惡,噁心也感到噁心。
你覺得自己非要寫點什麼,這一回不為別人,只為自己。做了千年的孫子,這一回你要做一回自個兒的爹。你不知道這力量是從那兒來的,只覺得一些詞句的火花從幾盡生鏽的腦細胞中擦出,思維的碎片飛快地排列粘合,斷了的思緒走馬燈似地認祖歸宗。寫完後,你念了一遍,竟然不相信是自己寫的。有兩滴清淚打在寫字板上,你不知道是為自己高興,還是為自己震驚?高興的是你在自己的身上重新發現了力量,這力量在這一夜之前是恆久地沉睡在你體內最隱蔽的某個區域的,你幾乎從來沒有動用過它;震驚的是,你不知道是誰創造了這股力量,又是誰在冥冥之中掌管著這股力量?這力量在使用之前你為什麼不知道?你把這一夜叫「火之夜」,或者叫「上帝之夜」,「神啟之夜」。
在這兒,這個國營企業的女職工信不信上帝,相信不相信人的尊嚴是上帝在造人時就賦予人類的基本感覺之一,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那樣做了,就說明一個人的尊嚴可以被踐踏,但不可以被磨滅。恆久地忍耐只意味著恆久地記住,立時地反抗也意味著立時地忘卻。一個人每天蛇行匍匐、忍氣吞聲地在生活中扮演著他所不是的角色,不能說明他已忘卻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感覺之一,即尊嚴感;相反,某些外在的羞辱、刺激以更為內在的方式堆放在某個無意識深層的隱秘空間。一旦遇到合適的契機,這些長期堆放的自然情感就會一躍而出,尋找一個與之同質同構的代理形式。消極寫作不過是無數代理形式中的其中之一。
這樣的寫作從一開始並不想和誰過不去,就像這個國營企業的女職工坐在桌前的那一刻,她只想抒發她對生活的真實願望和目標,她的憤怒,她的羞恥不過是以前環繞著她生活的種種侮辱種種壓迫的總爆發。也就是說她並不打算打倒誰或推翻誰。但後極權制度幾乎從她合上筆或關上電腦的那一刻起就把她當成了敵人。因為說到底,人類渴望在尊嚴中生活的目標和後極權制度渴望在謊言中「穩定」的目標是完全不相容的。也就是說,每一個堅持為人的權利和尊嚴而寫作的消極寫作者,之所以帶上「異議色彩」,並不是這些人都有政治熱情或政治野心,而是後極權制度的謊言本性決定了它把每一個生活在真實中的行動都視為侵犯,視為對權力的有意識挑戰。簡單地講,這些消極寫作者並不想當「反對派」。如果說他們的工作和當局有衝突,那是因為這種工作的性質和內在邏輯導致的,不是他們刻意製造的。照我的理解,他們甚至不指望改變現行的權力結構,他們的工作從一開始就是針對人的良知和意識領域的。
換一個說法,這些作家應該叫「獨立寫作者」。獨立寫作者不想為什麼人代言,更不會自動成為某個階級的先鋒隊,他只不過是無數生活在真實的人們中能運用紙筆的人。也許他是引人注目的,但那是寫作,然後發表這種活動必然具有的公共性決定的,並不是寫作這種勞動天然地比油漆匠和賣泡菜的高貴或重要。一個十字路口沒有警察,交通就會陷入混亂;但一個十字路口沒有作家,尤其是獨立作家,大家誰也不會感覺到。正如特務和小偷希望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一樣,一個有使命感的作家總是希望知道的人越多越好,但這僅僅限於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更多的人讀到。因而,我反覆強調,獨立作家不是救世主,也不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他們寫作,僅僅是告訴人們,生活在真實中是可能的。他們並不想解放全人類,只想捍衛一個具體的人活著的,或表達的權利和尊嚴。他們寫作,他們生活,當然也吃飯、性交,和每一個早出晚歸、宵衣旰食的勞動人民一樣,他們希望看病不用排隊,手機單向收費。坐在書桌或電腦前,他們並沒有想這是「為工農兵服務」,倒常希望「工農兵」為自己生產些更便宜的糧食和布。
但與一般以文字討生活的人不同,獨立作家相信個人經驗具有普遍性,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任何時代任何地方的老百姓,只要有機會選擇,都會選擇—— 富足,而不是飢餓;和平,而不是暴力;尊嚴,而不是恥辱;公開審判,而不是秘密警察。相信良知和尊嚴是上帝根植在人性深處的最基本感覺,眾水不能息滅,大火也不能吞沒,若有拿金錢和權力去換良知與尊嚴的,就全被藐視。他們堅定,沉著,甚至有些天真,他們相信一個人的光亮可以照亮周圍的事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因而,寫總比不寫好,說出來總比不說好,像《古拉格群島》的作者所揭櫫的那樣。
三
這樣寫有什麼用?有人會問。我的回答是,沒有什麼用。如果沒有一本揭露謊言的小說,沒有一篇批判歪理邪說的文章,沒有一部戳穿黑暗的歷史紀錄片,當地的工農業生產總值不會受到影響,理髮店照樣開門,西紅柿黃瓜也不會漲價,但正如社會環境是一個巨大的複雜整體一樣,人類的精神生活也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統一場。誰能估計缺少了這樣一本小說,這樣一篇文章,這樣一部紀錄片會對整個社會的精神文化生活發生多大的影響?它將會使一個謊言,一個假象,一個不可告人的陰謀詭計的暴露推遲多少年?這樣的推遲又在多大程度上削弱或窒息了人們瞭解自我,反省自我,調整自我的能力?誰敢肯定地說,即使打壓了這樣一本小說、這樣一篇文章的作者,這樣一部紀錄片的導演,後世總會有人發現曾照亮過他們的「火之夜」?誰能估計這樣一本小說,這樣一篇文章,這樣一部紀錄片的出籠會點燃多少有才華作者的創造性思維?這些被點燃的頭腦又會激勵多少有志於學的讀者頭腦?
因而,消極寫作者的權力不在有形的方面,在有形的方面他甚至比不上樓下一個戴紅箍的老太太。他的權力隱藏在無形的方面,即由良知支撐的社會無意識深層。他的信心建立在這樣一種牢不可破的信念之上:即人是有良知和尊嚴的,而良知和尊嚴是神賜的,不是人賦的,因而,任何人都無權褫奪或出讓另一個人的良知和尊嚴。一個人怎麼能褫奪或出讓不是他自己的東西呢?對手作為一種創造物,也同樣是有良知和尊嚴的,否則,他們怎麼會感到羞恥和憤怒呢?因此,這場不見硝煙的戰爭,最終的勝利不取決於士兵的多少,信徒的眾寡,核彈頭的部署與威力,而是整個社會的覺醒程度。
也許有人會擔心,假如所有人都從事這樣的「消極寫作」,誰來進行那些真正原創的,前瞻性的,富有建設性的「積極寫作」呢?我的即興回答是,這樣的假設不存在。不用說在教育壟斷、新聞出版被嚴加管制的極權社會裡,就是在教育獨立、言論自由到可以燒國旗的社會裡,願意犧牲眼前利益,從事一種後果完全無法把握的寫作的人也是少數。因而,這個命題實際上是一個偽命題,它的荒謬程度等同於,假如人人都是同性戀,那麼,誰來為人類生孩子?尤其是在官方壟斷一切經濟、政治資源,知識分子、文人只有加入官辦的學校、團體、協會才能獲得榮譽和保障的社會裡,想讓所有的人都頂住壓力從事一種拒絕謊言的寫作,不是奢望,就是迫害狂的妄想症。原因很簡單,這樣的寫作不划算。也許他的作品能發表,並換來菲薄的稿酬,但更多的時候,由於他工作的「烏鴉」性質,他必得付出比那些體制豢養的專司「建設」的作家多得多的代價,他必得忍受來自市場和權勢兩方面隨時隨地的歧視與傷害。尤其要命的是,由於消極寫作針對的是社會的意識層面,它對社會的影響是緩慢的,看不見的,因而後果是不可預測的。也就是說,他和對手的較量不是爭一時,而是竟千秋。所以,很難想像一個精於算計的人會投身到這場偉大而前途茫茫的寫作實踐中來。
但這並不意味著社會或政府有權禁止或打壓這部分人的工作。也許任何時代任何社會的老百姓不管是受人哄騙還是出於好逸惡勞、求樂避苦的本性,總是願意接受那些陳陳相因的意見和知識。也就是說,對大多數人來說,思想自由是沒有意義的,自由是閒置的;但這絕不能證明,某些人或社會的公權機關可以依照自己的嗜好替他們決定——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什麼是應該大力宣揚的,什麼是應該限量發行的。因為一個人或機構一旦獲得了這樣的權力,他(它)就有可能通過自己的權力將自己的價值、信念和趣味強加給我們。他(它)就破壞了一種思想、一種理論成長的有機環境。創作自由也絕不意味著每個人都有相同的能力寫點什麼或讀點什麼。言論自由的創立者不相信政府替我們甄別過的信息。
這就是消極寫作的意義:它維護了人的尊嚴,捍衛了少數的權利,把寫作者從謊言矇蔽的泥淖裡解救了出來。權力以為它滴水不漏的計劃可以覆蓋整個社會,精心籌劃的陰謀可以確保萬世無虞,但現在從「人民」當中站出來一個「人」,一個具體的、活生生的、有七情六慾的人,這個人永遠不再像「人民」一樣默不作聲,而是以他自己的全副嗓音、全副人格、全副良知作抵押,向他的父母、他的街坊鄰居、他認識不認識的每一個人大聲呼喊——皇帝沒有穿衣服。
你可以將除你之外的每個人都當成傻瓜,但現在有一個人用一枝筆證明了一個事實:即至少有一個人你沒有矇蔽,這就說明你的計劃仍然不夠周密;你可以動用警察抄沒他的電腦,毀壞他的研究室,甚至可以僱傭秘密警察將他套上黑布套帶到集中營「勞動改造」,但你毀滅不了一個事實:即他蒙受了真理之光,你的棍棒、手銬、黑布套不過是證明自己惱羞成怒而已;你可以竊聽他的電話,封鎖他的網站,干擾他和國外的一切聯繫;你可以在路邊恐嚇他的孩子,在單位挑撥他的老婆離婚,……你可以幹你想幹的一切,包括毀滅他的生命,但你即使把他焚屍揚灰,他仍然比你高貴。因為在生命結束以前,思想之光帶他從黑暗之地走向了光明,以一個人的姿態站到了毀滅他的面前,而毀滅他的即使把他殺了,也什麼都不知道。
因而,從長遠來看,思想者是不可戰勝的。對手雖然擁有全部的殺人武器和宣傳機器,但他面對的不是一個單個的作家,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書生,而是一個靈魂,一座由良知支撐的信仰大廈。老子說,「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傷其手矣」(《道德經》第74章)。意思是說,天道(司殺者)掌管著人的生殺予奪,代天殺人就是代大匠斫木,哪有不遭到報應的?具體到消極寫作,就是由於這種寫作的動力來自人類生活在真實中的天性,因而,毀滅它的人不是向一個作家開戰,而是向人類的尊嚴和良知開戰,向人性開戰,而向人性開戰誰見過有勝利的?
──轉自狄馬博客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