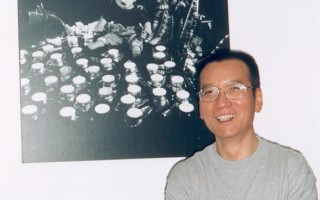【大紀元5月29日訊】
「口腔糖並不消滅形而上學,而就是形而上學。」——『德』霍克海默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的中國,與存在主義熱、弗洛伊德熱同時出現的還有「法蘭克福學派熱」。當時,我也讀過一些法蘭克福學派的書,阿多諾的「否定的辯證法」給我的反傳統以理論的激勵,本雅明的「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是我非常喜歡的文字之一,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以及哈貝馬斯的一些文章,也是我批判中國現實的理論參照之一。
現在,我身陷囹圄,讀《法蘭克福學派史》(原名:《辯證的想像》,馬丁·傑著),除了汲取該學派的批判方法之外,還體驗到某種宗教式的悲憫情懷,故而,閱讀時平添了一層情感上的激動。
有關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合理性的批判,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合理化是對「異化社會」的批判,韋伯社會學的文化意識結構合理化對「工具化理性」的批判,發展為法蘭克福學派的否定理性合理化對「單面人」的批判。法蘭克福學派創始人之一霍克海默指出,批判理論就是「理性」,但此種理性不是西方傳統意義上的一體化的、追求同一性的辯護性理性,而是關注多元化和個體性的批判性理性。在這點上,他們吸收了柏格森、尼采、叔本華、薩特、海德格爾等存在主義的非理性主義。但這種吸收是謹慎的,他們只吸收了存在主義對僵化的理性主義的非理性反叛,而否定其對理性的極端化排斥。因為徹底的非理性主義是無政府主義、進而是極權主義的最佳土壤。法蘭克福學派的理性,是指一種開放的、多元的批判視野,理性的批判是一種相互競爭性的對話,是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是建立在多元對話基礎之上的交叉共識。
同時,這理性是立足於個體生存——個人對有意義的生命價值或幸福的選擇,而不是冷酷的中立化的工具理性。因此,他們一直對韋伯提出的學術中立化立場持懷疑態度。人化的理性首先是一種懷疑的、批判的態度,其次是個體生存品質的標誌,再次是一種價值化的選擇。到美國之後,法蘭克福學派儘管吸收了經驗的、實證的研究方法,但是他們一直沒有放棄德國式的理性主義的思辯方法。這是一批悲天憫人的理想主義者。其智慧的憂鬱代替了尼采的智慧的歡樂。
在法蘭克福學派看來,儘管西方現代國家大都實行憲政民主,但個人自由仍然處在岌岌可危的狀態之中。現代化催生出的極權主義、工具主義和消費主義的相互支持,毒化著人類精神,扼殺著個人自由。所以,為了保衛個體的自由,就要確立一種健全的批判意識,甚至是一種激進的毫不妥協的批判立場。這種立場,有人稱之為「左派」,而在我看來,儘管該學派的思想資源之一是馬克思主義,但他們繼承的僅僅是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而不是歷史決定論和共產主義烏托邦。即便是法蘭克福學派的理想主義,不再具有馬克思式的實踐品格和現實價值,而僅僅具有批判現實的參照價值;他們不是要建立馬克思式的人間天堂(其結果恰恰是人間地獄),而僅僅是為了讓人類在近於絕望之中保持信心。
換言之,理想中的完美之物,不是自我標榜的光環和能夠實現的世俗目標,而是一種純精神的尺度,類似神或天堂,是人類得以保持住自我激勵、自我壓力、自我批判、自我反省的絕對價值和參照系。換言之,上帝的無限是為了凸現人的有限,天堂的完美是為了反襯人世的不完美,理想的光明是為了朗照現實的黑暗。故而,能實現的僅僅是生活目標而不是理想,永遠企盼而永遠無法實現的才是理想。
在我看來,主要由德國猶太知識分子構成的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立場,更根本的動力來自現實的苦難——不僅源於納粹所製造的人類浩劫,而且源於對產生納粹體制的整個現代社會的失望;他們的批判最為關切的是具體的活生生的苦難,旨在確立人的個體性和主體性的。所以,阿多爾諾才說:奧茨維辛之後,寫詩是可恥的。本雅明才說:正因為絕望,希望才給予我們。
這是一種智慧和良知的雙重憂鬱,一種知識或精神貴族式的悲觀主義,一種清教徒式的叛逆,不僅在態度上與現代社會絕決,而且用行動來踐行自己所信奉的叛逆性。
在哲學上,他們批判西方的傳統本體論——形而上學傳統。他們認為此種傳統是現代總體性、一體化的單面人社會和歷史決定論的最深的思想根源。所以,從一開始,他們就像尼采一樣拒絕任何完整的哲學體系,使其哲學批判在一種開放的、對話的方式中展開。他們最不能忍受的是,凡是形而上學哲學家,大都只關心抽像的本體和真理,而對人類的具體苦難卻熟視無睹。那些關注形而上學問題的大哲人大智者,可以終身沉浸於對終極真理的冥想之中,卻不會去理睬一個正在受苦的孩子。而偉大的宗教文學家陀思朵也夫斯基曾在《卡拉瑪佐夫兄弟》中決絕地說:如果用一個真理去換一個孩子的痛苦,那麼我就會斷然地拒絕這真理。我寧可去為解救一個瀕臨毀滅的孩子而獻身,也不會為抽像真理而犧牲。
如果說,在古代西方,關心人類的苦難、罪惡和救贖的主要是宗教情懷,那麼,現當代的一切人文理論或多或少都具有這種宗教的救贖情懷。因為,二十世紀是一個大邪惡造成大苦難的世紀,不僅是法西斯極權和共產極權對人類肉體的集體性滅絕,更是二者的輿論壟斷對人類精神的扼殺。換言之,二十世紀最醒目的標誌,不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世界的崛起,而是無視人的價值和尊嚴的反人性嗜好及其制度的盛行。
法蘭克福學派反對高高在上的哲學——那種只關心真理而不關心苦難的形而上學,反對傳統的思維方式所追求的那種抽像的、一元化的決定論。它把自己的立足點放在具體的存在上,即那些具體歷史情景中的個人身上。世界上從來沒有所謂普遍的抽像的精神和存在,而只有具體的根植於一定歷史之中的多元的具體存在。顯然,他們受到了馬克思的歷史主義的影響,但他們拋棄了馬克思的歷史決定論,而與波普爾的政治哲學息息相通。
偉大的真理需要懷疑和批判,而不是使之偶像化絕對化。任何嚴肅的人文探求,都必須正是人的弱點、人的苦難和塵世黑暗。好的人文理論,無論多麼抽像,也大都是有現實關懷,它不是去尋找並敘述、論證那些不可改變的絕對真理,而是直面人類的苦難和罪惡,為了消除或減輕這苦難這罪惡而指導並催化社會變革。
在阿多爾諾看來,如果不關心一個處在自殺邊緣的人,對奧斯維辛和古拉格的苦難無動於衷,對極權國家肆意踐踏人權的暴行保持沉默,再大的學問也不配談哲學。哲學應該是血肉豐滿的,哲學家應該具有悲憫情懷。抽像的烏托邦式承諾,也許會在人的生命中投下一絲安慰,但在具體的現實生活中卻是謊言。形而上學是一種高智商的謊言,它只在智力遊戲的層次上才真實。它確實是有閒貴族的精神奢侈品,但它決不適於大災難的二十世紀。在這點上,法蘭克福學派拒絕一切先驗的烏托邦承諾,包括馬克思主義的烏托邦。
二戰後,法蘭克福學派一面批判性地反思納粹主義的根源,一面反對任何意義上對個體自由、個體主體性的壓抑和異化,無論是法西斯主義的、斯大林主義的,還是現代資本主義的技術-工具理性的,也無論是囚禁肉體還是毒化精神,統統都是對個體性生存的無動於衷。他們特別批判現代社會的技術化、工具化和消費化,稱之為建立在技術-工具-消費-享樂的一體化上的總體社會,這種總體社會通過把人物化為同質的工具而達到操縱的目的。(續)
──原載《民主中國》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