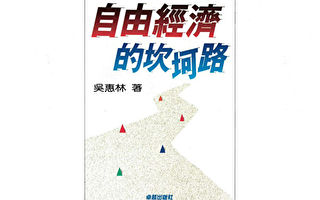【大纪元2024年01月01日讯】1970年代末,共产世界苏联、东欧,及中国等几乎不约而同,掀起改革浪潮,世人也殷切盼望、热烈期待着全球走向经济自由、政治民主之途。经过40多年的演化,人们的期盼是否落实了呢?
表面上看,绝大多数共产国家的确已同时实现“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只有北韩和古巴还死抱着共产体制不放。而中国和越南、尤其中国,虽曾大幅度开放了经济自由,但政治民主和自由却仍原地踏步,甚至不进反退。
经济自由、政治自由难两全
尽管“体制变革”并不顺遂,但在运输和通信、网际网路高科技的带动下,“全球化”形成了沛然莫之能御的潮流。而地球暖化、气候异常、成长极限来临、人类社会沈沦,乃至濒临灭绝边缘的言论和症兆,充斥人间;“人心回升”、“俭朴生活”、“返本归真”等等的呼声也此起彼落。在盈庭的检讨声中,也不乏对于中共坚守共产独裁权力、“民主中国”无法实现,以及自由经济只以“半吊子”面目实现的讨论。
其中,经济自由、政治民主较多获正面看待,但也有视为“祸害因素”的说法,2008年下半年引爆的全球金融海啸,及其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大衰退,就是典例。主因之一是“自由”的基本观念在今日还是混沌不清,甚至被误导、污蔑、指鹿为马。所谓“人者心之器”,而“心”又被“观念”带动,因而寻回正确的自由观念更加显得重要。
这种省思对于共产中国的重要性固然不需多言,就是经济和政治都已自由的台湾,也不能轻忽。今天的台湾,继“经济奇迹”之后,历经1996年的总统直接民选,以及2000年“政党轮替”的实现,似乎又创造了“政治奇迹”;而政治奇迹的具体意义,就是“民主政治”和“政治自由”的落实。衡诸现实,进入21世纪的台湾居民,可说已享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在“言论自由”上不只没有禁忌,还因为缺乏必要的民主素养而被滥用,对于“自由的真谛”也在迷茫中,有着非常大的改善空间。
不过,虽然台湾离理想的民主境界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但比起其他地区来,成就还是相当可观。当然,这项成就并不是自然演变而来,而是诸多前辈坚持理想、牺牲奉献,经过一段漫长奋斗时日之后才得到的。在这些令人崇敬的人物中,1995年12月23日逝世的夏道平先生,无疑是顶重要的一位。
事实上,被引以为骄傲的台湾经济奇迹,其基础的奠定必须溯自1950年代末的第一次经济自由化运动。可惜当年的舵手尹仲容先生于1963年逝世后,经济自由化就停顿下来,以致往后台湾经济的发展并不顺遂。后来除了1980年代中期以来推动的“经济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外,较具规模的“经济自由化运动”,应属1995年被称为跨世纪工程的“亚太营运中心”;而其基本精神也就是“自由经济”。不过,这项方向正确的工作,其进程坎坷,甚至被误解为“西进中国”方案。不但立法部门难以配合,连主其事的政府部门,也不能有效推动。究其原因,自由经济理念的缺乏应是关键。此与第一次经济自由化运动之半途而废,如出一辙。
回顾自由经济观念历经六十多年来,依然成效不彰、甚至还倒退,正足以显示“观念”的威力,也显示观念建立、传布之不易。哲人曾说:“拔除一个信念(观念)要比拔除一颗牙齿还要疼痛,况且我们没有知识的麻醉药。”的确如此!而拔除一个观念固然不易,要根植一个观念更不简单,在长期戒严下的台湾,自由经济理念的植根工作本就困难,更何况自由经济导师一直都是凤毛麟角;而夏道平先生正是其中之佼佼者。
自由民主和经济自由理念,两者之间的关系异常密切,但同时兼具两者的思想家却极为罕见,夏道平先生却正是这样的一个“稀有人物”。虽然夏先生名气不算很高,但其学养和风范,确有如和煦的春风,也像涓涓的细水、长期耐心传布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的理念,影响极为深远;在此人类生死存亡的重要时刻,更凸显其光辉和重要。
在金融海啸肆虐,自由经济、自由市场被误解、诬蔑的现时,更让我们深深感念、缅怀夏先生,此时也是重新将夏先生的得道历程,以及他一贯坚持的自由经济、政治民主自由理念与精神,加以阐述、诠释的良机。而夏先生早年在白色恐怖、颠沛流离的年代,不但勇敢秉持自由经济理念痛批时政,却又能免于牢狱之灾的神奇能耐,也一直令人好奇和津津乐道。他究竟如何在平凡中展现伟大,成就其典范呢?他所坚守的理念又具有什么内涵呢?我们就由夏先生的如何走上“自由经济”思路开始谈起。
夏道平如何走向“自由经济的思路”
夏先生在1907年5月诞生于湖北省大冶县保安镇的一个九代同堂大家庭里,是父母的独生子,全镇人口不到一千人,都以开店铺做生意为生。他的家算是一镇的巨富,也是地主阶级,因而请得起家塾老师。在四位老师中,长于词章学、作文讲究谨严的桐城义法的杜星符先生最有启蒙作用,夏先生写的文言文和白话文,其布局、结构、字斟句酌的不苟且草率,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在因缘际会中,夏先生以“同等学力”考进新制学校,之后于1929年考进武汉大学文预料,两年毕业后直升到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一年级时先被一位刚从德国回来的先生教经济学,所教的正是当时德国流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而这位老师同时对三年级学生教授从铁血宰相俾斯麦以来的那套经济政策。因此,夏先生自认在起步念经济学时,被误导到“非”经济学的歧途。
还好的是,夏先生到二、三年级时不但脱离了那位老师,还适时被好几位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回来的教授导正,才免于继续往歧路走。武大毕业后,夏先生留校当助教,本想趁机多读些书、学好外语、准备公费留学考试,奈何两年后抗日战争爆发了。在往后动荡的八年中,武大迁到四川,夏先生也随着到后方,但也同样逃不掉惨遭重大轰炸的命运。在几次死里逃生之后,觉得现代战争没有前后方区别,乃毅然离校到洛阳前线任一文职军官,到抗战后期转回重庆,任职于“国民参政会”。就在国民参政会的这一阶段,才使夏先生走上“自由经济的思路”。
“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央民意机关。夏先生回忆说,当时政府所遴选的参政员,的确是各界、各党派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尤其是学术教育界一向秉持清议的名流,大都在内。在这样一个论政机构中的工作者,只要心灵没有自我封闭,在耳濡目染中,自然会吸收或多或少得以抗拒种种反自由的政治神话之抗生素。夏先生在国民参政会任职的单位叫做“经济建设策进会”,该会的组成人员是几位参政员,经常主持会务的是参政会的副秘书长雷震先生,夏先生当时的职位是会中研究室主任。当时所谓的研究,不过是审阅民间陈情申诉的文件,加以签注拟办意见而已。虽然由于工作业务,得以对当时经济管制流弊增加一些认如,但对经济管制本身之必然为害,夏先生却还没有深一层的理解。
真正使夏先生走向自由经济思路的种因是雷震先生,这位在参政会是夏先生顶头上司的雷先生,就是影响台湾民主化既深且远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创办人。由于雷先生不摆官架子,身为下属的夏先生乃与之成为朋友。战后还都南京,夏先生就在雷震家的餐会中首次会见胡适先生,而胡适和雷震两位先生是《自由中国》的灵魂和骨干。夏先生之所以与《自由中国》自始至终的关系,就是在国民参政会时段结缘的。
《自由中国》时期的夏道平
《自由中国》半月刊是1949年11月在台北市创刊的政论性杂志,共有十一年的寿命(1960年9月被禁)。那段时期的台湾政治气候,被夏先生形容为“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也就是“风雨晦冥期”,既不同于当时中国的雷霆斗、日月昏,也与变天过程中风云诡谲的1980年代的台湾有别。
《自由中国》总共出刊249期,社论共有429篇,其中116篇是出自夏先生之手,其他尚有不少夏先生以本名或笔名写的和译的,以及早期刊出的若干短评。总之,夏先生是《自由中国》的一只健笔,已故的台大张忠栋教授称之为“如椽大笔”。
虽然《自由中国》半月刊当年风靡一时,对社会人心发生重大影响,以至今日仍有人称颂赞扬有加,而夏先生是该刊不可少的人物;但夏先生却相对地被忽视,与殷海光先生比,逊色许多。张忠栋认为原因在于殷先生被取消台大教学的权利,出国遭遇困难,最后又得了癌症,晚年的生活充满了困厄,所以他的言论角色得到特别的彰显。相对地,夏先生性情比较平和,而《自由中国》结束后,夏先生也一直从事教学研究工作,虽有一些横逆,但都平顺度过,因而其当年的政论文章,反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实,夏先生写的文章中曾有惊天动地的影响。
政府不可诱民入罪
夏先生在1989年元月应多位朋友敦促,将其在《自由中国》的文章,依有关史料性的和问题至当时尚未解决的两个标准选择结集,由远流出版公司出版了《我在《自由中国》》一书,张忠栋教授在序言中就作了生动评述。张教授举了几篇夏先生写的社论为例,说明夏先生的文章掷地有声,批评的矛头直指军方、高层官员和官方传播机构。最轰动的一篇是1951年6月1日的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
该文指出有人在土地银行开户,取得银行期票,然后以期票作押,付高利向人借款,等到借贷成交的时候,即由治安机关当场出面破获,告贷方以地下钱庄罪,而金融罪、买卖金钞罪和地下钱庄罪当时罪名极重,都可援用〈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进行军事审判。该文进一步指出此案三个疑点。第一、从破案资料看,在土银开户的人存款不少于一百七十万元,数额不小,似非普通人,然则此人是谁,外界不知道。第二、治安机关起诉书始终只有贷方姓名,而无借方姓名。第三、借方以一百余万元存于银行,取每月四、五分利息,再用银行期票去质借,付高达一角二至二角六的高利,这种傻瓜行为,实不可解。由于这三点疑问,夏先生在该文里认定整个案件必非寻常,而是政府机关或政府人员为谋破案奖金,事先设计的诱民入罪案件,对于政府威信将会造成重大的伤害。
该篇社论触怒了当时执行金融管制的军方。但军方保安司令部督察处长陈仙洲发表的谈话,却不直接答复社论中所提出的疑点,而只把非法金融活动和匪谍活动扯在一起,语带威胁地要求新闻界合作,“支持各级官员推行金融经济措施,防范匪谍阻挠政府政策,破坏政府威信,打击人心士气”。由于治安单位的反应强烈,《自由中国》接着又发表一篇社论,表示赞同经济管制,也肯定台湾经济管制的成效,以及主管机关的认真和辛勤,同时声明〈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绝对不是故意侮辱有关机关工作人员的操守。张忠栋教授指出,从事后的各种资料看,整个事件惊动了许多党国要员,其中如吴国桢、陈雪屏、陶希圣和黄少谷,最为愤怒的则是当时权倾一时的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
但是〈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得到胡适先生高度的支持,他认为这篇社论“有事实,有胆气,态度很严肃负责,用证据的方法也很细密,可以说是出版以来数一数二的好文,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所以他“十分佩服,十分高兴”。但是他正在高兴的时候,听到军事机关有压力的传闻,又看到《自由中国》的新社论,感觉言论自由已经受到很大的伤害,因此他连写两封信给雷震。他的第一封信说:“《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胡适说他要辞去《自由中国》发行人的头衔,一来表示他百分之一百赞成〈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二来表示他对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他的第二封信说:“自由中国不可没有自由,不可没有言论自由。总统和行政院长在这个国难期间,更应该切实鼓励言论自由,使人民的苦痛、政府的毛病,都有上下周知的可能。此是大事,我的辞职的事是小事。我要先弄明白一点:究竟你们在台北办《自由中国》有没有言论自由?你们是否能继续发表像〈政府不可诱民入罪〉一类批评文章?”
〈政府不可诱民入罪〉一篇社论批评到军方,惊动党国大员,激起胡适的义愤,张教授认为它的价值在《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历史上可以永垂不朽。大约四年之后,夏先生又为《自由中国》写了一篇社论,题目是〈从孙元锦之死想到的几个问题〉,性质内容类似〈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结果却大为不同。原来孙元锦是一位从中国播迁来台的毛纺织商人,最初事业甚为顺利,当时向政府缴纳各种税捐即高达三十万元;但是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台北经济组组长李基光以其资金来源可疑,不断对他敲诈,他不堪其苦,又得了肺病,终于厌世自杀。夏先生在那篇社论中报导了这一件事,进而批评政府追究工商界资金来源之不合理,治安机关的职权太滥,治安和税收机关的奖金制度要不得,以及治安人员之滥权谋利实因为合法待遇太低。这篇同样有骨有肉的社论已经印刷厂排字印好,正待装订的时候,竟然被迫抽换,那一期的《自由中国》也延迟了一天才发行。
《自由中国》停刊的主因
1957年8月到58年年初,《自由中国》发表一系列的社论,讨论“今日的问题”,其中也有夏道平先生写的,譬如〈我们的军事〉,譬如〈小地盘,大机构〉。这一系列的社论,终于引起官方传播机构的围剿,指《自由中国》鼓吹“反攻无望论”,主张“两个中国”,“破坏民心士气”,“为朱毛共匪张目”,要“扯垮反共抗俄的政府”,是“从批评政府转向批评宪政”,是“从批评中国国民党转向于侮辱中国国民党,并否定中国国民党”。当时《中央日报》有两篇社论,一篇是〈亡国主义和救国主义〉,一篇是〈中立主义的转变〉,代表围剿的意图,转弯抹角就是要把《自由中国》说成“亡国奴”、“汉奸”、“中立主义者”和“敌人”。针对这些围剿,夏先生也写了两篇社论,一是〈救国主义与亡国主义的对照〉,一是〈一篇血腥气的怪论——“中立主义的转变”〉。其中有一段话说:“《中央日报》讨厌我们的言论,反对我们的言论,但它又不能从理论和事实上硬绷绷地拿出反对的理由来,只是一味地谩骂。它骂人的文章,差不多已经八股化、公式化了。就是:从骂共匪而骂到大陆沦陷前所谓‘民主人士’,有时再骂骂沦陷后的所谓‘靠拢份子’,然后画龙点睛,骂到它所要骂的人。这时,一顶特制的帽子,就顺便给你戴上。这样千篇一律的公式,已成了近来官方报刊骂人文章的特色。这类的文章,有它所特有的逻辑。它可以随便拿出一个不能成立的前提,再把这个前提像以牛头对马嘴一样,硬套在一个定罪式的结论上面”。
国民大会增订临时条款,破坏总统任期的宪法限制,让蒋中正三连任(乃至后来有四任、五任),也是《自由中国》和海内海外舆论当时批评的焦点。夏先生在这个题目上,先后以社论方式发表的文章,包括〈蒋总统不会作错了决定吧?〉,〈好一个舞文弄法的谬论─所谓修改临时条款并不是修改宪法本身〉,〈对政经半月刊事件的观感〉,〈敬向蒋总统作一最后的忠告〉,〈敬告我们的国大代表——团结、法统、政治买卖〉,〈怎样才使国大的纷争平息了的!〉〈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代?〉这些文章的文字不必引述,它们立意的剀切也无庸置疑;然而事实的发展,却是和夏先生的想法相反,和《自由中国》的基本立场相反,为海内海外的众望所不归。张忠栋认为,后来雷震被捕,《自由中国》停刊,早先看去是因为雷震等人筹组反对党,最近的一项资料显示,由于《自由中国》的批评,特别是反对总统三连任的言论,有关方面早已准备下手,反对党的筹组,只是给了他们一个下手的最新借口。
自由经济思路的养成、传布
在《自由中国》的十一年,夏先生不但写了深具影响力的社论,也培养了对自由经济理念终生不渝的情操。当时,夏先生一面撰稿,一面不断地充实自己论政的知识,特别对自由理论的钻研更起劲,那时张佛泉和殷海光两位先生又对夏先生助益良多,他们在自由哲学上时常辩论,虽然个人的自由理念有异,但相互却有重要启发性,都对自由理论的钻研有同样炽烈的热情。
这里,有一件特别值得一提的事,那是在《自由中国》停刊的三年前(1957年的上半年),夏先生的一位同乡詹绍启先生寄给他一本《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US News & World Report)著名英文杂志,那一期正好介绍米塞斯(L. von Mises, 1881-1973)的《反资本主义心境》(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这本书的摘要,就因多读了这篇文章,夏先生才免于跟随殷海光或张佛泉两位先生走上“非理知”自由主义的思路。殷先生所崇拜的是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69)型的“浪漫的自由主义”,张先生所讲的自由是类同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积极性自由主义”。而米塞斯是奥国学派经济学家第三代宗师,他们的自由主义是从市场机能的运作中发现的。
夏先生说,市场机能这个名词,在台湾现已成为财经官员的口头禅,也是传播媒体的常用语。但是,真正透彻懂得市场机能的人,实在太少。它的运作微妙,非写一本厚书无法讲得清楚。不过,扼要地说,它的特征,是在于从个人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而演绎出来的。他们在观察社会现象时,总要落实于一个个的活生生的“人”的互动过程。至于社会、国家、民族,乃至阶级这类集体名词所意涵的概念,不可高于或外于活生生的个人而成为独立的实体。所以在这种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中,真正地是“把人当人”。因而他们反对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处理社会问题。自然科学所处理的是“物”、不是“人”。如用这种方法处理社会问题,就是把“人”物化了。
在译了米塞斯那本著作的内容摘要以后,不久夏先生又译出他那本书的全文。米塞斯用英文写的书有六本,夏先生译出了三本,另两本是《经济学的最后基础》(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和《人的行为》(Human Action)。《人的行为》这本书有八十多万字,是米塞斯理论体系的代表作。
由于译了米塞斯的三本书,激起夏先生更浓厚的兴趣,进而研读海耶克(F. A. Hayek, 1899-1992)的英文著作。于是,他又译出海耶克三本论文集中最精彩的一本《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然后又译了不属奥国学派的德国罕有的自由经济学家洛卜克(W. Röpke, 1900-1968)的《自由社会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the Free Society)。
笃信“理知的”自由主义
翻译了这五本名著以后,夏先生更深切地、更周延地理解理知的自由主义,而笃定了他的自由经济理念。由于这一理念的抱持,夏先生受到两大益处。一是理知的自由主义者研讨社会问题,不是一味地靠经验知识,他们更凭借先验的推理。举例来说,米塞斯在社会主义风靡世界、而苏联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制度受到世人赞赏时,他独树一帜,预言社会主义因扼杀市场机能而终将惨败。海耶克在凯因斯学派声势赫赫的时候,痛斥他们将导致通货膨胀率长期累增而终将陷于假相繁荣中的贫困。米塞斯、海耶克凭先验推理的预言,现在都已实现了。
夏先生所翻译的米塞斯和海耶克的那四本书,都是唯心主义凭先验推理的论著,也都是二十世纪的宠儿─迷信科学万能的知识分子所排斥的。他那时默默地翻译那几本书,却是在做不合时潮而又吃力的冷门工作。但是,他却偏好这种理论体系,而有乐在其中的自我享受,得有精神生活的安适。而且,20世纪末由于米塞斯、海耶克二人的预言实现,夏先生以前埋头做的冷门工作,在今日台湾的学术界已博得相当的肯定,这一“不虞之举”,又给了他意外的安慰。
《自由中国》结束后,殷海光先生也英年早逝,那时与夏先生谈学问的对象是周德伟先生。这位做官而不忘学问的稀有人物,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直接受教于海耶克,夏先生也从此得以接触更多海耶克的著作,于是更加坚定走向海耶克的自由经济理念和体系。
夏先生特别在意的是,海耶克的自由理论体系,多年来被所谓进步分子或美国型的自由分子称为“保守的”。而“保守的”这一标签一经贴上,就成为时髦的言论市场中被尘封的产品,于是在一般顾客的心目中,仅凭这一标签已可想见其品质的陈腐,用不着再去检视了。为了破除探路者可能已被误导的成见,夏先生特别向想了解海耶克体系的人士推介先读海耶克的〈个人主义:真的和假的〉(Individualism: True and False)这篇文章,最好能读原文,如此或可预防他人轻率的误导。
经济学家可区分为三类
夏先生将通常统统被称为经济学家的那群人,就其思想言论的底蕴分为三类,一为真正的经济学家,二为经济工程师,三为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这三类人同样都是使用经济学的一些名词、术语和某些模型,外行人看到他们发表的文章都在谈经济问题,也就很自然的把他们都叫作经济学家。因此,在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当中,有的是鱼目混珠的被捧,有的是背黑锅而被骂,青红皂白不分,褒贬毁誉也就混乱了。所以夏先生特别说出辨识的方法:对于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本身已够明显,不必多加解说,夏先生虽看不起这种人,但也认为若这类人赤裸裸地讲出他们所争取的是什么,也是光明磊落,无可厚非;但他们大都是每每把内心的真正企图伪装在富国利民的宏论中,藉以在舆论界造势。
经济工程师就是把公共经济事务的处理当作一项工程来做,亦即将人“物化”,这些人都是搬弄一些经济学名词,而以工程师的心态、工程师的技巧,来处理活生生的人的行为所形成的公共经济事务。至于真正的经济学家,是在研究活生生的“人的行为”。人是具有争取自由的本性,从事不得已的选择行为,于是演化出分工合作的互动行为,以“无形之手”或“长成的社会程序”来维系互动行为。政府的有形之手,是帮忙无形之手,以法制来协助,使市场运作顺畅,而非干扰或扰乱“长成的社会秩序”。有这样的基本认识,才能走向正确经济学家的思路。
夏先生的这种看法,当然得罪不少人,但终其一生坚持不渝,而此种自由经济理念如今却已绽放出炫人光芒。
在《自由中国》停刊之后,夏先生曾在政治大学、东海大学、辅仁大学、东吴大学、铭传商专等校教学,继续传布自由经济理念。退休之后,因缘际会进到中华经济研究院担任特约研究员。
那是1981年那一场“蒋(硕杰)王(作荣)论战”时候,夏先生深受蒋硕杰先生两篇文章感动,乃写信给蒋先生表示敬佩和支持。蒋先生乃邀夏先生到中经院从事改稿和编辑《经济前瞻》季刊(自1995年1月起改为双月刊)的工作。于是自由经济的种籽乃播到中经院研究员身上,而远流出版公司一系列的《自由主义译丛》,就是此种成果的展现。
自由主义与宗教
1989年,由于年老病痛,夏先生离开中华经济研究院回家静养。为消遣时间,除了读唐宋诗词、写写毛笔字外,其求知欲转向安身立命的宗教文献。如佛教的《金刚经》、《心经》、《六祖坛经》,天主教与基督教共奉的《圣经》─《新约》与《旧约》,以及基督教资深的信徒们所写的导读圣经与解释圣经的书。于是夏先生对佛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异同,有了大概的认知。
夏先生认为,同的方面很多很多,总而言之,都是教人为善,也可简约到一个“爱”字。在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中也富有“爱”的教诲。从异的方面看,佛教似乎没有讲到宇宙万物的创造者这一至高无上的神,而基督教与中国固有传统文化却都有这一观念。基督教的上帝耶和华与中国经史子集中的“天”字都是指的宇宙万物的创造者,而且是唯一无二的。佛教与基督教都是外来的,这两个外来的宗教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中的信仰不同的地方,即前者是有组织的、有教会、有教堂;后者没有组织,因而没有教会和教堂。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中没有宗教,只有儒家、道家、法家等等所谓的“家”。中国人在信仰上所一致敬畏的“天”,并非来自宗教,而是由于“家”的传承。
信奉“基督教”以终
夏先生之信教是由于求知欲要找一个最后归宿,他之选信“基督教”有两个原因:一是上面已讲到的基督教的上帝耶和华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中的“天”,同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这一超逻辑的信仰,毕竟解答了知识面认为不可思议的问题——如何由“无极”的“无”而生所有的“有”?另一个原因,是基督教也解答了另一个受人质疑的问题,即:上帝耶和华既是全能的宇宙万物创造者,而祂也是爱人的,为什么要造些坏人到人世间作恶为害呢?这又是一个不能从知识面理解的问题。但在基督教经文中有了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偷吃禁果的神话(神所讲的话),对这个问题给了解答。夏先生说,当你到了自觉自己的知识追求再也不会有何增益或贡献的时候,你的求知欲就可因相信这个神话而得到安息了。
为了要让求知欲找到最后归宿,就不能停止在中国固有的“家”的传承,必须从外来的三大宗教之间选择一个来信。此所以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夏先生,终于选择了基督教。
1995年12月23日傍晚,这位前半生致力于台湾自由民主、后半生为自由经济散播种籽不遗余力的哲人——夏道平先生安详地离开尘世到他的天国,我们只能在他留下的《我在《自由中国》》、《自由经济的思路》、《自由经济学家的思与言》三本文集中继续探寻并接续其真正知识分子典范。
在这混乱过渡期的台湾,夏先生的“要减缓台湾当今滚雪球般的公共政策,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负起知识的责任,拿出道德勇气,针对那些只求增加个人选票的政客和只求提高个人知名度的舆论界人士,予以无情的痛击,并就持有的知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是个长期的教育性问题,这要靠那些正钻研海耶克纯正的、主观的个人主义的年轻一辈不停的努力了”谆谆告诫,很自然地在我的耳际响起。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