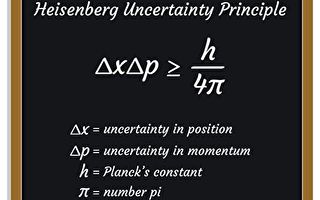(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3月27日讯】温绪伦,农民。
61年生于重庆江津朱扬镇,不在镇上,在村里。生那年,家中吃饭的人就是7个,温绪伦四兄弟、父母、奶奶。爷爷是早逝,得肺癌命归黄土。奶奶也死得快,死的时候温绪伦才两岁,所以只隐约听长辈讲过一些温绪伦被爷爷奶奶吼抬起屁股爬的故事。
温绪伦的脾气后来像他妈,火炮脾气,暴躁凶猛。他跟他爸不像,他爸似乎从不发脾气,有气就喝点闷酒,但也死得快,记得跟杨华芝结婚才23天的时候,他爸就死了,那时温绪伦大概23岁。
六几年的时候,生活太苦,吃的是麦根根、高梁根根,稀饭是罕见的,就是有,也是放在碗里就沉下去,米粒清晰可见,就那么几颗稀哇哇地摆起。
小的时候,温绪伦的爸妈在生产队抢公分做活,10个公分才一角多钱,他们两个一天到晚舍死忘生,才不过4公分一天,所以到年终时,那些搞得快的就一担谷子一担谷子地挑回家,但温家却只有被别人把猪牵走——公分太少,反而拿猪来抵账。
温绪伦读过书,读到小学二年级上半学期。衣服很烂,别的孩子好衣好裤,他的衣服左右肩膀、腋窝、裤腿都是大洞洞,别人看不起,他就干脆不读了。那时大约7岁。
7岁不读就回来捡狗屎,遍山去捡,拿来做肥料,赚公分。但难得干,就放弃了捡狗屎,看见家中没柴烧,就跑到火车站捡煤炭,寒冬腊月跟着铁路一节一节地捡落下来的煤炭,拿回来煮饭。
9岁的时候,胆子大了,想到捡实在太慢,就干脆偷,背个小背兜,在火车上上钻下跳,冒好大的险。反正为了吃饭,偷了煤炭一堆又一堆,堆得自家屋檐全是煤炭。这时,别的小孩也跟着学精灵了,也伙同别的孩子去偷,温绪伦脑筋一转,干脆把那些堆着的煤炭拿来卖,钱卖了,交给家中凑伙食。看见大人抽烟,他也想抽,说抽着好看,他就去捡别人的烟头,躲在墙角抽得直咳嗽,这样一来二去,9岁就把烟学上了。
12岁的时候,温绪伦开始和他爸学做生意,买点米、辣椒、鸡,再卖出去,但不幸被抓,那时的政策不比现在,政府说你是投机倒把你就是投机倒把,温绪伦的爸爸被拉进去关了10多天,教育一顿之后,放出来,做老实人。
13岁的时候,温绪伦胆子大了,干脆一个人做生意,他老爸劝他,他不管,跟他爸吵了一架,他老爸不敢打他,就说你遭抓了不关我的事,温绪伦说,我温绪伦做事,一人做事一人当,怕啥子?他就把自己家中好的红苕拿去卖,烂的红苕自己留着吃,温二、温三、温四三兄弟不比大哥吃苦,看见红苕就不吃,说味道太苦,温绪伦就吼几个兄弟:“你狗日几个晓得个锤子?日你妈屋头没的钱来哇!跟老子吃了!”几个兄弟忍着苦味道就骨碌一声吞下去,没吃几口,就冲出门槛,哇哇哇地呕……
14岁的时候,连温二都还没干活路,只读书,温绪伦为一家人吃饭就跑去生产队跟爸妈一起干,但力气小,人又瘦,做不赢别人,别人就拿他开涮,看不起这小子。越是看不起,温绪伦就越是努力干,看见别人在割谷子,他就在后面捡谷稻根,只要上面还有几颗稻谷就捡起来。手在水里捞,捞得两只手血淋淋的,稻谷插在肉里面,两只手整天都拿布来包起干。捡来的谷子一颗一颗地放起来,交给保管室,一天就有几十斤。
15岁的时候,温绪伦开始正式上斗打谷子了,摇打谷机、担谷子,啥子都干。谷子是一百斤一挑,有时路程远了,挑不起,他就咬紧牙关挑过去,到点时人累得骨头都散了架,背上红压压一片伤痕,想得人都要哭。尽管温绪伦如此卖力,但到年终结账时,别人还是要到自己家中来牵猪走,公分不够,就要补,不牵不得行。
第二年,温绪伦会犁田了,破了命地整。那时的犁田按计件来做,多劳多得,温绪伦挣了一口气,一天犁他十多块田,每个月差不多每天犁。到年终时,温家的谷子才一挑一挑地担,生活有了改善,整整十六年终于过了个“保全年”。
17岁的时候,温绪伦开始到重庆跟别人学手艺,盖房子,泥水匠,修公路,搭电线,样样学,样样钻。这样漂泊浪荡的日子过了两年多。
要满20岁的时候,温绪伦谈媳妇了,谈了个隔河的人,杨华芝。为维持生计,就到他五舅那里学打石头,不想才不过二十天,打石头把自己的脚指拇给打了,只好脚一瘸一拐地回来。刚到家中,就看见家中灵堂肃立,父亲死了。好大一笔花费,家中一穷而白,还债主林立,屋外人整天对他的这个媳妇指指点点,说是这个人有邪,才进门几天就把公公害死了,说不定是哪晚上男人不在,跑去跟公公乱搞,邪气太重,把人给搞死了,温家屋头肯定有鬼,这个鬼就是杨华芝!
就连温绪伦的老师(他五舅)也说,温绪伦啊,你那个媳妇我看有问题,长得妖里妖气,人不死才怪。我这边呢,你就不要再来了,你看你屋头还有恁个多桔子没的人管,你来学我这一行,恐怕不得行,我看你还是不要再给我惹麻烦了,把你老汉安葬好,自己另谋出路。温绪伦说,我现在搞成这个样子,你还说这种话,落井下石嗦?五舅说,你不认我也无所谓,我还稀罕你这个穷亲戚?笑话!
温绪伦伤心地把父亲遗体安葬后,不得不开诚布公地对三个兄弟说:“家里有难,大家只好各自谋生。你们中最大的也有二十一了,最小的也有十七了,都是应该能找到饭吃的年纪了。我们从今天开始分家,以后各走各的前程。”三兄弟不敢反抗,等大哥走后,三兄弟对着大嫂破口大骂:“是你龟儿这个烂女人把我们家搞得家破人亡、四分五裂,我们三个一辈子都不喊你喊嫂子,你龟儿姓杨的算啥子东西?!”
杨华芝忍气吞声过了一年,娃儿刚生下来,三个兄弟就讽刺她:“这娃儿要喊我们喊哥哥才对,看来我爸爸还是整得出娃儿来哦!哈哈哈……”温绪伦回来看娃儿,是个女的,取名为温永会,希望她啥子都会,不要将来找不到吃的。
温绪伦回厂了,不料才不到一个月,收到一封电报:“华芝疯了,速回!”一看发电报的人,是个村里人,不是他的三个兄弟,他顿时火冒三丈。回来还没到家,就对着三个兄弟大发雷霆:“你们嫂子疯了,为啥子不早说?”
“我们还敢说啥子?整天拿起刀,要砍死这个砍死那个的,我们把娃儿跟你抢回来就算好的了,你还发啥子火?”
“病是咋个搞起的呢?”
“还咋个?想多了呗,你不要说在屋头我们三个欺负她哈,你看她现在这个样子,我们还敢动?”
“嘿嘿,你们是啥子名堂我是一清二楚,不要麻我,把我温绪伦当傻瓜看待,你们就大错特错了!”
温绪伦回了家,一看家中搞得硬是不像样子,饭菜米粒到处都是,家中的坛子、罐子、缸子弄得稀里糊涂。到处找人,找不到,后来在一个山洞找到,只见杨华芝披头散发,手里拿着一把菜刀,喝道:“你是哪个?不要过来哈,过来老子就杀死你龟儿!”温绪伦才不管,走过去两脚一踢,把刀一把拿下,几个耳光一闪,就把杨华芝拖回去了,周围的人跑出来看热闹,温绪伦走在人群中间:“看啥子看哇?有啥子好看的?!”
回到家中,急了,身上没几个钱,不敢进大医院。听几个村里的人说请妖婆来就得行,温绪伦不信那套,可也没别的办法,就叫人来干。一个又一个来了,装神弄鬼,七跳八跳,唱唱巫巫,费了500多块钱,没用,反而弄得越来越糟糕,以至于杨华芝后来看见老太婆就骂得震天响。
温绪伦想起老丈人杨定发是个经历过风浪的人,就到朱沱找他,杨定发过来一看,不得了,要杀人,杨华芝举起刀就要砍人。从屋里头逃出来,杨定发抽上一根烟,说:“天命难为,需要感动上天才行。就在九尘崖,有个菩萨,昨晚托梦给我,说他想回家,这个家其实就是四望山,你今天跟我过去拿跎金放到菩萨背心,送到四望山时再给他穿上红布,这样可能有点作用。”
照温绪伦后来的话来说:“我是最不相信那套的,但是人到紧要关头不信也不得行,不想磕的头我磕了,不想拜的神我拜了。”
杨定发所说的九尘崖,到四望山起码有十里路,中间隔条江。温绪伦坐船过来,到了九尘崖,找了个村里人,两个人抬一个菩萨,一抬,天啦,四百多斤绝对有。杨定发说:“做这种事,贵在诚心,你只要心中对他敬畏,那么就轻。”温绪伦先给菩萨磕三个响头,再给他擦干净身子,最后在菩萨背后的洞里放上一块所谓的金,又磕三个响头,开始抬,温绪伦说:“嘿!果然轻了不少!”抬到山望天子那里时,人已经累得满头大汗,又抬,抬到长江边,已经到了下午五点。怕人来抓,说搞神弄鬼,温绪伦说:“赶紧上船!”可哪只船敢装?好不容易碰到个老船夫,温绪伦上前递支烟,说:“不装人,只装菩萨,装到四望山河边,我跟着菩萨走,你到了那里就等我,可不可以?”那人本来不答应,但他也敬神,就说:“没问题!”
杨定发马上叫温绪伦买几圆鞭炮,看见船逆水而行,温绪伦和杨定发手里拿着鞭炮,沿着长江边走,鞭炮对着菩萨放,周围人看奇怪,温绪伦也不紧张。
天色已晚,温绪伦和杨定发走到了四望山,拿出钱给船夫:“辛苦了!辛苦了!”不料船夫说:“运的是菩萨,不是人,我一分钱不收!”就帮忙把菩萨搬下来,开着船走了,真是令人不知说什么才好。
四望山很高,菩萨依然抬上去,抬上去时只有一个割猪草的人看见,其他都没看见,温绪伦不想扰乱菩萨清静,认为菩萨也累了,到了那里要休息,最好不要有外人来。
认真抬上去,到了一个地方,看见个绝好的洞,把菩萨放进去,穿上红衣。不想,正在这时,只听得后面的鞭炮声“呯呯”地响起来了,一传十、十传百,好多人都晓得了消息,都来敬菩萨……
直到现在,那个菩萨还在四望山。
尽管温绪伦诚心诚意地抬菩萨安家,但效果仍然不行,倒是杨华芝开始信神信鬼,一开口就说:“那个菩萨啊,在叫我呢……”
看见媳妇的头发一根一根地掉,人也越来越苍老,人心里焦得没办法,差点自己也快发疯了。这时他打听到某处也是他这种情况,但人居然好了。他去探访,一听,原来在永川城边有个地方叫三教神经病医院,难怪他以前听人骂,都说成是:“你龟儿从三教跑出来的!”
马上去三教。医药费倒不贵,第一回拿药才几十块钱。拿回来吃,嘿,有效果,就又去拿,拿了三回,病就好得差不多了。花钱上主要是往返多,路费钱花得不少。在三教,那是他平生第一回看到原来这社会还有那么多神经病!一个二个三个四个都是些眼睛眩乎乎的家伙,看着都怕!
医治当中,气愤的是有一回,杨华芝趁温绪伦不在家,自己偷偷地翻箱倒柜,把药一大把就吞来吃了,等温绪伦回来时,一找药,药没有了,气得他双脚乱跳。
杨华芝的病一年多才好,此时家中更是穷得揭不开锅。而且自己的女儿也似乎不大正常,一两岁时就静得不得了,一天到晚不哭也不笑,不打也不闹,她就坐在山头上,你跟她说:“永会,你坐着,不要跑哈。”然后你拿两颗米给她,她就紧抓着那两颗米,除非你来叫她她才走,你不来叫她,就是到了天黑她都还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时间转到86年夏天,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温绪伦又到外面打工去了,帮别人抬石头、修铁路。打谷子的时候就上成都去帮别人,一去一回,除了路费,还能剩个三四百块钱。谷子打了两年,这两年里,媳妇能够干庄稼,家里慢慢好转起来,债虽然有,但不是太多,也就一千多吧。
到了91年,温永会要读书了,杨华芝就跟着她娘家的一个亲戚高舞英到永川去学理发,不想才两三天就说不习惯,看不来那些男人喜欢勾勾搭搭的,干脆还是留在家中看娃儿。
此时的温绪伦正在朱扬镇给别人当“棒棒”,又帮别人抬石板。如此慢慢过了几年,温永会的书越读越高,成绩不错,但就是经济压力太大了,每到一学期的开学或预缴之类的,温绪伦就头痛。
98年的时候,温永会已经14岁了。农村里弄不了几个钱,杨华芝考虑到要让娃儿多读点书,就联系在广东东升农场的二哥杨庆华,这样,杨华芝就去了。家中留下温绪伦和温永会,父女生活维系艰难,尤其是这时的温绪伦没有了老婆在身边,赌博成瘾,经常是辛辛苦苦得来的抬板钱两三分钟就输个精光,输了就借,借了要还,常常是第二天的抬板钱刚拿在手中,连温度都还没生起,就被要债的人拿过去了。
温永会在初中最先读住校,家中常常是温绪伦一个人,所以一有空,马上叫些三朋四友来打牌,最惨的时候,拿米来抵钱,六角钱一斤,往往人家一盘“大贰”糊个红牌,就是六磅八磅乃至十多磅,那就意味着:就那么几分钟时间,二三十斤米就归人家了。这样的日子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女儿突然对爸爸说:“爸爸,我要回来吃饭,不想读住校了。”
父亲极为紧张地反问:“你回来干啥子?学校里头住不得咋子嘛?”
“反正我要回来吃,我都跟老师说了。”
其实温永会是想管住爸爸,温绪伦也看出了这当中的利害,决定还是回到正道上来。于是还是到外面帮别人抬板、上货、锯木料、修铁路、打石头,甚至到火车站帮别人擦鞋他也干。早上六点起床,给女儿煮饭,中午十二点又回来煮饭,晚上六点又回来煮饭。赌博之类,再没兴趣。
99年12月22日,出了个特大意外。那天温绪伦如往日一样抬着六百多斤重的石板到四楼上,八个人抬两块板,四个人一组,走在木制的“??”上“哼吭呫…??盘和…??盘吭呫…和吭吭呫…吭着呫”地吼着号子,不料“??”突然“啪”地一声断了,八个人中六个人从四楼上直笔笔地掉下来,另外两个稳得住,没下来,温绪伦当然是掉下去的一个。六个中当场就死了两个:一个被几百斤的板子压在底下,头都破了;另一个在桩子上被钉住,桩子很尖,直穿内脏,痛苦惨叫而死。三个重伤,一个腿断了,一个手断了,另一个后脊椎断裂,脸上一块骨头飞出几米远。温绪伦命大,掉下去,腿被磋掉一块肉,马上滚开,脸吓得铁青。忘了腿上的伤,只呆呆地望着一团团血在面前,神情木然。
在场的人马上把六个人送到永川,温绪伦说:“不要管我,他们要紧!”不料其中一个重伤者,才上车五六分钟就断了气。另一个的死更是离奇,明明到了医院,医生说这个人不医算了,医了也是一个残废,几个人不服,你管他残不残废,医了再说,医生说,需要血,医院里头没的血,现场的人说我们献血,医生说你们的血?还要看是啥子血,要晓得是啥子血,还要搞些时间……就这样一拖再拖,那个人当场闭气,大家都知道这是个才二十三岁的生命。只有一个被医好了,交了两万多的手术费,开了两刀,光是照片都照了400多张,医好后残废一个,永久地失去了双腿。
第二天,温绪伦瘸着腿去问老板:“我这个是不是要解决点钱?”老板瞥了一眼说:“这个嘛,问题不是好大,没的来头。”那个时候,温绪伦也给自己壮胆,不是很怕。但到了晚上就怕了,他想起那个场景,血到处飞,肉到处跑,人死了那么多个,周围都围了那么大一群人,一个二个三个四个都说:“六个人都死了。”好像自己也确实死了一样。从四楼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哗哗哗”落在下面乱七八糟的东西上面,“咚”地一声,自己没死?死了?到底是死了还是没死?再去看那个现场,下面全是砖,血被沙掩盖了,推开沙一看,还有血,甚至还找到一根人肠子!他怕了,整个人站不起来,腿软得没有力气。
那一晚温二、温三、温四都去找温绪伦,四处都找不到人。温绪伦这时就在杨华芝疯的那个山洞里,自己想都不敢想从四楼上掉下来的那个可怕情景,好像自己真的是个死人,整个人精神下降。生产队的人打着火把到处找,他当没听见,自己的娃儿就在远处喊:“爸爸,爸爸!”他也当没听见……
第二天,温绪伦回来了,大家都惊呆了,好像看见一个从坟里头爬出来的人,没人敢接近他。他倒在床上,什么也不敢想。抬板的事情也再也不要去做了。温永会回来也被吓一跳,就像看到一个鬼,叫两声“爸爸”,不答应,又叫两声,突然得到一声厉吼:“狗日叫啥子叫?!”
接着他的那些朋友就来安慰他了,说,哎呀,没的啥子,来,喝酒喝酒。看见一帮兄弟过来闹热,心中稍微平坦一些。
这时,收到一封从广东来的信,杨华芝来的,说就在老丈人那边,有个人叫张二,他就是我们农场的人,说要回家过年,你走他那里一趟,叫他把你带过来,具体路线他晓得,就是在重庆菜园坝坐火车,买到广州的票,火车要经过贵州,34个钟头就到广州,到了广州,就在火车站对面的汽车站上车,坐到番禺钟村的车,注意看车牌号,要写得有“282”的,不然容易被骗,要被拉到一些阴暗处“黑吃黑”,你到钟村下车后,就坐摩托到东升农场,只要四块钱摩托费就够了。
温绪伦不大识字,只好到老丈人那里问张二,一听老丈人说:“他爸爸喜欢喝酒,赶场天都要到馆子喝。”温绪伦这才想起是张华友那个二娃儿,就在新建十一队。马上跑过去,一看,人家在办生,是张华友五十大寿,温绪伦就买一包糖,送了二十块钱。碰到张二,一看,二十一二的小伙子,就拿起一封信,张二一看,认得认得,就说,我们一路就是,小事一桩。来,喝酒喝酒,我们两老表是头回见,多喝几杯哈!
温绪伦回家后,把温永会安排到温二家中,然后收拾东西就跟张二来到了广东东升农场。但一去,不招人。温绪伦在里面住了一晚上就被赶出来,里面规定严,最亲的人也最多只能歇一晚上。没有地方睡,就到一个江津老乡的小茅房里睡了两晚。不好意思打搅久了,就跑到朱沱老乡周四那里去睡。周四当时在跟农场水房,水房就在池塘上,池塘里全是鱼。到了晚上,周四去弄鱼,温绪伦说:“你拿人家的鱼,要遭不?”
“遭啥子遭,这里头鬼得很,一两条鱼算啥子嘛?”
当晚农场总管吴锦通也来喝酒了,吴总管问:“这是哪个?”
周四说:“来农场干的。招他一个得不得行?”
吴锦通扬头一句:“这个嘛……”
温绪伦明白意思,马上摸出五十块钱:“这个,是一点小小的意思,吴总管拿去买几包烟。”
2000年1月1日,温绪伦进去了。先是很一般的“打铲”,就是成天挖土,干了20多天,然后去打药,干了一年多,干了一年多以后,温绪伦被调到从化那边,带着杨华芝一起打药除草,地有80多亩,80多亩地的员工才8个。后来,温绪伦甚至还打过耗子,晚上背着电瓶打,只要耗子一碰电就跑不脱。活路做还是做得下来,就是员工看不惯他,说他做得太快了,你快我慢的话,我就要被开除,出来打工卖恁个大的力气干啥子嘛?
2001年8月份的时候,家里又出一回事情。温永会初中考高中,没考上,不但没考上,而且还做了一回让温绪伦雷霆大发的事情。她为求穿得好,打扮得漂亮,把父亲寄回来的900多块钱在两天之内花得精光,买些衣服、裙子、高档皮鞋、项链、手表、化妆品、耳环,甚至还有种种补药,这下消息传开,温绪伦气得暴跳,说:“书不要再读了,再读也是条猪!”
就这样,温永会也来农场打工了,是年17岁。虽说17岁,在农场做了三个月,活路太苦,就去进离东升农场不远的石壁月亮贺卡厂,一进就喜欢上一个80年生的人,是个四川泸州的,叫黄天华,人腆但又义气,是个主任,这一撞上不得了,马上同居。温绪伦还算开放,看了人,觉得平平常常,还是要得,就允许了。
温永会在月亮贺卡厂做了一些月数,从厂里面出来的时候到过我的家乡朱沱,人虽然比过去漂亮,但慢慢变得刻薄、计较了。从我家离开后,她和黄天华又到了广东,黄天华搞广告,跑业务,跑2000块钱的业务有300块钱收入,但打工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上个月的20号,他们就离开了广东,回了四川泸州老家,黄天华还是继承他老爸的事业——做煤炭,温永会也准备学电脑,将来和黄天华一起搞设计。其实她要是迟走三天,就在我这里,我都可以教她,不须15天,就可以教会,不想这次机会错过,她竟要拿一两千块钱去学那点皮毛,真不值得。
温绪伦现在也还在农场干,分在蘑菇场,上次我去东升农场拍照时,他就拉着我说:“到春天的时候,你再来,那时你一定会看到一大片漂亮惨了的蘑菇,安逸惨了!”其实我是过去专拍东升血泪,在那血雨腥风的资本之地,望着一个个雷电下依然被强行弯腰做工的打工人,我又怎会记得要展示那些长满雪白镣牙的蘑菇呢?
在结束本文之前,对温绪伦还做了一次短暂的采访,全录如下。
杨:打烂仗这么多年,有啥子感想?
温: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杨:对比几个年代,真正幸福的日子有多少?
温:我这个人比较深沉,不大会讲话,要求也不高,所以啥子年代都一样。
杨:最难受是什么时候?
温:过去那些都不算啥子了,人嘛,荣辱不惊,现在也一样,不计较那些了。
杨:女儿差不多成人家的人了,是啥子心情?
温:说不伤心是假的。温永会这个小姑娘是我一天天看着长大的,她的脾气依我看,将来比她妈还怪,吃不得苦,又喜欢撒谎骗人,做事没有原则,做不成啥子事,只好看黄天华的能力了。
杨:黄天华这个女婿,你认为要不要得?
温:马马虎虎嘛,农村人还要求恁个高干啥子?但是我希望这个娃儿是条真汉子,不要在我面前耍啥子花招,要晓得我脾气发起来的话,没一个吃得住。
杨:我看你以前在朱杨镇那个房子已经倒了,在农场这么多年,目前有能力整个房子没的?
温:我要先声明,无论我有无能力,我都不会求人,更不会求女婿这些,不然人家说起来,说你这个当老汉的,修个房子都是你娃儿卖身来修的,这不好听。
杨:在广东干工也有两年多了,有没有想过离开?
温:想过,我主要是看到娃儿她妈精神承受能力差,怕她再犯那种事,所以决定留下来。我们这些年钱总共有一两万,还不够,还要找,但不会破了命地整,给别人当狗也有当狗的聪明。坦率说,我看不惯这些耀武扬威的人。
杨:父亲死后,妈呢?
温:还在,就在我老汉死那年,妈就嫁人了,嫁到大坝,大坝你应该晓得在哪里吧?但我很少去,那个老头我也没叫过他爸,都是叫四爷。
杨:没有生娃儿?
温:没有。原来四爷在没结我妈之前就有三个姑娘,三个姑娘都嫁人了,但很少打交道,跟这些人理理扯扯——没必要。人还是要自强,找不到吃的,靠人家,那是窝囊废。
杨:三个兄弟呢?
温:温二在家开压模板厂,温三在重庆煤炭厂,温四在北京,都比我好。这恐怕就应了一句老话:“出头哥子先遭难”,当大哥位置不同,命就不同。认了。你也是你们杨家的大哥,你的路啊,要好好走哦!不要像我这样,到头来“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
2003年3月19日@(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