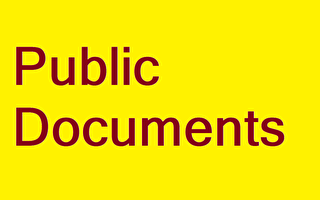龍的傳人
三十多年前的1979年, 「龍的傳人」這首著名歌曲問世。 當時美國政府決定與搬遷台灣的中華民國斷交, 宣布與中國大陸的共產政府建交。 因此台灣作曲家侯德建寫了這首歌。 首先由台灣歌手李建復演繹, 後來經過香港歌手張明敏和關正傑的分別演唱, 這首 「龍的傳人」傳遍了世界,在各地華僑中產生轟動。
龍的傳人
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江
它的名字就叫長江
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河
它的名字就叫黃河
雖不曾看見長江美
夢裡常神遊長江水
雖不曾聽見黃河壯
澎湃洶湧在夢裡
古老的東方有一條龍
她的名字就叫中國
古老的東方有一群人
他們全都是龍的傳人
巨龍腳底下我成長
長成以後是龍的傳人
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
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
百年前寧靜的一個夜
巨變前夕的深夜裡
槍砲聲敲碎了寧靜夜
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劍
多少年砲聲仍隆隆
多少年又是多少年
巨龍巨龍你擦亮眼
永永遠遠的擦亮眼
母親的堅守
中國人近百年的種種難關, 從八國聯軍到抗戰與多年的內亂, 炎黃子孫已無從見證祖國的輝煌,尤其對於離家鄉遙遠的海外華裔, 他們也只能在夢中看見這傳說中的巨龍 ,並希望這條巨龍會擦亮眼, 從百年的沉睡中醒過來。
1979 年, 我的母親被這首 「龍的傳人」 所動, 寫了一封信給還未出生的我。 信中描寫著她產前的心情。 二十幾歲來自台灣的她, 雖然選擇在異鄉結婚生子, 但她依然抱著一線希望: 在離故鄉遙遠的美國, 能夠教導她的女兒成為一個真正的「 龍的傳人」。
2000 年, 我二十歲生日, 母親將這一封我從未看過的信交給了我。 碰巧在同一年, 台灣出現了一個和我一樣在美國長大的歌手, 名叫王力宏。 他推出了自己改寫過的「龍的傳人」 。歌曲有搖滾風味, 而歌詞方面添加了他本人的家庭狀況, 讓我想起了自己父母的故事。 兩首歌曲當中最大的差別在這一段:
Now here’s a story that’ll make you cry
Straight from Taiwan they came
Just a girl and a homeboy in love
No money no job no speak no English
Nobody gonna give’em the time of day in a city so cold
They made a wish
And then they had the strength to graduate with honors
And borrowed 50 just to consummate
A marriage under God
Who never left their side
Gave their children pride
Raise your voices high
多年前寧靜的一個夜
我們全家人到了紐約
野火呀燒不盡在心間
每夜每天對家的思念
別人土地上我成長
長成以後是龍的傳人
巨龍巨龍你擦亮眼
永永遠遠的擦亮眼
我拿著這封信, 聽著這兩首歌曲, 開始思考母親為何會寫這封信, 又為何會在這時將它公開呢? 那一年, 我剛滿二十歲, 也許還看不出她的用意。
1964年, 十三歲的父親隨著祖父祖母來美。 當時移民到美國的中國人很少,而當時家裏不鼓勵小孩繼續講母語, 盡量讓他們入鄉隨俗。 1978年父親認識了母親, 據說對她一見鍾情, 但是母親和他交往的條件有一個: 必須要重新學好中文。 為了討好母親, 父親別無選擇, 只好埋頭苦幹。
1980 年, 我出生在美國的新澤西州。 從那一刻起母親就費盡心思地實現她的夢想, 尤其強調在家裏只能說中文。 這套規矩可不是開玩笑的: 要是犯了忌便家法伺候。 母親對我說話時並不會特別調整自己說話的風格, 一向都把我當大人對待, 非但不會刻意地簡化她的言語, 還經常採用具有歷史典故的慣用語和成語, 並且解說給我聽。 另外, 母親也一直很注意教導我待人處事的倫理道德: 忠孝仁愛,禮義廉恥, 母親無時無刻不在提醒我, 語言固然重要, 但道德修養才是中華民族的精粹所在。 長大的過程中, 母親是如何以身作則地照顧自己的父母和家人, 如何真誠的對待朋友, 我不敢說我做得到,但我看在眼裡, 記在心裏。
愛上中文
三十年前住在新澤西的中國人並不多, 附近的華人超市只有一家小小的東方雜貨店。 每個週末方圓百里的華人,多半都集中在這裡, 所以一到雜貨店,就派我拿著一個小籃子開始排隊, 準備算帳 —— 平常需要排一個多小時! 輪到我的時候,菜買完了, 還可以詢問老闆娘,她那櫃檯後面的錄影帶有甚麼新來的連續劇。 一次借用幾集, 下一個星期我們吃飯的時候就邊吃邊看。 我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就是這麼開始的。 先是 「星星知我心」 陪伴著我長大, 再是 「三朵花」、 「婉君表妹」 、 「啞妻」 、 「一簾幽夢」 帶著我度過少年時期。 比較成熟後, 迷上歷史和武俠片, 例如 「李世民唐太宗」、 「楚留香」 、「射鵰英雄傳」、 「倚天屠龍記」 、 「天龍八部」 。 雖然我並沒有特別去注意屏幕上的字,但多多少少在無意中吸收了一些。
1992年, 十二歲左右, 我已上了幾年的中文學校, 再加上對某些劇情已略知一二, 我發現自己勉強能看懂一些瓊瑤作品。 當然, 一開始認識的字並不算多, 但久而久之我發現自己看不懂的部分越來越少,我也學會如何用各種字典去彌補自己不足之處。
還記得, 那時侯沒有小耳朵電視, 沒有網路, 但每週五週六有一個電台提供兩小時的中文節目。 我有一天聽到綜藝節目主持人介紹了兩個青年音樂團: 一個叫紅孩兒, 一個叫小虎隊。 從此我就愛上了他們: 一聽說有親戚朋友要去台灣或香港, 就拜託他們帶錄音帶給我。 再過幾年,新澤西中部終於開了一個大型中國超市, 旁邊開了一個 世界書局。 我並不清楚它平時的生意如何, 但我能肯定, 我在高中賺的零用錢是完全被它吞噬了。 我經常一整個星期不吃中飯, 把省下的錢拿去買光碟。 書店的阿姨看我可憐, 還特別送了我一張能打九折的貴賓卡。 更神奇的是我其實也不清楚自己喜歡哪些歌星, 所以下手購買的時候我也不能確定專集的質量。 還算幸運, 我就這麼誤打誤撞, 認識了當時港台流行的歌手: 周華健、 王菲、 張宇、香港四大天王 、黎明、 張學友、 郭富城、 劉德華、 還有台灣的四小天王, 林志穎、蘇有朋、吳奇隆、金城武。 我把磁碟拿回家以後, 必定會從歌曲中挑選出自己欣賞的一個, 再用注音符號寫出歌詞, 所以每個專輯至少有一首歌我能唱。
同時我也開始迷上京劇。 我想在美國生長的小孩中很少會有如此的興趣, 但我是真的喜歡看。 只要聽說有劇團表演, 或是跟師傅有學習的機會, 我一定是第一個報到。若是到了台北、 香港、 北京, 二話不說就開始詢問有甚麼新戲上演。 親朋好友都各自被我強行逼迫參加文化欣賞節目。
母親特別鼓勵我參加中文學校每年舉辦的演講比賽,一直認為這種挑戰能夠提高我對咬字發音的警覺, 同時也能訓練上台的風度。 我在大紐約和美東地區連續拿了不少比賽金牌, 而從小演講的經驗讓我建立了一定的信心。 但更關鍵的是, 無論我寫得有多辛苦, 母親堅持要我自己準備講稿。 相信她當年也沒有料到, 我也是因此學會如何用注音和拼音輸入中文字體, 而這兩種輸入方式也讓我有了意外的收穫: 打字時必須對咬字和發音有一定的把握才找得到正確的單字。
到了哥倫比亞大學, 我為了讓中文更上一層樓, 選修了中國現代文選讀, 古代漢語, 和歷史文學方面的課程。 雖然唸得非常吃力, 但至少不懂的地方還能連夜傳真向母親求救, 也因為願意挑戰自己而認識了許多鼓勵我的好老師。
找回文化的根
我就是經過這麼多方面的磨練,加上母親和老師的指導, 隨著自己的興趣, 漸漸地奠定了語文的基礎。 我發現語言能力使我跨越時代、地理、輩份、文化、及各種圍牆。 我能躺在外婆的臂彎, 聽著她形容自己在抗日時期是如何勇敢的帶著公婆到山洞裡逃難; 我能握著外公病危的手,看懂他輕輕在白板上用中文寫出的指示;我能與湖南鄉下的遠房親戚說說笑笑, 或談論他們是如何度過文革和大躍進;我聽著大學的古代漢語老師解釋老子、 莊子, 能體會其中的奧妙。 不知不覺, 語言讓我開啟了一扇千金門。 如果沒有父母從小的叮嚀,我也許連入門都談不上。
今天去回想這一切, 常問自己當初是為甚麼如此的投入中國文化。事實上答案並不偉大。 我還記得以前常聽父母和朋友提起, 二十一世紀將會是中國人的世紀, 常聽他們告訴小孩, 學中文以後能夠對事業有幫助。 但事實上我從未為這些實際的原因所動。
我成長於白人的社會, 而我最早的記憶就是自己一直都是一個被排斥的旁觀者。 童年時我因為自己的中國面孔而遭遇的岐視還真不算少。 不懂事的同學會拉著眼皮, 壓扁著鼻子, 嘲笑我的長相。 我想和別的孩子玩鞦韆, 卻被同學惡意地推下來。 平常在家理活潑開朗的我, 在學校反而變得非常害羞, 不敢多說一句話, 也因為被歧視而缺乏自信。
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將自己投入了對我張開雙手的中國文化,把它當成自己的避風港。 在中文學校我得到了我渴望多年的歸屬和接納, 我漸漸從這個環境中找到了自己的聲音。 我發現我是一個能夠輕而易舉地啟發同學的領導人。 無論是好事還是壞事, 到養老院當義工或是帶著朋友開舞會,我總是很自然地被列為愛出餿主意、 帶頭搗亂的老大。 我因此建立了一種獨特的自我, 讓我有力量去面對嘲笑我的人,有信心去對抗岐視所造成的外界環境。
我是個愛打抱不平, 熱愛自由的人, 需要寬廣的生活空間和毫無拘束的選擇方式。 我喜歡以坦誠、 直接的態度面對任何挑戰。 同時, 我也深深地被母親的精心教導影響, 強烈的感到對父母和家人,自己有一份濃厚的責任和義務。 對人處事, 我時時記得母親的叮嚀, 反省自己的舉止言談, 常感到自己做的真是微不足道。
責任與使命
三十年以來世界對於中國的看法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改變了。小時候因為自己是中國人而經歷過許多挫折, 甚至要求父母幫我染頭髮和皮膚。 但現在反倒是外國人緊追問著我如何打入中國市場。 無論是北京、上海、香港、台灣, 處處都能找到正在努力的外國商人和學生。最近我也幸運地爭取到了夢寐以求的發展機會 ——我將要搬到香港, 幫一家美國金融公司開創中國市場。 面試途中不只一兩次的考驗我的中文會話能力, 接二連三地從「你好」握手開始,就沒說過一句英文 —— 真是把我嚇得滿身大汗。
在許多思想觀念方面,我是個正宗的美國人, 我也相信這一點將會帶來一些工作方面的難題。 我一直認為美國最可愛之處,是它對改革的熱情:無論是法律、 政治 或社會觀念方面, 美國是一個容易推動、 富有彈性的社會。 對我來說, 中美文化間最大的差異就在於它們對社會挑戰的處理態度。美國人總是認為世上無難事, 若想要改變甚麼, 就該推動大眾, 實現夢想。 相對來說, 中國人則比較保守, 一切以維持現狀, 自掃門前雪為準。
尤其是接受了這份新工作之後, 我發現自己將要面臨的挑戰還真不簡單。 我深深地體會到, 要做一個貨真價實的「龍的傳人」,要求的不僅是語文方面的知識。 身為一個在美國生長的中國人, 我肩负的責任是雙面的:一方面我渴望能夠與外國人分享,我所認識的中國文化和思想;另一方面我也感到有義務,將美國的自由思想和社會精神傳播到中國, 希望它在不久的將來,能夠因為人民的意願和力量而變得更開放、 民主。
母親將那封信交給我時, 我剛滿二十歲。 十年後的今天, 我希望能夠對母親在我出生前定下的願望有所交代, 讓她能看到自己的苦心沒有白費,另外告訴她, 我將不斷地努力, 完成她的心願: 做一個貨真價實的「龍的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