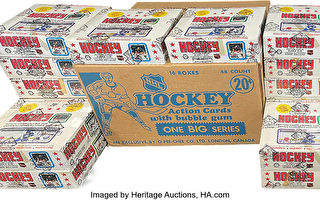【大紀元2017年08月16日訊】看到吧,王子草都要長到人頭那麼高了。
好幾次,我回老家,在爺爺的墓前,母親都這樣說。
在我們湖北老家,有這樣一種說法:墳頭上的王子草(茅草)長勢越好,後人就越新旺發達。
生活無止無休的動盪。多年來,我的生活被卷進了季節的淤滯之中,在同一個地方來回地打著轉,爺爺墳頭上王子草的庇蔭,仿佛是刻意繞過了我。反正,在我身上,絲毫看不到發達的跡象。
母親嘴上說王子草長的旺盛,實則是在寬慰我不要灰心。
和親人們拉家常,唯有把話題轉到童年時光,我才會變得活泛和健談,一起經歷過的事情,都還記得清楚,儘管前後脈絡和情節全是空白,但是一個個場景的色彩卻鮮明地浮現在當事人的腦海里。
「記得妹妹一個人躲在廊檐下吃柑子,躲著我和弟弟。」
大我五歲的姐姐揭露我小時候吃獨食。「還記得不———抬豬,你每天睡覺前都要玩抬豬。有一次,我和姐姐故意把你拋到地上,你扯著嗓子嚎,害得我們挨一頓打。」
我頭上的小哥也參與對我這個淘氣妹妹的控訴。抬豬,姐姐和小哥獨創的遊戲。睡覺前,姐姐和小哥各自站在床頭床尾,各自拎著被子的兩角,我則躺在被子上,任由他們兩個往上拋,接住,再拋,再接住。我高興的咯咯笑,他們累的胳膊酸疼。那晚,大概是我賴著不下來,惹惱了他們,姐弟倆聯手把我給拋到了地上。
「妹妹小時候真的很霸道。橫。六一兒童節,我和同學有一個舞蹈節目,同學借穿了她的紫紅燈芯絨上衣,正在台上表演,妹妹在台下瞧見了,不干,爬上戲台,非得讓人家當場脫下來。」姐姐說到這裡,笑。聽的人也都笑。
我們就這樣確認著彼此共有的各種場景。他們說的,有的我還記得,有一些,我想不起來了。
記憶中我有偷吃過南瓜子。那是來年做種子的。怕我和小哥偷吃,母親把南瓜子裝在布袋裡,懸掛在在天花板的正中央。我仰頭觀察了幾次,終於想出了辦法,用細竹竿去戳那個布袋子,功夫不負有心人,那布袋子被我戳了一個小洞,想吃的時候只需用棍子扒拉那個布袋,南瓜子就一顆一顆的往下落。
第二年春天,母親把布袋解下來準備去播種,發現沒剩下幾顆,她以為是老鼠,於是,家裡那隻老黃貓遭了殃,被冠以失職罪,遭到餓飯一天的懲罰。
長路漫漫。在我缺席的這二十多年裡,家鄉的變化是驚人的。首先是沒有了人。八十年代出生的第一批獨生子女均已長大成人,或求學或外出打工,一個一個離開了故園,到處可見鐵將軍把門無人居住的空房。若不是間或有車輛疾馳而過,你會懷疑這裡是否還有人煙。
老的人大都走了,一個個走進了土裡。偶爾看見路邊新聳起的一個墳堆,上面插著白色的清明吊子,憑著記憶,想著這是誰的地界,估摸著裡面埋著的又會是誰。有的是不該走的人,還很年輕,疾病或是車禍什麼的,聽人說起,說的人和聽的人都唏噓。這個世界,很多時候不按規矩出牌。
半老不老的人還留守著,像一片片枯黃的落葉,天氣晴好時,他們各自要忙自家的營生,雨天就聚在一起打牌,佝僂的背影,仿佛記憶或夢境裡的人物。偶爾也會談談在外謀生的兒女。年輕人在外謀著生,他們的父母在家等著死,這是當今社會的普遍真實寫照。
其次是沒有了水。家門口的小河,過去,一到夏天,男孩子們三三兩兩,結伴下河游泳扎猛子。而現在差不多徹底乾枯了,河灘邊滿滿的,全是淤沙,除了白茫茫一片沙灰,細細的流水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唯一沒變的,是賭風依舊盛行。在中國,無論城市還是鄉村,有人的地方就有麻將,就有賭場。這真的很悲哀!可我們卻無力去批判———醒目的貧富差別,東西部地域的差別,從上到下,大小官員魚肉欺詐百姓的事件屢出不窮,被壓在最底層的民眾,麻木是他們生存狀態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這世上,有太多十字路口,有的通往光明,有的通往黑暗,而在極權國家,民眾根本沒有選擇的自由。民眾集體的麻木,成了社會穩定的大法碼。換言之,我們所謂的社會穩定,所依賴的,正是底層百姓無意識的集體麻木。遠的不說,就說現在,社會分裂如此嚴重,可有些人不僅看不到,反倒還覺得眼前一片歌舞昇平。
一旦民眾從麻木中醒來將是如何的天翻地覆!歷史已經告訴了我們很多很多……
由此,也就明白了,為什麼意識形態(奴化)教育要從娃娃抓起。一切,都是統治階級為了統治的需要。
除此,再也沒有別的什麼了。
責任編輯:岳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