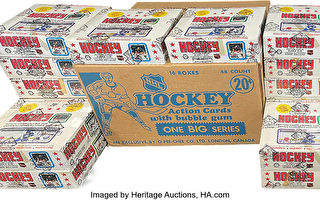【大纪元2024年02月26日讯】我出生正赶上“三年大饥荒”,那是饿肚子的年代。因为生孩子,我父母托人买了30多个鸡蛋,把鸡蛋腌起来等着坐月子吃。街道居委会看到我妈妈要生产了,就到我家里来“拜访”。从床底下发现了那盆咸鸡蛋,就全部端走了,说是鸡蛋都要出口。
从我记事起,什么都是凭票限量供应。能吃饱饭是最大的奢侈。我邻居家孩子多,吃饭时每人一个馒头(多是粗粮窝窝,因为粮食供应比例就是那样),剩下的馒头就锁起来了。有的老工人为了让孩子能吃饱,辞去公职带着孩子回东北林区老家,想开荒种地,那从此就是城乡的区别了。
一天,我妈妈和她同事从机关食堂买饭出来,突然冲出一个农村小伙,抢了她同事两个馒头,他先往馒头上吐吐沫,然后蹲在地上用胳膊护着狼吞虎咽地吃,不知他多少天没吃饭了,任凭怎么打也不动;妈妈办公室还有个男同事,月初没计划好,饭票提前吃完了,到月底喝酱油兑水充饥,饿得起不来床;我刘叔的母亲在农村,在自家屋后种了几棵玉米,被生产队长当作“割资本主义尾巴”羞辱批斗一番,老太太回去就上吊了。
毛XX讲:“深挖洞,广积粮。”很多家都挖防空洞,我邻居董叔挖了很深的防空洞,我们小孩爱去钻洞玩。一天,他把洞口盖起来了又扎上篱笆,不让我们小孩进去了。很多年后才知道他在洞里养兔子,半夜杀兔子吃。
我家有本书,内容是怎样做饭能让粮食变多,都是骗肚子的把戏。几十年后我妈妈还提到她们书记,一开大会就说他家粮食怎样够吃,又吃干又喝稀的,其实大家的粮食都是定量的,都饿。他就是做那种说鬼话招人恨的工作。有一次我妈妈同事告诉她,我爸爸在买饭回家的路上偷偷吃了一个馒头。那年代有的家庭饭票都是分开的,各吃各的。
我记得小时候邻居大娘大婶来我家串门,说话间有个很常见的动作就是拉高裤脚、按小腿让对方看,一按一个坑不弹起来,长大了才明白,她们都是饿得浮肿。
据我妈妈讲农村更差,很多女人饿得不来例假,没有了生育能力。待经济缓过来一些后,有农村人进城偷孩子养(我们那是新建城市,周边是农村)。有一个丢孩子的人家好像找到了自家的孩子,不过对方的邻居们帮助藏那孩子,换别的孩子让他辨认;孩子丢的时间长了,孩子也变样了,孩子太小也不记事,更难找了,那时候也没有DNA鉴定。有一个电工孩子丢了,疯了一样,也不工作了,天天背着一包印有孩子照片的印刷品,到处张贴找孩子,造成另类悲剧。
“臭老九”撑起的中国科技
从我记事,我家里就有电话,那电话就像系在我爸爸脖子上的细绳,电话由单位总机室接线员转接,都是半夜工作上的急事。我爸爸只要不出差就是白天上班,晚上看书,查资料,我从来不知道他几点睡觉,家里最多的就是书。半夜电话铃一响,全家惊醒,我爸爸接了电话就得走。冬天屋檐上挂的冰溜子一尺多长,夏天电闪雷鸣,越是极端天气,工地越容易出事故,见他缩着脖子,推着自行车就冲出门。我从小就知道那是工作,是责任,那个年代的人都非常敬业。
苏联专家撤走前夕,在东北一个重工业基地,我爸爸提出要修改设计图纸(他一直跟随苏联专家工作),大家都反对,因为是苏联专家的设计。后上报给上级领导,他们也不敢决定。后来苏联专家听到了这件事,专门过来和我爸爸见面。经过讨论,专家同意了修改方案。新的设计方案为国家省下几十公里的电缆,这事也上了报纸。并奖励他300元钱,他全部请客给参与者,他说:“活都是大家干的。”后来2、3次涨工资他都主动让给别人。那时人的道德水平普遍都高。
反右运动过后知情人告诉我爸爸:“他是内定的右派。”反右时工作组传达上级精神要大家“向党交心”,人人发言过关。他同学之间相互传递着一些消息,有人抱着为国家建设的良好心愿,可能话也有偏激,结果都记录在案,就是日后当右派的证据。我爸爸在大会上说些小事,不足以当右派,上级工作组就多次找他单独谈话,每次都被告知,“他下井了,他在工地”,没找到他,上天恩赐让他蒙混过关。
当上右派的同事就凄惨了,别说为国效力,生活都很艰难,甚至失去人身自由。提起往事他痛心地说:“今天还是在一起工作的同事,隔天就得划清界限,或者是人不知去向,太可怕,共产党太阴险了。”
我妈妈年轻时也是“拚命三郎”,我小时候在长托幼儿园经常是最后一个被接走,周六的晚上我趴在幼儿园窗户玻璃上,希望路灯下小道上走过来的人是来接我的。阿姨安慰我,我也知道如果我要被接走了,她也就下班了。
恢复高考后,我发现我很笨,我妈妈说:“是因为你没有受过系统教育。”或者说:“那时候大人都吃不饱,孩子智力就受到影响。”我说:“你都吃不饱,你还生孩子,你不是害我吗?”在我生孩子后,我妈妈才告诉我,在一次工地事故中,她为了救人,她给别人献血,不知道肚子里还有一个生命。不管怎样我还是四肢健全地来到了世上。
那年代工程技术人员都是非常敬业,也爱学习,省吃俭用买书,家家都有很多技术书。我门叔进京搬家时,书不能全带走,用三轮车往造纸厂送;我爸爸让他处理书就像要割他的肉,千挑万选,其实知识老化更新早都是废品了;我家楼上退休多年的刘叔家里装修时对老伴说:“你给我留几本,让我还能想起我这一辈子是来干什么的。”那一代的工程技术人员对专研技术、对书,那种情感上难以割舍的心,现在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下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有人身自由的那些 “臭老九”们 ,就是这一大批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凭着一颗颗拳拳的爱国之心,饿着肚子、负重前行,撑起了祖国建设的脊梁。
栗子不好吃是苦的
为了摆脱饥饿,我妈妈要求下放当工人,这样粮食定量从每月26斤增加到每月40多斤。她下放后在总医院修理医疗设备。
一年秋天,鲁山军用飞机场(在大山里)仪器出现故障,让我妈妈去帮助排查修理,当时是机密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她回来带回一些苹果、核桃和板栗。我爸爸就说:“板栗留着,等过年有肉了,栗子炖肉那才好吃哪。”我就盼着过年吃栗子炖肉,我父母属于那种不太会生活的人,栗子很容易生虫子,很快发现板栗坏了,赶快剥开,除了变黑的之外,有点变色的部分都舍不得扔。栗子炖肉我是没吃着,但我知道了栗子不好吃,苦。
有一次我爸爸到山东某市开会,当地盛产花生。那年代市面上根本就见不到花生,据说是出口给外国人吃了。我爸爸在电话中暗示可能带花生回来,全家沸腾。他回来后讲述花生米来之不易的故事。
他们先内线联系,半夜起来,大家要分头离开宾馆再聚合,在向导带领下走很远的山路到达约定地点,去的人都是能背动多少就买多少(带壳),天亮之前交警还没上班就赶回宾馆,半夜起来剥花生,在回家的火车上同行人相互关照防止被乘警发现,一路上偷偷摸摸终于把花生米带回家。
我姥爷是给大财主家赶马车的(会点武功),属于被剥削阶级。听我妈妈讲:“马车后面有一个专门装零食的小木箱,他每次回家都会给孩子们带点花生、瓜子、麻花之类的。我妈妈说:“我和你爸爸这么努力工作,你们现在的生活还不如我小时候生活好。”我姥爷挣钱少但还能给孩子买些零食吃;我父母挣钱多但市场上没有,买点心也要粮票,粮票就那麽多。
有个词叫“鸡屁股银行”,农村老人家养几只鸡下几个鸡蛋舍不得吃,卖掉换几个活钱买盐什么的。在路上经常看到农村大娘跨个篮子,上面蒙块布,布下面放几个鸡蛋。擦肩而过时会轻声问一句,“要鸡蛋吗?”也有成年人从身边走过说句“要布票吗?”如果想买就到一个僻静地方交易,那是违法了。也见过农村女人卖什么被抢秤抢篮子的,坐在地上撕心裂肺地哭。
给孩子做件新衣服,老大穿完,老二穿,讲“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电影上的白衣服蓝裤子,那才是胡扯八道哪,别说一年就那几尺布票,肥皂票也限量啊,洗白衣服多费肥皂!
后期又出现了农民进城换大米,是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农民拉着架子车,车上放着几袋子大米,走街窜巷吆喝着“换大米”。比如:一斤半玉米面换一斤大米,你从家里面袋里挖出几碗粗面交换大米,这也必须是有道德和信任做基础的。现在市面上有毒大米,你敢要陌生人的大米吗?从你家里拿出来的面干不干净?掺没惨什么东西?人家敢收你家的面吗?人的道德不行了太可怕,谁也不敢相信谁,谁都防着别人,最后把自己也圈死了。
责任编辑: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