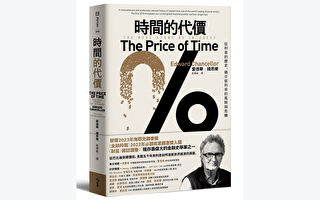【大紀元2015年01月28日訊】【筆者按:這兩封與友人探討當代中國知識界以及陳寅恪、馮友蘭問題的信,或者更明確地說,探討黨文化中對於理性等概念的扭曲和再造,探討為甚麼它們是一種新話的書信,寫於二〇一〇年。之一發表在《新紀元》雜誌第243期(2011.09.29),而之二則一直沒有發表。人生匆匆,現在不覺四年半過去,中文知識界對於這些概念及問題依然沒有討論,更遑論推進對它們的探究了。但是,這些思想問題在我看來是非常基本的問題,如果不弄清楚,那麼就再討論其它問題就只不過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甚至可以說以訛傳訛。
我之所以認為這些思想問題,也就是這些基本的概念問題是根本問題,是因為它們是五四以後中國知識界的「逐漸」意識形態化,四九年後的「完全」意識形態化的產物。它隨之又導致最近半個世紀中國文化知識界的徹底「黨文化化」。這一切可以說完全是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曾經指出的黨文化、新話的活現實。
為此在這種意義上,這兩封看來討論具體概念和問題的信其實針對、分析的是這十年來越來越被人們關注的黨文化。這個黨文化不僅是政治統帥一切,一切為政治服務而導致一種以論帶史的「假大空」——在思想方法上徹底地使得中國的知識界產生了癌變,而且還推出了一整套的奧威爾所說的「新話」、新的語言方式。這種新話、新的語言概念和語言方式首先使人們忘記了那些原來概念的含義,尤其是那些翻譯過來的思想及概念的原文意義是甚麼。為此,就如我們這一代,就是在共產黨社會中再看到那些概念,再使用這些概念也根本不再是原來的意義了。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筆者過去曾經討論過的、現在中文世界普遍使用的「自由主義」、「科學」以及「啟蒙」了。在本文中討論的對於「理性」的理解和解釋的遭遇也是如此。
其次,如奧威爾所說,這種對傳統或外來概念的解釋或再造讓人們再也看不到、感覺不到原來的思維方式是甚麼了。
「新話的目的,不僅是要為英社的支持者提供一種適合於他們的世界觀和智力習慣的表達手段,而且是要消除所有其他的思維模式。這樣在新話被採用、老話被遺忘之後,任何異端思想、也就是違背英社原則的思想就根本是不可能被想到了,至少在思想還依賴文字的情況下會這樣。
新話的詞彙之所以如此構建,目的就在於使黨員在想合適地表達每種意圖的時候,都能夠精確而且常常是非常敏銳地表達出來;而排除了所有其它意圖的存在,甚至用間接手段獲得這些含義的可能性都將會完全不再存在。要想能夠做到這一點,部份要依靠發明新的單詞,但更主要地是要消滅那些不合需要的舊詞,清除那些被保留下來的單詞的非正統含義,而且只要可能,就要把所有次一層的含義全部清除。」(奧威爾,《一九八四》,附錄:「新話的原則」)所以我在零三年悼念李慎之的討論中曾經說過,這個討論在六十年代末期就應該開始。而只要我們還不曾開始討論這種新話,黨文化就會繼續籠罩著我們。但是令人遺憾的是,我們推遲了二十年以上。至於信中所涉及馮友蘭、陳寅恪等學者的歷史問題,我以為也是與此相連的問題。
歷史之所以能夠發展到四九年那樣的結局,而四九年之後,這些東西之所以在中國知識界迅速蔓延,以致使得中國知識傳統的毀滅達到在任何一個共產黨極權主義國家所不曾經有的徹底,都有著偶然的、具體的歷史的原因。所以我認為,對馮友蘭這代人重新討論和認識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其二,黨文化對於這幾代人不僅在知識上是毀滅性的,而且對知識、對人生觀、對人生中的求知、治學觀都產生了毀滅性的影響。我談到的陳來們,我對他們的批評絕非是批評他們個人,而是對黨文化給他們的人生觀、治學觀不同意。我希望下代人能夠不重蹈我們這代人的覆轍,越早看到並且從這種黨文化的畸變中走出來,重新確立傳統的人文和人生態度越好。
基於這個希望,我希望把兩封信重發於此,希望有更多的人來討論這些具體問題。這個討論在現今中國知識界,「黨文化」問題是絕對不能迴避的問題。誰看不到這個問題,沒有反省討論過這個問題,誰在知識領域的工作就一定會出問題!(2015-01-26,德國•埃森)】
陳寅恪、馮友蘭及當代中國知識界問題——致友人的信(一)
XX,你好!
關於你傳來的陳寅恪與馮友蘭比較一文,由於不是我的專業題目,所以只能夠談幾點自己的感受。
首先是題目,我覺得這個題目太大了,按照我的想法我覺得叫《學術尊嚴與學人品格》更為合適。因為牽扯到理性問題,我覺得你在文章中把握得還不很清晰。如果把一切歸於你所說的那個抽像的「理性」,如你文章中所說,「理性,是學術的靈魂,沒有理性,就沒有學術可言」,「沒有理性,既不能有科學,不能有哲學,也就沒有了學術」。那麼首先你以此為出發點的論述方式,就不是一種學術式的描述、分析的論述,而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式的論述了。
因為對於學術的探究問題來說,如果你要使用「理性」,你就必須給予明確的交代,甚麼是理性,你用的是那個西文詞是Ration,還是德文中的Vernunft。就是同一個理性單詞,在黑格爾、海德格、薩特那裏,和在休謨、洛克、波普、維特根斯坦、羅素那裏也是不一樣的。
我曾經想深入細緻地研究一下「理性」問題的,也準備了一些探討這個概念的書。但是由於時間和精力,計劃中的極權主義問題的尚沒有完成,所以這個題目一直沒有完全展開。
說來有意思,促使我想對「理性」問題做一個詳細研究的是,因為我的老師許良英先生等馬列主義哲學學者們始終口稱「理性」,但是,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說,直到文化革命還進出韶山痛哭流涕,要緊跟黨干革命。七十年代中期後,他說自己政治上「有所覺悟」,但是,於我來說奇怪的是卻沒有反省自己的「理性」和「良知」出了哪些問題。為此,對於他們推崇的如此的一種「理性」,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理解,最後還是只好我來研究回答。
第二,許良英先生他們終生所攻擊的科學哲學家們,例如當代維也納學派、波普、羅素,也就是他們所說的近代經驗主義、唯理主義為代表的哲學家們,他們對於「理性」的理解是和許良英先生他們理解的完全不一樣的。這涉及到,近代科學思想是甚麼。而正是由此出發,馬克思主義哲學沿襲的傳統實際上是反「科學」、反「理性」的。同樣是這一點,使我看到曉東轉給我的你的文章中對馬克思主義的論述讓我吃驚。因為你居然看到馬克思主義的「非理性」的一面。
解決這個問題,本來對於我對於啟蒙問題的進一步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許良英先生也罷,李澤厚也罷都還不知道究竟甚麼是西方哲學思想中所說的「理性」,不知道必須對這些基本問題上去思索反省。他們推崇啟蒙,但是恰好就是在這一點上,也就是「理性」問題上,馬克思的思想是沿襲的是對抗近代科學思想所推崇的「理性」的傳統,馬克思是反「啟蒙「的,所以馬克思主義究其根本是和啟蒙帶來的思想潮流對抗思想。
對於理性這個問題更有意思的是,在我正在關心的政治化宗教問題中,Voegelin認為,對人來說,有一種外部的超越人的宗教,一種內在的宗教,內在的宗教是人的精神和所謂「理性「產物。當不適當地誇大了希臘的這種理性化傾向的時候,也就是不適當地誇大了內在的能力的時候,就產生了政治化宗教、宗教世俗化,也就產生了極權主義。極權主義是當代的諾斯替派。
毫無疑問,極權主義是當代西方文化的典型產物。當代西方文化的兩個淵源一個是希臘文化,另一個是沙漠而非《河殤》所說的海洋來的宗教文化。在政治化宗教這個探索方向上,我摸索到了宗教文化,也就是基督教文化中的一些被世俗異化的因素,但是Voegelin的這個論述卻讓我看到了當代極權主義的希臘淵源,套用那些專門喜愛假大空煽情語言的人的說法,也可以說來源於「海洋文化」。自然,波普在《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中從認識論的角度追溯到了柏拉圖。但是,那是從科學的認識論的角度。而Voegelin卻是從非科學的,形而上學的宗教文化思想史上讓我摸到了極權主義的希臘的思想根源,也就是極權主義的「藍色」文化思想精神根源。
Voegelin是文化保守主義,崇尚思辨,激烈地反對維也納學派的實證主義,可是在一些文化政治哲學方面還是可以說是一位嚴肅的,可以與之討論的社會學家。可見無論是自由主義思想,還是保守思想,對於理性與非理性問題的研究一旦具體了,就不再是意識形態式的了,就可能進入深入的問題討論和研究!
無論是「理性」,還是「非理性」,都有可遵循的嚴格的學術探索之路。沒有理性,當然就沒有科學,但是,沒有理性卻可以有哲學、有學術。
說到底就是完全沒有西方學術,不知道西方學術,也不能夠像馮友蘭、週一良、季羨林那樣討論問題,治學和為人。例如陳寅恪的精神其實就完全是中國的,他堅持的也完全是中國的,可他卻是一座高山。
先寫這一點,對於你對馮友蘭等的評價,稍後,我會再談幾句。因為我正在構思自己的關於五四的一篇反省文章,回信也不敢拖得太久,故此先匆匆如此。
如有不對,敬請不客氣地指出。
維光
2010-4-19
陳寅恪、馮友蘭及當代中國知識界問題——致友人的信(二)
XX,你好!
你談到所說理性是指英文的reason,但是我突然想到,陳寅恪「王國維遺書序」所用理性一詞,如果一定要對應西文的話,應該指的是理念、理想的意思,也就Idea。Idea這個詞,有時候也翻譯成觀念。
談到這裡,我想加一句,很多詞的中文翻譯不一,要瞭解真正描述的意思,必須懂得西文。語言由於是一種思維方法,嚴格說根本不能夠百分之百對譯,只能夠解釋。所以我認為以後在哲學系,乃至物理數學系的教學都要給出西文原來的詞來。因為迄今為止我們說的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哲學、乃至物理學,其概念範疇都是西方人做出的。一種語言是一種思維方式,所以如果談論這些學科就必須給出原來的西文。換句話說,不懂西文的人,是很難真正進入這些學科,到達一定深度的。我認為這話是可以這樣武斷地說的。而更由於現在學術及語言的互相滲透,影響,現在就連專門的中國文化、思想、各種學術研究,如果想準確深刻,也需要西文的根底。
但是,在這裡我卻還想說,對於陳寅恪來說,由於他的思想和學問根底,也由於這是一篇紀念中國傳統文人,傳統文化的文章,因此這裡使用的「理性」甚至最好不去比照對應西文的意義更好。它應該如「氣功」一詞一樣,真要對應翻譯成西文的話,就要直譯,就要直接去尋找中文這個詞的意義。
你讀過錢基博,也就是錢鍾書的父親的《中國文學史》嗎?那是一位和錢鍾書不可同日而語的大「家」,可是名聲卻居然不如錢鍾書。但這就是人生!
錢基博在書的開端就對文學二字的含義作了探討。中國人的「文學」並非西語的Literature,中國傳統文化中對文學是如何認識的,以及他的中國文學史如何對待這個概念。
對陳寅恪這樣根基的人來說,當然西學要追隨中學,去開掘它的意義了。這其實也是陳寅恪後來不去治「域外史」(西洋史)的原因。治西洋史,他要追隨人家。此種對學術與自我的感覺,也是我下面要說的,是他之所以與馮友蘭有根本區別的淵源。
由於你的很多想法我以為很難得,所以,我才想多說一句,你是否能夠再斟酌一下某些提法。這裡,我想說的是你對於馮友蘭所寫紀念陳寅恪一文的看法,認為它是「精品」,對此,我覺得,這種提法,很可能會給你以後研究馮友蘭的觀點帶來困惑。像馮友蘭這樣的一個人,我不認為他可能寫出「精品」來!
我以為,馮友蘭和陳寅恪的不同,不是一般的程度性的,而是根本不在一個層次、一個世界,從為人到治學。馮友蘭之表現不僅是在共產黨統治時期,究其終生,其治學、為人都有待商榷之處,這就是說,他前期的治學為人是在哪種層次、領域和境界,也還必須要辨析。對於近代中國思想史,我瞭解不多,僅就管中所見,就他們的區別談幾點看法。
一、為人:陳寅恪吳宓,在清華獲知北伐軍北上的消息,其反應並不是你我從小受的歷史教育上的那種歡欣鼓舞,而是憂心忡忡,相約絕不入黨,「他日黨化教育瀰漫全國,為保全個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有捨棄學校,另謀生活。艱難固窮,安之而已。」(《吳宓與陳寅恪》,49頁)這段話非常值得思索!而與此成為鮮明對比的就是你文中提到的馮友蘭與國民黨和當權者的關係。陳寅恪的這種態度是他後期所以隱居嶺南,並有那些與專制者直接對抗的根本所在。馮友蘭從來沒有這些,不僅談不上對抗,而且也無處可以和陳寅恪對比。
二,陳寅恪是地道國學,但是馮友蘭前期就是取西洋哲學觀念來梳理中國哲學問題。這是五四以來的一個典型傾向,直到如今,仍然是用西方哲學的範疇來肢解中國哲學。陳寅恪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審查報告中說的已經非常清楚。後來的馮友蘭不過是換了一個框架,由「取西洋哲學觀念,以闡明紫陽之學」、《新理學》,換成唯物、唯心、階級、革命而已。這對於我這樣的只專注於他的思想問題、而非政治問題的人來說,他的後期和前期,從方法論上說,並沒有甚麼區別。
在此,我認為,陳寅恪對於這種「取西洋哲學觀念,以闡明紫陽之學」,是非常不以為然的。在那樣一種時代的氛圍,以及那種人際關係下,陳寅恪特別說到此,已經算是說到了極點,留下了一個大大的伏筆。
多少年來我們已經習慣於以這種外在肢解的方法來理解另外一種文化思想精神。這是一種西方中心論思想的產物。今天在西方通過科學認識論,已經使我們清楚地看到這種肢解的界限,及不真。觀察滲透著理論,戴著眼鏡看別人的文化,如何能夠看到真面目。一種文化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追求方式,用另外一種概念和思想不可能完全理解它,窮盡它。為此,也就更使我們對當年陳寅恪看法的深刻和準確,對於他對於西方「方法問題」與「思想問題」的「區別」「把握」感到驚嘆。
在此,我記得我太太還學文的導師,洪謙先生四九年前曾經和馮友蘭有一個爭論。我以前讀過,他批評馮友蘭對形而上學問題及維也納學派的思想的瞭解並不准確,甚至完全是錯誤的。
洪先生地道的西學,清楚簡練的分析、行文,當時就讓我歎為觀止。
三、如上,馮友蘭的道路和思想基礎決定了,最後,也就是八十年代後馮友蘭對於中國傳統的所謂「回歸」,也不過是個別觀念的回歸,並且他注重的問題依然是表面的社會效應,而非最根本的文化、思想問題。這和陳寅恪有著根本的區別。陳寅恪對於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區別的論述,在我所知道的有限文獻裡,最典型的是二十年代初期,吳宓所記載的與陳寅恪交流中的看法。
「自宋以後,佛教已入中國人之骨髓。唯以中國人性趨實用之故,佛教在中國,不得發達,而大乘盛行,小乘不傳。而大乘實粗淺,小乘乃佛教古來之正宗也。然惟中國人之重實用也,故不拘泥於宗教之末節,而遵守『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之訓,任儒、佛(佛且多為諸多宗派,不可殫數)、回、蒙、藏諸教之並行。而大度寬容(tolerance),不加束縛,不事排擠,故從無猶如歐洲以宗教嵌入政治。千餘年來,虐殺教徒,殘毒傾擠,甚至血戰百年不息,塗炭生靈。至於今日,各教各派,仍互相仇視,幾欲盡剷除異己者而後快。此與中國人之素習相反。今夫耶教不祭祀祖,又諸多行事,均與中國之禮俗文化相悖。耶教若專行於中國,則中國之精神亡。且他教可以容耶教,而耶教(尤以基督新教為甚)決不能容他教。(謂佛、回、道及儒(儒雖非教,然此處之意,謂凡不入耶教之人,耶教皆不容之,不問其信教與否而))。」(《吳宓與陳寅恪》,12頁)
陳寅恪的這種看法和當代多元文化的看法是一致的。各種文化不同的價值觀,生活方式只有互補的關係,沒有「好」、「壞」,「高」、「下」的區別。當然作為經驗問題,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現象是存在的。中國文化傳統與西方的區別,及互補性,在於它的最根本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以及由此決定的生存方式。
四、馮友蘭的紀念陳寅恪文,為甚麼看起來比後人的似乎深刻,原因在甚麼地方?馮友蘭前期做的很大部份工作還是學術,儘管是迎合世俗,後期做的則不僅是迎合,而且是被扭曲的「學術」。這是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區別,國民黨是可以「迎合」的,而共產黨就是「迎合它」也是有嚴格戒規的。馮友蘭、季羨林之輩,沒有錢鍾書、週一良那樣的運氣和聰明,熬了幾十年才熬到被「批准」「迎合」的地步。然而,這些被一般社會教育出來的人,是知道世界上真正存在一些甚麼,在該遮醜的地方,遮醜,還是不敢輕易夜郎自大,肆意胡來。這就是馮友蘭在紀念陳寅恪的文章中,提到陳寅恪堅持的究竟是甚麼而不敢過分放肆的原因。這本是一二三的事情,在後人看來「深刻」,就在於後人已經失去了這種能力,也就是我說的被閹割的一代。
陳來,蔡仲德是被閹割變性的一代,井底培養出來的一代人的典型,眼睛里根本辨別不出何為俗,何為真正的學品。所以馮友蘭在談陳寅恪的時候能夠把陳寅恪是何方神聖說清楚,而陳來、蔡仲德則根本不知道陳寅恪是何來之人。然而馮友蘭也僅此而已,要馮友蘭如陳寅恪寫王國維那樣,余英時解析陳寅恪那樣,則確實不現實也不可能。因為馮友蘭也罷,週一良也罷,如果他們能寫出紀念陳寅恪文章的精品來,他們也就不會是馮友蘭、週一良了。
孟子曰,「吾善養浩然之氣」。文章之氣並非是說來就來的,沒有的永遠不會有。文章之氣,是天才,是修養!馮友蘭、週一良,從做人、做學問看,當然不是四九年後,而是早就洩了氣的人。
最後我要加一筆的是,陳來的文字,八十年代初期我看過,感到平庸而無才氣,這次再看,比我留下的印象還差。如果把一個人的思維能力比喻一把刀,那麼陳來就根本連鈍刀都不是,而純粹是擀麵杖了。在思想領域中,他不是有沒能力庖丁解牛,而簡直可以說是□麵杖吹火問題。他對陳寅恪、馮友蘭、週一良的對比解釋,讓人哭笑不得。這樣的人如今據說是重建的清華國學研究院院長,與創院初旨相較,真的是南轅北轍!中國的學術看來是百年無望了!
祝好!
維光
2010-4-21
責任編輯:朱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