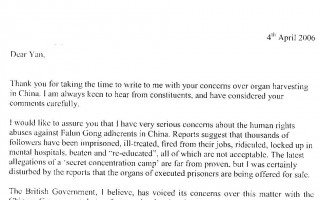【大紀元4月10日訊】「有法輪功嗎」?這是我2002年11月7日凌晨3點踏進北京市看守所204監區204監室的第一句話。此前的幾年間,法輪功信眾因堅守和平信仰而慘遭血腥鎮壓,被捕的修行者填滿了中共的勞改營、監獄、看守所和派出所。我非常希望見識一下這些稀有的勇於反抗的中國人,為她/他們所遭受的磨難作見證更是我的願望。我在秦城期間沒有遇到過法輪功信仰者。後來聽說在我被關進來之前1個月,秦城有一個長期絕食的法輪功反抗者被轉回了區看守所。兩個月後,我在北京公安醫院的地牢裡見到了此人。
他叫王甫,家住北京朝陽區勁松,30歲。據《明慧網》介紹,2000年10月1日,他和未婚妻李琦推遲了次日的婚禮,雙雙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的抗議。我的印象是,他此次被捕是因為參與了一次轟動北京的在建築物上懸掛橫幅的抗議,在鄉下躲避1年後被捕,判4年半,是十多人中判的最輕的。王甫從秦城轉回區看守所後,因再次絕食被轉進了公安醫院病犯區,一直關在B監室。
2003年1月17日,我開始了首次抗議恐怖主義絕食。絕食時間選在伊拉克戰爭開戰日,目標是100個小時。不僅因為對家人的擔憂,也出於對公然踐踏自定法律的暴政機構的痛恨。由於國保隊的關照,我不能像其他囚犯那樣得到家人的經濟援助,由此我判斷家人也被剝奪了至關重要的知情權,這會明顯加重家人的恐慌。獲釋後我得知,家人始終沒有收到我的逮捕證,也沒有被告知我的下落。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這類害人不利己的變態行為。看守所為了配合國保隊挖口供,也對我實施了嚴管,每天只配給4個乒乓球大小的玉米面窩頭,基本上處於半絕食狀態。這兩個多月的飢餓經歷對我以後的絕食有很大促動。因為營養極度不良,絕食第三天就出現了昏迷。
我被轉進病犯區C監室後,繼續尋訪法輪功。由同號處得知對面B監室關著一位。一天晚上,聽到一男子高聲抗議迫害法輪功,徹夜不息,我以為是對面B監室的法輪功反抗者在受刑。次日打聽出他的名字後,我向對面喊話表示問候。後來得知那次受刑的不是王甫,而是被關在B監室隔壁A監室的張雁斌(音),石景山人,在病犯區絕食4個多月。
以後我在衛生間遇到過王甫,他看上去像個「玻璃人」,應該是長期絕食和不見陽光的原故。
我第二次被關進病犯區是6月7日,這次抗議恐怖主義絕食的目標是「64」到「911」的100天。恰巧被關在王甫所在的B監室,他的絕食仍在繼續。我在43床,他在41床,對面40床是一位叫李連軍的死刑犯,殺4人,朝陽區雙橋人,30歲。他就是當初對張雁斌施暴者之一。當時他關在隔壁A 監室,和張雁斌鄰床。每個病犯都配發一個塑料尿壺。據李說,他曾逼迫被捆在床上的張雁斌「喝尿」,大概就是把尿潑到張雁斌的臉上。死刑犯都是上「搋」下「蹚」,手腳活動很不方便。而且死刑犯是地位最底下的刑事犯,這是七處在半步橋就形成的傳統。曾有一個看守當著我們一屋子人的面對李連軍講:「判了死刑,你就已經不是人了」。沒有看守的支持,死刑犯不可能對其他囚犯造次。
王甫的這次絕食是從中共十六大開幕的2002年11月8日開始的,與第一次絕食只間隔了一天。「吃朝陽,住海殿,既然關到朝陽,我得品嚐一下『朝看』牢飯的味道」,他主動吃了一餐牢飯。2003年6月21日,凌晨5時許,始終插著鼻飼管的王甫被來路不明的警察帶走了。睡意朦朧的同號們都為這個時間提犯人感到奇怪,或許是要轉送遠處吧。王甫的絕食方式是我所見最溫和的,他不拒絕輸液,每天還有一袋鼻飼奶,就是市面上常見的一元錢的「巴氏消毒袋奶」,但是會被其他囚犯分食,而負責鼻飼的護工也樂得清閒。王甫不僅從來不拒絕,而且主動詢問同號是否需要。他就是這樣在北京市公安醫院病犯區堅持了7個多月,過去的一年間,他只吃過一頓飯。不論他是否繼續絕食,此後他的處境都會更加凶險。
法輪功信仰者人數眾多,形形色色。我認為和王甫接觸過的人都能明顯感受到他的善良、平和,也不失機敏。這些或許都是他的天性,但是這至少說明法輪功信仰不會是「扭曲人性的邪教」。李連軍看不慣張雁斌把對師父的尊崇置於父母之上,在我看來這主要是中共「無神論」灌輸的惡果。另外,法輪功創始人是一位現實中的人物,他「突如其來」的影響力勾起了李連軍意識中的某種中國式的傳統情結。中國長期以來社會競爭秩序混亂,導致小人得志、惡人當道屢見不鮮,社會心理長期遭到扭曲,致使這種傳統情結異常頑固,以至於瀕死的囚犯也難以釋懷。
生活是各種行為,處於信仰的影響中。神是信仰的化身,不信神的無神論者也都有信仰。李連軍的信仰就包括了父母至上,父母就是他信仰中的神。我也信仰父母至上,還有許多人有這種信仰,那麼我們各自的神之間就可能存在著各種需要處理的關係,其中一部份處於法律之外。處理原則顯然必須超越各自的神,這就產生了共同的信仰,也就可能需要共同的神。對我們來說,自身的所愛能夠得到別人的認可和尊重顯然是重要的,所以在自由信仰中,作為信仰的化身,神有至高無上的名份,但是神的存在危害不到人們對父母的尊重,也不會分散對家庭的關切,在共同信仰的支持下反而會加深和擴展這種關切。
獨裁者要強行充當所有美好事物的化身,強行掌握所有權力,這就需要同時控制人們的靈魂和手腳。神的存在是獨裁者無上權威的威脅之一,獨裁者就必須醜化所有神,詆譭所有信仰。以近20年為例,大陸幾代人被灌輸過「五講、四美、三熱愛」,2004年,上海市在修訂《中小學生守則》時才率先加入了「孝敬父母」這一條,而且遠遠排在「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之後。獨裁者要求民眾信奉的不是無神論,而是「獨神論」,以此達到獨尊自己的目的。
有很多無神的信仰,也存在著很多被不同程度神格化的學說創建者和自然物。信仰是人的本能,作為信仰的化身,神可有可無,而剝奪其他信仰的「神」就是「魔鬼」。在宗教、學說等自由信仰中,信眾們擁有自由選擇的權利,而獨裁者卻用暴力手段把自身意志強加於所有人,即使內心不信仰它,行為上也要承認它的神聖。在我看來,法輪功信眾的反抗就是對這種自由權利的捍衛,對這種強加暴政的反抗,我理解、尊重和支持這類反抗。在此向所有不為外界所知的歷代暴政的反抗者們致敬。
在我被捕的387天裡,有200天是在北京市公安醫院地下的病犯區度過的,而且是從那裏獲釋的。我前後被送進病犯區3次,前兩次發生在絕食抗議期間,最後一次是釋放前突擊治療原因不明的浮腫。每次進來都會被不知情的人誤以為是法輪功,一來與眾多的法輪功反抗者相比,政治犯的人數實在微不足道;二來,相當一部份法輪功反抗者會進行絕食抗議,絕食抗議幾乎成了法輪功信眾的反抗標誌。
我相信在公安醫院所見到的法輪功反抗者屬於最頑強的一類。首先,非常頑強的反抗者大多會在北京進行抗議,而且只有在看守所堅持抗議而被折磨到奄奄一息的程度,才會被送進病犯監管區。當然,肯定還有相當多頑強的反抗者沒能來到北京,或沒有被送進病犯區,其中的一部份被屠殺了。曾有病犯區公職人員對我講過:「換個地方,一針胰島素就送命了,甚麼痕跡都沒有」。
我被關在20床時,隔壁是女囚室。那裏關押著一位非常頑強的法輪功反抗者 ——王晉香。不清楚她來自何處,曾多次轉押於病犯區和看守所。我經常能聽到她高聲抗議,勸說看守和醫護人員棄惡從善,當然也經常聽到她受刑時的慘叫。8月底的一天夜裡,我曾聽到監管科孔科長在隔壁喊:「王晉香,牙都打掉了,還鬧呢」。9月初,始終絕食抗議的王晉香又被轉走了,去向不明。經過我所在的囚室門口時,痿頓在輪椅中的王晉香努力轉過頭,向19床的法輪功老人示意。
王晉香所在囚室的對面囚室曾關押過一位從來沒有任何聲息的法輪功反抗者——張連軍,內蒙古赤峰人,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學生。他的生活、學業和整個家庭都被暴政輕而易舉地摧毀了,自身又深陷於無休止的折磨和變本加厲的羞辱之中,信仰堅定且性格剛烈的張連軍不堪侮辱和折磨,以頭撞牆,身負重傷。由於嚴重影響了治療,外科醫生明確要求監管科改善張連軍的關押方式。自身利益被觸動的看守和盡職的醫生發生了激烈的爭執,而這場衝突的始作俑者正在離病犯區1000多米遠的地方忙於裝扮「親民」形象。張連軍有時能吃點東西,也就一兩口的程度,從來不說話。由於是斜對門,我經常能看到被捆在8床上的張連軍,頭上纏著繃帶,牆上是大片的血跡。
病犯區還關押過一位絕食抗議的法輪功女大學生,小王。「師範大學」在校生,不清楚是北師大還是首師大。坐過牢的人大概都清楚,看報紙是很難得的享受。有時我能搞到一些報紙,主要是監管科的《北京日報》,護士室的《健康報》,以及看守在上班路上買的時報、晚報等。國際新聞版等敏感內容都被不厭其煩地抽掉了。有機會我會把報紙傳遞給一位沒有被嚴管的男法輪功囚徒,後來小王傳話過來說希望能看到報紙。她送回來的報紙裡夾著幾隻紙鶴用來表示謝意。每間囚室都有監控攝像頭,傳遞報紙的情況很快被監管科掌握了。那位男法輪功反抗者被調到了遠處的囚室,而有看守開始給小王報紙。有一天的《北京日報》頭版刊登了有關法輪功轉化成果的消息,小王看到了那份報紙。有使命感畸強的看守大光其火,認為黨報刊載的上述成果不適宜法輪功信仰者知曉,在監管科鬧出了一場風波。小王是我唯一能確定被釋放的法輪功反抗者。2003年10月21日下午,她換著便裝離開了病犯區。
病犯區還曾關押過一位叫劉雲的女性法輪功反抗者,年齡在60歲左右,北京人。她被指控在天寧寺附近的居民區散發法輪功傳單,案子是由宣武區檢察院起訴的。看守曾經徹夜捆綁劉雲,痛苦的呻吟通宵達旦。另有一位北京老太太,在中秋節前夜被關進了病犯區,連續多天被捆綁在床上。小王經常安慰她們,還給她們唱歌,因此遭到看守的嚴管。
我相信北京市公安醫院掌握著世界上最完備的飢餓症臨床資料。絕食反抗者病歷的病因一欄填寫的都是「重度飢餓症」。獲釋後,出於體檢和治療的需要,我曾嚐試複印自己的病歷,但是沒有獲准。被關進病犯區的法輪功反抗者也有因患重病送來急救的,病犯區和公安醫院急診科是一套班子。我遇到過一位這樣的法輪功反抗者,叫馬紅軍,北京人,很年輕。他判7年,妻子判9年。馬紅軍患的是某種「著色性肝脾病」,週身皮膚蠟黃。他不絕食,反而因為病因需要「大量進食」。他曾和張連軍同號關押過。
法輪功囚犯中也存在「歷史反革命」的情況。有一位72歲的北京老太太,早年就不再參與法輪功的集體活動了,但是因為和偶遇的前同修攀談了幾句,就被朝陽區國保隊關進了看守所。一段時間後國保隊決定釋放老太太,但是老太太已經被折騰出了一身病。家人要求國保隊負責給老人治病,國保隊就把老太太鎖到病犯區要挾。11月26日,無處申冤的老人帶著一身病回家了。
到此,我在北京市公安醫院病犯區(10病區)所接觸到的10位法輪功相關囚徒的記述結束了。感謝這些不為外界注意的暴政的反抗者,她/他們前仆後繼的反抗給了我坐牢期間最寶貴的收穫,這就是:中國還是有一些不怕坐牢的人,還是有一些不畏死亡的人。遭遇剝奪時敢於表達不滿,就是民眾為實現法治社會應盡的本分。反抗者的努力不可避免地惠及其他人,肯定有中國人不以為然,但是我相信每天經過內森。黑爾雕像的中情局僱員們能夠理解這些反抗,每年走進靖國神社的日本人敬重這些反抗。將來,這些反抗者的痛苦不應該成為任何人的交易籌碼。沒有人擁有代行他人寬恕權利的資格,哪怕是你的親人,因為你無法分擔他人的痛苦。如果反抗者被折磨致死,兇手就永遠不能得到寬恕。
尋找李毅兵先生@
3月25日
轉自民主中國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