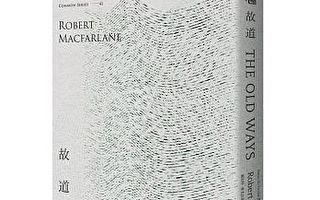「二○一四年,伊斯蘭國攻擊娜迪雅在伊拉克的村莊,於是,還是二十一歲學生的她,人生毀了。她眼睜睜看著母親和兄長被強行拖走處死,她自己則被伊斯蘭國戰士賣來賣去。她被迫祈禱,被迫盛裝打扮讓人強姦,一天晚上甚至被一群男人凌虐到不省人事……
但娜迪雅拒絕沉默。她反抗人生貼給她的所有標籤:孤兒、強姦受害者、奴隸、難民。她反過來創造新的身分:生還者、亞茲迪領導人、諾貝爾和平獎被提名人、聯合國親善大使以及新銳作家。」
——艾瑪·克隆尼(Amal Clooney,人權律師)
***
娜迪雅‧穆拉德 (Nadia Murad)
2018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伊拉克亞茲迪人。
娜迪雅歷經伊斯蘭國(ISIS)對亞茲迪族的種族滅絕及俘虜,成功脫逃後移居德國,現為人權運動者。獲首任聯合國人口販賣倖存者尊嚴親善大使、瓦茨拉夫哈維爾人權獎以及沙卡洛夫獎。
目前和亞茲迪族權益組織「亞茲達」(Yazda)合作,戮力讓伊斯蘭國為其種族滅絕和違反人性的罪行,接受國際刑事法庭審判。
她亦創辦「娜迪雅倡議」(Nadia’s Initiative),旨在協助種族滅絕及人口販賣的生還者治癒身心及重建社群。
***
我們等了幾天,納賽爾和我才成行。
我在那間屋子裡過得自在,但迫不及待離開摩蘇爾。
伊斯蘭國無所不在,我也確定他們正在找我。我可以想像哈吉.薩曼削瘦的身體氣得發抖,輕柔但恫嚇的聲音威脅要給我更多折磨。我無法再和那種男人待在同一個城市。
一天早上在米娜家,我在刺痛中醒來,發現身上爬著很多隻小紅螞蟻,我將它視為徵兆。在我們通過第一個檢查哨之前,我不會感到一絲真正的安全,而我知道我們可能根本過不去。
在我到達米娜家幾天後,納賽爾的雙親一早就到屋子來。
「是離開的時候了。」希山姆說。
我穿上凱薩琳的粉紅色和棕色連衣裙,然後就在準備出發前,才套上黑色的罩袍。
「我來唸一段祈禱文。」瑪哈對我說。
她態度和藹,所以我答應了,靜聽她說完那段話。然後她給了我一枚戒指。
「你說達伊沙搶走你媽的戒指,」她說:「請用這個代替吧!」
除了我從克邱帶出來還留著的東西,我的袋子也裝了這家人買給我許許多多的額外物品。在臨別一刻,我拿出狄瑪兒漂亮的黃色長連衣裙,送給米娜。我吻了她的雙頰,謝謝她收留我。
「你穿這件連衣裙一定很美。」我說:「那原本是我姊姊狄瑪兒的。」
「謝謝你,娜迪雅。」她說:「願阿拉保祐你平安抵達庫德斯坦。」
我不忍心看那家人和納賽爾的妻子跟他道別。
離開家之前,納賽爾把身上兩支手機的其中一支給我。
「我們坐計程車的時候,如果你需要什麼或有問題要問我,傳簡訊給我。」他說:「別開口說話。」
「我怕我在車裡坐太久會吐。」我提醒他。
於是他去廚房拿了幾個塑膠袋給我。
「用這些吧。我不希望我們停下來。」
「在檢查哨時,不要顯出害怕的樣子。」他繼續說:「盡可能冷靜。我會回答大部分的問題。如果他們問你話,簡短回答就好,音量小一點。只要他們相信你是我的妻子,就不會要你說太多話的。」
我點點頭。
「我會盡力。」我說。
我已經覺得自己可能害怕到昏倒了。納賽爾一副若無其事,他好像天不怕地不怕似的。
大約上午八點三十分,我們開始一起走向幹道。我們要招一輛計程車載我們到摩蘇爾的計程車行,另一輛納賽爾事先叫好的計程車已經在那裡等候,準備載我們到吉爾庫克。
人行道上,納賽爾走在我前面一點點,我們沒有交談。我低著頭,盡量不看經過的路人,深怕我眼中的恐懼會立刻洩露我是亞茲迪人。
那天很熱。米娜的鄰居在給草坪澆水,試著救回枯死的植物,孩子則騎著彩色的塑膠腳踏車在街上衝來衝去。那些聲音嚇到我了。在屋裡待了這麼久,明亮的街道感覺十分凶險,毫無遮掩、危機四伏。
我在米娜家等候時嘗試鼓起的希望蕩然無存。我確定伊斯蘭國會追上我們,我會被抓回去當薩比亞。
「沒問題的。」
當我們站在幹道的人行道上等計程車出現時,納賽爾輕聲對我說。他看得出來我擔心受怕。
一輛輛汽車快速掠過,使我黑色罩袍的前緣覆上黃色的細沙。我抖得好厲害,以至於在我們叫到計程車時,我幾乎無法使喚自己的身體進車裡去。
在我腦海盤桓的每一個腳本,結局都是我們被捕。
我看到我們的計程車在公路邊拋錨,我們被滿載好戰分子的卡車接走。我看到我們在渾然不覺中經過一枚土製炸彈,在路邊奄奄一息。我想到所有家鄉認識的女孩、親人、朋友,她們現在四散伊拉克和敘利亞各地,想到我那些被帶去克邱學校後面的哥哥。
我回家後可以找誰呢?
摩蘇爾車行擠滿要叫計程車載他們去伊拉克其它城市的民眾。男人跟司機討價還價,妻子靜靜站在一旁。男孩兜售冰涼的瓶裝水,周邊小販兜售銀色包裝的洋芋片和糖果,或驕傲地站在精心疊起的香菸塔旁。
我懷疑車行裡有沒有女人跟我一樣是亞茲迪人?我希望她們全部都是,而那些男人都跟納賽爾一樣,正在幫助她們。
車頂有小型標誌的黃色計程車,在周知目的地的招牌底下停車或怠速:塔阿法、提克里特(Tikrit)、拉馬迪(Ramadi)。這些地方全都起碼部分被伊斯蘭國控制,或受恐怖分子威脅。我的國家有好多領土現在歸那些奴役我、強暴我的男人所有。
計程車司機在為行程做準備時,一邊跟納賽爾聊天。我坐在離他們稍遠的長椅上,試著扮演好納賽爾之妻的角色,聽不清楚他們說些什麼。
汗流進我的眼裡,使視線朦朧,而我把袋子緊緊抓在腿上。那個司機將近五十歲。體型不碩大,但看起來很強壯,還留了小鬍子。我不知道他對伊斯蘭國是何感覺,但我每個人都怕。
在他們協商期間,我試著勇敢,但很難想像我沒有再次被捕的結局。
最後納賽爾點頭要我上車。他坐在司機旁邊,我爬進他身後的座位,把袋子輕輕放在身邊。車子開出車行時,司機隨手玩他的無線電,尋找頻道,但每個頻道都只有靜電干擾,他嘆了口氣,關掉它。
「今天真熱,」他對納賽爾說:「我們先買點水再上路吧!」
納賽爾點點頭,於是一會兒後,我們停在一家報攤前旁,司機去買了幾瓶冰水和幾包餅乾。納賽爾拿了一瓶水給我。
水從瓶子邊緣滴落,積在我旁邊的座位上。餅乾乾得難以下嚥;我試了一片,只是想擺出輕鬆的樣子,餅乾卻像水泥一樣卡在喉嚨。
「你們為什麼要去吉爾庫克?」司機問。
「內人的家人在那裡。」納賽爾回答。
司機從後照鏡看著我。我一對到他的眼,就撇過頭去,假裝為窗外的城市神魂顛倒。我相信我眼裡的恐懼會出賣我。
車行周邊的街道處處可見好戰分子。伊斯蘭國的警車就停在路邊,警員沿人行道巡邏,槍插在腰帶。那裡的警察似乎比老百姓還多。
「你們會待在吉爾庫克還是回摩蘇爾?」司機問納賽爾。
「我們還不確定。」納賽爾說,完全按照他父親的吩咐:「要看到那裡要花多久時間,還有吉爾庫克的情況。」
他問那麼多幹嘛? 我想。我很慶幸自己不用說話。
「如果你願意,我可以在那邊等,載你們回摩蘇爾。」司機告訴我們。
納賽爾微笑以對:「或許可以唷!」他說:「到那邊再看看。」
第一個檢查哨在摩蘇爾轄區內,是像蜘蛛一樣的龐大建築,由高大的柱子支撐金屬屋頂。這裡曾是伊拉克軍方檢查哨,現在則驕傲地展示伊斯蘭國的旗幟,而曾屬於伊拉克軍隊、現歸伊斯蘭國的汽車,停在一間小辦公室前面,車外也插滿黑白旗。
我們停車時,有四名好戰分子當值,從他們躲避炎熱、填寫文件的白色小崗亭出來外面工作。
伊斯蘭國意欲控制所有進出摩蘇爾的交通。他們不只要確定沒有反伊斯蘭國的戰士或偷運者進入城市,也想知道誰離開了,以及離開多久。如果叛逃,伊斯蘭國會處罰他們的家人。最起碼,好戰分子會榨乾他們的錢。
前面只有寥寥幾部車在排隊,我們很快就接近其中一名衛兵。我開始控制不住地發抖,覺得眼淚就要奪眶而出。我愈想用意志力逼自己冷靜,就抖得愈厲害,而我相信那一定會洩漏我的身分。
也許我該逃跑,我想,而當我們慢下來,我將一隻手放上門把,準備在必要時跳車。當然,這其實不算選項。我根本無處可逃。車的一側,燠熱的平原綿延無盡,另一側,也就是我們在身後的,是我亟欲逃離的城市。好戰分子監視摩蘇爾的每分每寸,要追上徒步逃走的薩比亞根本不費吹灰之力。
我祈求神,別讓我被捕。
納塞爾從側鏡看著我,感覺到我很害怕卻不能跟我講話。他臉上閃過微笑,要我冷靜下來,就像在克邱時凱里或我媽那樣。沒什麼能阻止我心狂跳,但至少我不再幻想跳車這件事了。
我們停在其中一座衛兵崗亭旁,我看著門打開,一名全副伊斯蘭國制服的好戰分子踏了出來。他看起來跟那些來伊斯蘭國中心買我們的人沒什麼兩樣,所以我又開始嚇得發抖。
司機搖下車窗,那名好戰分子彎下身子。他看一看司機、看一看納賽爾,然後瞥了我和我旁邊的袋子。
「Salam alakum,」他說:「你們要去哪裡?」
「先生,我們要去吉爾庫克。」納賽爾說。
他把我們的身分證從車窗遞出去:「內人是從吉爾庫克來的。」
他的聲音毫無顫抖。
好戰分子拿走身分證。從崗亭打開的門,我看到一把椅子和一張小桌子,桌上有一些文件和那名好戰分子的無線電。桌子一角,一部小電扇輕輕地旋轉,桌邊則有一瓶幾乎喝光的水搖搖晃晃。然後我看到了。
和其他三人的照片一起掛在牆上的,是哈吉‧薩曼強迫我改宗那天,我在摩蘇爾法院大樓拍的相片。那底下寫了幾句話。距離太遠,我看不到那寫什麼,但我猜那列出我的資訊,以及如果抓到我要如何處置。
我輕輕倒抽一口氣,很快掃視其它三張照片。其中兩張因為反光我看不清楚,剩下一張則是我不認識的女孩。她看起來年紀很輕,而跟我一樣,她的恐懼躍然臉上。
我移開視線,不想讓好戰分子發現我盯著那些照片,那一定會讓他起疑。
「你們去吉爾庫克要見誰?」衛兵還在問納賽爾,幾乎沒注意我。
「內人的家人。」納賽爾說。
「要去多久?」
「內人會待一個禮拜,我今天就會回來。」他說,按照我們排練的腳本。
他聽起來毫不畏懼。
我不知道納賽爾從座位能否見到我那張懸掛在崗亭裡的照片。我相信如果他看得到,就會要我們回頭。見到我的照片證實伊斯蘭國正積極地尋找我,但納賽爾只是繼續回答問題。
衛兵繞過來我旁邊,示意要我搖下車窗,我照做,同時覺得我可能會害怕到昏倒。我記得納賽爾的勸告:保持冷靜,盡可能平靜簡短地回答問題。
我的阿拉伯語相當完美,我從很小就開始說,但我不知道自己的口音或用字會不會洩露我其實來自辛賈爾,而非吉爾庫克。伊拉克是個大國,你通常可以從對方說話的方式判斷他在哪裡長大。我不知道吉爾庫克出身的人該怎麼說話。
他彎下身子,透過車窗看著我。我很感激面紗遮住我的臉,而我試著控制我的眼睛,不要眨得太多或太少,當然,無論如何,不可以哭。在我的罩袍裡面,我汗流浹背,但仍害怕得發抖。但我在這個衛兵眼鏡裡的形象仍是一般穆斯林女性的模樣。我坐直起來,準備回答問題。
問題很短。
「你是誰?」他的音調很平,一副很無聊的樣子。
「我是納賽爾的妻子。」我說。
「你要去哪裡?」
「吉爾庫克。」
「為什麼?」
「我家人在吉爾庫克。」
我輕聲回答,視線放低,希望我的恐懼會被當成端莊,我的答覆聽起來不像排練過。
衛兵直起身子,走掉了。
最後他問司機問題:「你是哪裡人?」
「摩蘇爾。」司機回答,聽起來這個問題已經回答過一百萬遍了。
「你在哪裡工作?」
「有錢賺的地方啊!」司機咯咯笑著回答。
然後,衛兵不再說話,從車窗交還我們的身分證,揮手要我們通過。
我們開過一條長長的橋,沒有人說話。橋下,底格里斯河在陽光下波光粼粼。蘆葦等植物緊挨著河水;它們靠得愈近,就愈可能生存。離開堤岸,植物就沒那麼幸運了。它們會被伊拉克盛夏的豔陽烤焦,只有少數得到住民細心灌溉,或從降雨汲取一些水分的,春天會再發芽。
我們一抵達河的彼岸,司機就說了:「我們剛過的那座橋,可是布滿土製炸彈呢,」他說:「是達伊沙設置的炸彈,以防伊拉克或美國人試圖收復摩蘇爾。我很討厭過那座橋。我覺得橋好像隨時會爆炸似的。」
我回頭看。橋和檢查哨都愈退愈遠了。我們活著通過兩者,但結果是可能截然不同的。檢查哨的伊斯蘭國好戰分子可能問我更多問題,可能從我的口音聽出什麼,或注意到我的舉止有什麼可疑之處。
「下車。」
我想像他這麼說,而我別無選擇,只能照他的話做,跟著他進入崗亭,而他會命令我掀開面紗,讓他看到我就是相片裡的那個女人。我想到橋可能在我們通過時爆炸,土製炸彈把我們的車子炸個粉碎,讓我們三人當場斃命。我祈禱,當那座橋真的爆炸時,上面都是伊斯蘭國的好戰分子。◇(待續)
——節錄自《倖存的女孩》/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責任編輯:余心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