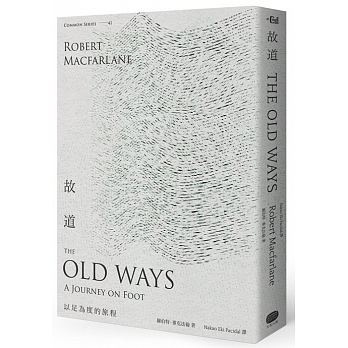追隨
人是動物,跟所有動物一樣,凡走過便留下足跡,在雪上、沙上、泥濘上、草地上、露珠上、土地上、青苔上,留下行過的痕跡。
狩獵術語中有個頗具啟發性的詞彙,可以形容這類印痕——嗅跡(foil)。生物的嗅跡就是足跡。但我們很容易便忘卻自己本是足跡創造者,只因如今我們多數的旅程都行在柏油路或混凝土上,而這些都是不易壓印留痕的物質。
克拉克(Thomas Clark)在雋永的散文詩〈行之頌〉裡寫道:
「人無時無處不行走,於地表錯綜劃下可見與不可見之徑途,或對稱,或曲折。」
確實,一旦開始留心便會發覺,大地依舊織滿徑途與行跡,在現代道路網上投下陰影,與之或斜切或直交。朝聖之途、林蔭之路、獸群之道、殯葬之徑,踏境、牧地、溝堤,夾道、鋪道、籬徑——將途徑之名朗聲快速唸出,它們便成詩歌、成儀式——沉徑、白堊步道、引水道、趕牲道、抬棺道、騎道、馬徑、貨徑、橋道、堤道、戰道。
許多地區依然保有舊道,連結一地與一地,導引人通過關塞,繞過山陵,來到教堂或小禮拜堂,行至河流或海洋。它們的歷史未必都快樂。
愛爾蘭有千百公里長的飢饉之路,是一八四○年代的饑荒者所建,不過連結的是空無與空無,所得回報甚薄,未曾載入全國地形測量局的地圖。
荷蘭有死亡之路和鬼魂之路,兩者交會於中世紀的墓園。
西班牙不僅有至今尚在使用的廣泛趕牲道網路,也有長達數千公里的聖雅各伯巡禮路,是前往康斯波特拉聖雅各伯的朝聖路徑。對走在巡禮路上的朝聖者來說,每一步都具有雙重意義:同時落腳於現實的道路與信仰的旅途。
蘇格蘭有疊石道與棚屋道,日本則有狹窄的鄉野步道,是一六八九年詩人松尾芭蕉寫作《奧之細道》時所行過。
十九世紀,寬廣的「野牛道」縱橫美洲草原,是成群的野牛驅趕多種獸類時所留下,早期移民以之為途,向西挺進,橫斷北美大草原。
歷史悠久的路徑存在於水上一如在於陸上。
大洋海道密布,途徑為風向和洋流所決定,而河流也躋身最古老的道路之列。在嚴冬月份,要進出印度喜馬拉雅山區偏遠的桑噶爾谷地,唯一的途徑是一道冰封河流所形成的冰道。
這條河下落穿過兩側陡峭的泥岩山谷,其險坡是雪豹狩獵之處。此處的深潭之冰既藍且澄。沿河而下的旅程叫做chadar,踏上chadar之旅的人雇航冰者為嚮導,他們經驗豐富,清楚何處有危機潛伏。
不同的徑道自有其不同的性格,端視地質和目的而定。
坎布里亞郡有些棺道在上坡那一側置有扁平的歇憩石,可供抬棺者卸下重擔,甩甩疲憊的雙臂,聳聳僵直的雙肩。
愛爾蘭有些棺道有嵌壁式的歇憩石,可供弔唁者在石上的凹槽安置卵石。
英格蘭白堊丘上的史前道路歷經多少世紀的踩踏,土壤變得緊實,其上雛菊繁生,欣欣向榮,因此路徑至今可辨。
在外赫布里底群島的路易斯島,成千上萬的工作道路在苔地上刻出縐痕,從空中俯瞰,外觀有若岩羚羊皮。
此外我還想到蘇格蘭高地山徑間的之字形紋理、〔英格蘭東北部〕約克郡與威爾斯中部地區滿布旗幟與橋樑的駝馬徑,以及(英格蘭東南部)罕布郡那沒入水中的綠沙徑。綠沙徑上,羊齒蕨類植物自成蔭的堤岸中湧現,蜷曲一如宗教牧杖。
標示古道的活動本身便是一種不傳之祕,牽涉到疊石、灰色風化石、史前沙岩巨石、地界標、立長石、里程碑、巨石圈以及其他的引路標。
在達特摩爾的沼澤地區,標示路徑的白瓷碎片讓人們在晨昏時分得以安全行走,有如童話故事裡韓森和葛莉特的卵石小徑。
山區鄉間的巨礫通常指向可以涉水而過的淺水地帶,例如紅山山脈的烏茲石,標示著摩爾溪可以涉水抵達傳統牧地之處,由是而來到雕刻靈動的岩畫前,每當黃昏的日光拂過岩石,馴鹿便躍然欲生。
長久以來,路徑與路徑標示者一直誘惑著我,將我的眼光引而向上向內向遠方。雙眼受路徑的誘引,心眼亦如是。
想像力無法不去追索地上的線條。線條在空間裡向前延伸,卻在時間裡向後回溯其作為路徑的種種歷史,及其之前的諸多追隨者。
走在路上,我常好奇道路的由來,揣想是什麼樣的衝動導致路的創生,思索因路的存在而衍生的慣常旅程,以及道路所保存的關於冒險、相遇和啟程別離的各種祕密。
我在至今為止的人生當中,在步道上大概已經走了上萬公里,或許比多數人多,但與某些人相比卻還相形見絀。
德昆奇(De Quincey)曾揣測說,華茲華斯一生大概走了二十八萬公里路。他那名聞遐邇的虯結雙腿,被德昆奇惡毒地形容為「所有……女性鑑賞家都會認為是遭遇了嚴厲天譴」,但在行走及負重時,這樣的小腿何其可敬。
就我記憶所及,我已經步行了數千公里,只要一失眠(其實夜間我多半失眠),我就把自己的心智送去重溫舊路。有時候我就這樣慢慢踱入夢鄉。
克萊爾(John Clare)對田野小徑的形容很是簡樸:「它們在我前進時帶來喜悅。」於我心有戚戚焉。
惠特曼在《草葉集》裡宣稱「我的左手攬著你的腰,我的右手指向大陸地景,以及平凡無奇的公共道路」,口吻既友善又情色,此外還頗為強橫。
若取「凡塵」(worldly)一字最好的意義,「步道」可謂具有其中的世俗性,向所有人敞開。道路權以使用為界定的依據,也因使用而得以存續,這些權利構成一種自由的迷魂陣,是公共土地上纖細的網路。
我們的世界之私有化,其方式頗具侵略性,處處是電纜、閘門、閉路電視攝影機和「不得擅入」的告示牌,而將這樣的世界串連起來的便是那迷魂陣。
這種迷魂陣,是不列顛和美國在土地利用方面的重大差異。美國人向來羨慕英國的小徑系統及與之伴生的自由,一如我艷羨斯堪地那維亞的慣習權(Allemansrätten,字義為「每個人的權利」)。
這種慣習誕生於不曾經歷數世紀封建統治的地區,故而並不臣服於某種地主階級。於是,只要不造成損害,公民可以隨意走上未經開墾的土地,可以生火,可以在有人居住的宅邸外的任何地方安睡,可以採集花朵、堅果和莓果,可以在任何水道游泳。
蘇格蘭近來終於開竅的「進接權法」(access laws)可謂越來越接近這種權利。
路徑是大地的習性,是兩廂情願的造物。創造自己的步道並非易事。
藝術家隆恩(Richard Long)曾經有此嘗試,他轉彎數十次,踩出一條進入漠地的僵硬直線。但那是足跡而不是步道,除了自己的終點便所向無處。
隆恩那種走法像老虎在籠內踱步,也像泳者來回游動。既然沒有延伸的指望,隆恩的線條便有如斷枝之於樹木。
道路乃是彼此相連的存在,連結是道路的首要之務,也是道路存在的主因。就字面意義而言,道路連結了地方,而在引申意義上,道路更進一步連結了人。◇(待續)
——節錄自《故道:以足為度的旅程》/大家出版社
【作者簡介】
羅伯特·麥克法倫(Robert Macfarlane)
才氣縱橫的英國劍橋文學院士,被視為新一代自然寫作及旅行文學的旗手,也是英國史上最年輕的布克獎評委會主席。《故道》一書曾獲「多爾曼旅遊寫作獎」(Dolman Prize for Travel Writing)。
責任編輯:李昀
點閱【故道──以足為度的旅程】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