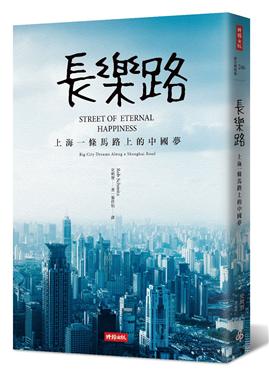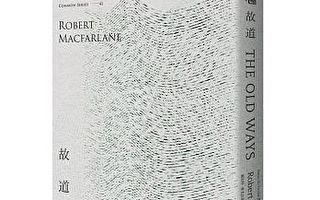第一章 CK及体制:长乐路八一○号
长乐路长约三公里,当交缠的路树枝枒在冬日落光叶子,你就能穿过枝干看到远方这座城著名的天际线:金茂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上海塔。这三大巨人矗立在比邻的几个街区,每一栋都比纽约的帝国大厦还高。
路树底下的人们却忙到无暇欣赏此景。
在长乐路中段的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里,许多新生儿展开了人生的首日;长乐路西侧的华山医院急诊室中,许多人则度过了人生的末日。
两院间的这段则是形形色色的生活:一个蓄胡的乞丐坐在街边吹竹笛,情侣手牵手经过他,一堆车子被堵住围着两个男人按喇叭,两人互啐口水争论到底谁撞到谁,穿制服的学生聚在一旁围观,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为了荔枝的价钱嫌恶地吼着一个小贩,至于其它区段则是被川流不息的人潮推着走,不时传来一阵阵肉包摊的咸香及车流废气的苯甜味。
这里的生活喧闹、脏乱,又生猛。
地图上的长乐路不过是上海中心人民广场西南侧一条弯弯曲曲的细线。我家就位于这条细线的西侧。
从我家望出去便是树冠,两层楼高且几乎终年成荫。在那底下唯一立定不动的生命只有这些树。有许多早晨我绕着这些树干迂回前进,从人行道走上路面再回来,身处争抢树荫的行人之列。
中国少有街道像这里一样种满路树。
到了周末,当地工人的扰攘被中国各地的游客取代,他们用长焦镜头捕捉这两排枝干,欣赏其中的异国风情。
这些树是在十九世纪中期由法国人所种下,当时欧洲人和美国人正瓜分此城为租界。近一个世纪后,法国人离开,树却留了下来。日本人曾轰炸上海,一度占领了这座城市,但最终是撤退了,留下这些法国人种的树毫发无伤。接着是毛泽东带领的共产党发起革命,阶级斗争,数百万人英年早逝。树却长存无碍。
这条街现在充满资本主义,两侧满是餐厅与各式店家,当我在人行道上漫步,偶尔会从关闭的闸门缝隙中瞥见倾颓的欧式家屋,心想这条街目睹了多少历史的残酷动荡。
此地犹如一朵帝国玫瑰,凋落后又重新绽放。
始终屹立的只有这些树。
在这条街上住了将近三年,我才注意到陈凯的三明治屋。这家店距离我的公寓不到一个街区,在一间很小的衣饰店楼上,且在温暖的夏天,几乎整间店都被茂密的梧桐树挡住。
从狭窄的螺旋楼梯走向二楼,首先会看到整片落地窗,窗外一整片枝叶摇映,将底下上海市的喧嚣隔绝开来。
陈凯(音译)──他总自称CK──有时会弯著身体在柜台工作,一头蓬乱黑发几乎盖住眼睛,细瘦手指正在为一份三明治或甜点收尾,然后甩开额前鬃毛般的发丝,转身以机械化的动作从义式咖啡机为顾客挥出一杯滚烫的咖啡。
不过店面通常空无一人。
“没关系,生意起步需要时间,梦想都是这样的。”他如此告诉自己。
每当此时他就会颓废地坐在吧台高脚凳上,长满青春痘的孩子气脸庞背对满是树影的落地窗。他讲电话时会切换不同中国方言,为副业谈生意:他还兼差卖手风琴。
他之所以想开三明治屋,是在芝加哥光顾过一家之后。那是他人生唯一的一次美国行,对美国人而言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却让他印象深刻,因而想为中国的外食客户提供类似体验。有点像是来过中国的美国人深受小面摊启发归国一样。
这种看似冲动的做法,这条街上我认识的很多店主却都是如此。身处上海这样富裕的大城市,只要有心几乎什么都能卖。
CK梦想有一天能靠这间带有艺术气息的二楼三明治屋维生。他投入多年贩卖手风琴攒到的存款,和一个朋友合资共同打造了这个空间,希望吸引跟他们一样的年轻音乐家和艺术家前来。
“某天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说不定我能把这些人聚集、团结在一起。我想寻找那些想要挣脱体制的人。我想要同类的朋友;那些对艺术、时尚设计或其他不同产业有独立想法的创业家。”他告诉我。
很多人有着与CK类似的野心,在长乐路散步于是成了一趟惊人的体验;狭窄的街道两旁满是与CK店面类似的小店和咖啡馆,双眼明亮的异乡人带着梦想争奇斗艳,都想在这座大城市追求成功。
成功可不容易。CK和朋友Max都没有在餐厅工作的经验,更别说是经营。他们相识于一家前法租界区的古董相机店,当时CK为了学习摄影在那里打工。如同CK,Max也拥有创业家背景;经过多次搭班的长谈,两人都欣赏彼此制造及销售商品的生意手腕。最后CK说服了Max与他合伙开一间三明治屋。
每当走在这个新定居的街区中,我总借着诵念这些听起来喜气的路名来练习中文,像是安福路、永福路、宛平路。我所居住的(路名)大概是听起来最喜气的一条:长乐路,代表“长久的快乐”。
他们把店面命名为“你的三明治屋”,距离一个繁忙的地铁站只有两个街区,旁边就耸立了一栋四十五层高的大楼,每天中午总有数百名上班族从大楼内涌出,寻找一顿能快速解决的午餐。但没人能看见这间被梧桐树挡住的“你的三明治屋”,没人在匆匆走过长乐路时抬头透过树冠望见他们。
所以他们把店名改成“二楼”,暗示路过行人抬眼看看他们。新店名底下以低调婉约的字体写了“你的三明治屋”。他们雇用一位新主厨,也打造一座提供多种饮料及进口啤酒的吧台,而且异常执迷于在菜单上玩花样。
某天我顺路拜访CK的公寓,看到角落堆放一叠电子平板,“触控式菜单!”CK微笑着对我说。他想必觉得,无法互动的枯燥菜单正是吸引不了i世代年轻人的原因。
他在销售手风琴的事业上快速赚了不少钱,但作为餐厅经营者实在天真。
此地的午餐食客通常是要辛苦挣房租的上班族,他们追求的是便宜的在地食物,通常也宁可选择使用筷子入口的熟食。接下来几个月,CK得努力适应这项现实。
他开始提供价格亲民的午间特餐,也稍微将三明治的价格调低。不过他自始至终都不担心这间快餐店的命运,毕竟销售手风琴的获利稳定。此外,他觉得能在自己住处同时处理两项事业非常幸运,如同一只懂得运用资源的松鼠为了过冬在自己的舒适树屋中囤满坚果。
这间三明治屋可说是避难所中的避难所。◇#(待续)
——节录自《长乐路:上海一条马路上的中国梦》/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作者简介】
史明智(Rob Schmitz)
旅居中国二十年的美国记者,勾勒当今中国面貌。横跨三个世代,在上海一条马路上共筑中国梦。每个真实人生故事,都是当今中国百姓的希望与哀愁。
责任编辑:李昀
点阅【长乐路:上海一条马路上的中国梦】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