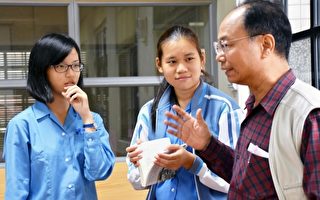每天都有晴好的太阳,爸爸可从床上下来,挪到屋檐下的阳光地里,盖上棉被躺在藤椅上。他整个人都瘦了,面上和身架皆骨头支棱。肤色倒白皙了些,双目黑亮沉郁,瘦成了新的。
爸爸常常温柔地、久久地注视着门前的长河,水上结着一层薄冰。田野里生着青绒绒的麦垄。他对兄弟俩说:“你们的爸爸不会成残废人了!我感觉到身上的骨头正在长拢。过了年,我肯定就能走路了。”
大年初一早上,爸爸给霄霄和乔乔赏了一个红纸包的压岁钱。妈妈和祖母,也各有一份。老的小的,接过压岁钱时的喜悦表情,令爸爸生出无言的欣慰。正月里的头几个日子,家里都有朋友们来喝酒,妈妈在厨房里切卤菜,煎鱼,温酒,做火锅。兄弟俩放了心,便又心安理得地欢活起来,和台上的伙伴们聚集在一起,带着烟花、火鞭、万花筒,冲天炮。去远远的田野上放爆竹,放野火烧荒,烤红薯和玉米,从家里偷出来的腊香肠,野鸭和米糍粑汇合,伙伴们聚餐。夜晚在荒沟里点燃的野火,红焰腾腾的,烧红了半个黑夜。孩子和家养的黄狗成群结队地在台上出出入入,气势扬扬,呈天不管地不收之态。
过完了元宵。天上下起了濛濛的雾雪,气温反倒比腊月里冷了。打工的人们就在这样的天气里,背着一床棉被出门去了。爸爸坐在屋檐下,和他们一个个地打招呼。男人们问道:“黑狗,你不出门了吗?”
爸爸轻松地说:“不打算出门了,我打算就在家里种地。”他招呼他们“进来坐一会儿,赶路也不迟。”那些人就放缓了步子,他们将行李搁在窗户底下,拿椅子坐在屋檐下。
“黑狗,其实谁他娘的想出门呢?谁不想在家里守着田亩老小,舒舒心心过日子?在家里终归没人欺负你把你不当人罢?可是,出门到外面打工终归是条养家的路。”
“种地真是种伤心了,棉花也贱,稻谷也贱,辛辛苦苦地耕地薅草,倒搭上肥料农药,日他娘到头来一样都变不出钱来。在城市里哪怕拣荒货捡垃圾,都比家里种十亩地强。”
爸爸陪着他们叹气:“是啊,谁说不是这回事呢?出门在外没一天不受气受累的,就仿佛乡下人都不是娘养下来的。”然而,他说:“可田里的地总是要有人来种的。再说,我出门也真是伤心了。再不出门了。”
他的朋友们就嘲讽道:“等着吧,你种一年地,倒莫名其妙欠他娘的一身的款项。都是驴打滚的利息。”
黑狗笑一笑,叹口气,双方都沉默着说不出话来了。他们抽着烟,望着长河里破冰的绿波荡漾的春水,田野的油菜花开成了黄灿灿的无涯的花海。一只船从远方突突突地驶来了,上头已经坐了许多出门的民工,爸爸的朋友们赶紧招手,招呼船泊到木粜边,他们背起了行李,紧一紧裤腰带,往河畔走,回头又对潘清波挥挥手,道:“黑狗!你留在村里,我们在外头到底还安心些。从开春起,我们的女人就都归你照看了。田亩也都归你耕啦!我们到年底再回来接管。”
黑狗听了,畅快地笑起来,大方地应承道:“你们安心走吧,走吧!田亩,女人,我样样都伺候得好好的。”
“要比狗日的四黑子伺候得好!别他娘的光调戏不耕地!”
黑狗挥挥手道:“走吧走吧,你们只管平平安安地发财去吧!”
陆陆续续几天间,台上人家就走了大部分,有些全家都出门去了,房子一把锁便锁上了。台上的鸡狗成群地在禾坪菜园里撒欢,飞上稻草垛,几日便有了颓败之势。春雨里,那些无人踩踏的屋檐下台阶上,迅疾地衍生出一层绒绒的青苔。潘渡依然只剩下老人和上学的孩子,长河边的村庄,寂寥得连历惯风霜的老人们都觉出了荒凉,老祖母说,她这辈子从没看过台上人家会这般稀少,越来越少了。
然而,生活还在继续,惊蛰一到,土就动了,天空轰隆隆地春雷。二月里是神社日。二月初一“晒土地”老人们组织了一个香火社,原野上的土地庙,红布神龛上蒙着的一尊眼睛咪咪胡子老老的土地菩萨,一村的孩子都来给土地爷磕头了,乞得智慧和福气。也保佑潘渡今年的收成会风调雨顺。二月十九日,要拜观世音菩萨。锣鼓香火里,村庄渐渐地从离别的伤痛里缓了过来。春雨里有农夫披着蓑衣,赶着牛下田耕地去了。豌豆花开了,紫朦朦地镶在油菜花海里。劳作了一个新年的妈妈,这回独自一人清清爽爽地乘船回下江娘家去了,她要去接外婆来家里住些日子。
爸爸在饭桌上对儿子说:“今年,我们家可能要种大约六七十亩地了。别人家扔下荒废了的地,爸爸都拣起来种。全部种黄麻和棉花。”
爸爸说:“我要骑着摩托车,去城里驮化肥回来。”他对霄霄和乔乔说:“你们俩个就坐在前面。嘟嘟嘟—–”
“我要买水彩笔,图画册。”霄霄文静地垂着眼皮说。
乔乔问道:“如果妈妈也想去呢?”
爸爸笑眯眯地:“就让她一个人在后面走着好了。”
夜晚,霄霄和乔乔骑在桑树的枝桠上。过年时热闹喧哗的潘渡,人家的灯火只亮起一小半。许多的房屋都黑黝黝地静立在台上。兄弟两个躺在树枝上,心里依然觉出一些凄清的凉意来。乔乔说:“霄霄,我一点都不想上学了,你呢?”
霄霄因为成绩好,在这一个问题上是很势利的。他思考了一下,回答说:“我觉得,学是一定要上的。不上学,这么小,能做什么呢?”
乔乔说:“我想在家里帮爸爸下地干活。我喜欢玩。”他兴奋地憧憬,天就该温暖起来了,在花海般的田野上,香暖的春风吹拂,绿茸茸的庄稼,水田埂下随便掏一个洞,就能捉到泥鳅。夜里提着马灯去捉青蛙,呱呱呱呱!不用上学,该多么自由!
乔乔说:“我打算养一棚鸭子,像念珠儿家一样。”
霄霄说:“可是你的鸭子会和她的鸭子搞混。一搞混的话,她就要骂你了。说不定要拿竹篙把你的鸭子拍个半死。”他一想起念珠儿来,就心有余悸地摇着脑袋:“我最怕那个烂嘴巴丫头了,她简直越来越会骂人了。”
乔乔满不在乎地摇摇头:“不要紧,她要是骂我,我就骂她。”
霄霄很不屑地对弟弟说:“你怎么可能骂得赢她呢?”
乔乔说:“慢慢就骂得赢了。”他扬扬拳头,说:“她很怕我打她的。”
霄霄听到这句话,出了一会儿神,半响他才说:“总之,我和谁都不喜欢相骂,也不喜欢打架的。不管打赢了还是打输了,心里终归觉得很难过的样子。我就想上学读书,将来考上大学。”
乔乔敏感地说:“可是,爸爸说大学都是在大城市里的。大城市里的人是很欺负人的,他们动不动就会打你。”
霄霄像一个胸怀抱负的人那样,宽容而温和地一笑:“不会的。上大学的人是有用的人才。只有像爸爸这样进城打工的农民,才会被他们欺负。”因为爸爸的遭际,城市这个名词,早已经伤害了孩子的心灵。他并不喜欢像城市那样的地方,感觉那里高楼入云,宽阔的街道和人群都有着毫无温度,冰凉的喧嚣,人山人海。然而,那里还有大学,图书馆,天文馆,是他小小的阅历里渴望抵达的地方。
“那你要去哪儿上大学呢?那你岂不是要一直一直读书,十七八岁了还在读书?胡子都长长了还在读书?”
“我将来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上大学。然后,去很多很多很远的地方。”他还想对弟弟说,等他走遍了世界以后,他就会回到潘渡来,和弟弟,爸爸妈妈,老祖母,一起过着相亲相爱的生活。然而,那时候,老祖母还会活在人世么?即便他只是一个孩子,也领略得到人世无常,生和死的相近。死亡就是,祖母不再在家,她睡到村子西头的坟地里头,一捧黄土是她永远敲不开的门。永远……想到这里,孩子的心瞬即地碎了一下,他的眼泪漫漫地蒙住眼眸,遮蔽了咽喉里的声音。然而,月光下望过去,他只是静静地靠在树杈间,双手攀着树干,双腿习惯地架着二郎腿,文静的小小书生,初具美雅的风度。
乔乔对哥哥这些汹涌的心理活动毫无察觉,他只是满目钦佩地望着哥哥:“反正,我的成绩不如你,要是读书读到那么大,早就被老师打成瘪瘪的残废人了。我长大了也不会进城打工。我就一直住在潘渡。”他计划道:“我先养5只鸭子,满十岁了就养20只,长大了,就养500只。”
小兄弟俩还讨论了一个很是羞涩的问题。霄霄认为乔乔如果一生都留在台上,又和念珠儿一起玩,一起放鸭子的话,长大了,怕是只能娶念珠儿这么一个凶丫头当堂客了。乔乔的脸红红的,他嘻嘻哈哈地笑起来,可是心里却已经做出了让步:真到了那个时候,希望念珠儿不要那么会骂人就好了。
这长河边絮语的一对小兄弟呵,没有人听见他们的说话。连念珠儿也不晓得她正在被隔壁家的小男孩打歪主意呢。村庄睡着了,长河睡着了,只有他们躺着的树枝上翠绿的叶苞,只有春风吹着漫野的油菜花的香,只有深蓝的天空上满天的繁星,眨巴着眼睛,闪烁着光芒,温柔无语地陪伴。(全文完)#
责任编辑: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