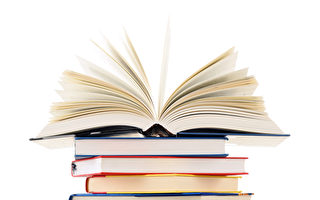(续前文)
脚下的悲惨世界
每一次,只要大家带着那么点幸灾乐祸,跟聚龙花园内的非中国居民交头接耳,说在他们舒适的公寓底下有个如痳疯般的悲惨世界,怀疑效应便会再度被强化,而这让我感到说不出的不自在。
“你说的‘老鼠’在哪?我们怎么从来没见过?”
一个法国邻居语带嘲弄地发问。
“这些人从哪里来的?他们在地底干嘛?靠什么过活?那里有厨房、有浴室吗?”
另一个人连珠炮似地追问。
另外有一个已经移民的法国女人,住在另一栋都是外国人的大楼里,声称我正在筹备一场团体“奇幻”之旅,地点就是我社区的地下室,好让大家见识隐藏版的北京。我大吃一惊,只好硬装出幽默口吻,尴尬地笑着附议:
“没错,而且我会负责准备一袋袋花生好让你们喂食,保证跟在动物园一样好玩。”
一个单纯的电梯按钮,便将我们的平常世界与“活死人”的天地隔开来,我们在上头重现西式享受,虽然有意无意混了点中国风。聚龙社区这条龙的光彩早已不复从前。
这里是中国房仲业者所谓的“豪宅”,有着一九七○年代巴黎郊区社会住宅一切优雅特质。“老鼠”住所的入口在第七栋大楼,这一栋的三楼驻有绿色和平北京办公室、一些外国媒体以及一个投资俱乐部。
电梯的按钮带着访客向下,门开往一个廊厅,地面的白瓷砖脏到看不出原本的颜色,灯光惨淡,还不时能听到“霹啪”的爆裂声响,一头斜放着一张布满灰尘的老旧黑色沙发,上面堆满纸箱。这里乍看之下没有任何异样,感觉不到人的痕迹,不过再走几步后,就可以发现隐蔽角落到处拉起绳子,上面晒着袜子、内裤、衬衫和长裤。便服里夹杂着成套制服,有清洁阿姨的蓝色或灰色制服、工人的蓝工作服、服务生的,可说中国大城市里廉价劳工的职业样本几乎一应俱全。
水泥地的阴暗宿舍挤了四十个工人,上下铺铁床一排接着一排。靠近墙壁另一侧由工人体育馆的一间夜店(里面出入的都是北京富家子弟)承租,住了店里十五个清洁女工,摆了床以后空间所剩无几。走廊底,则是附近一家餐厅的十人员工宿舍。
市中心地面房子的租金昂贵,但只能住得靠近工作地点才能免于舟车劳顿、撑得住爆肝的工时,种种考量驱使他们接受这样的生活条件。一股甜腻而令人作呕的芳香剂气味,随着我们靠近盥洗室越来越浓。
公共卫浴区入口通道只有一个,全部的房客共用两个洗手台,里头缺乏照明,中间仅隔着一片简陋的板子;女生这一侧有四间独立的洗手间,男生则有四个小便斗和三个蹲式厕所,臭气冲天。这里没有淋浴间也没有热水,洗澡得自己想办法,这七十名房客每个人都有一只塑胶脸盆,里面装着厕所水龙头接出来的水。
一转弯,有人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怎么,你们迷路啦!我还是第一次在这儿碰到楼上的房客。”
郑元昭惊呼。他是打杂的,负责捡纸屑、垃圾以及大楼出入口的清洁维护。
“这儿没有任何中国住户会来就算了……没想到我遇到的还是个老外呢!”
这个来自湖北的老头子相当有意思,只要在聚龙社区遇到老外,总是不忘热情喊一声你好。相较于北京人的作风,他显得可爱许多。我们刚搬到北京那个月,还拿捏不准我们在此地大人稠的都会里的定位,而他那亲切的笑容在某种程度上像一股安慰的力量。我于是对他解释起来。
“我正在写一本书,要谈住在北京地下室的人。”
我边说边祈祷他别被吓跑。根据以往经验,在中国若这么直白说明来意,十之八九都会吃闭门羹。我接着说:
“我没想到聚龙社区的地下室也有人住。我只是跑下来,就发现了这里,简直活像个迷宫。这个地方真的很神奇,你们的更衣室都在这里吗?”
老郑对我竖起大拇指。
“好、好、好,这主题好。所有人一提起北京啊,都围着它辉煌的历史打转,玻璃塔、财富、名车,可没人关心我们在地底下怎么生活。”
“所以您住在这儿吗?方不方便带我参观一下?”
“等等, 这是我老婆。”老郑转头向她介绍:
“这位先生是法国很有名的大作家。”
不管有意或无心,他并不在乎我的文学造诣大抵就是报章杂志的文章等级而已。
“他要写住在地下室的人的事,想知道我们是怎么生活的。”
他的太太刘舒真,跟老郑一起负责打扫我们大楼的出入口,听了,脸色微微一变,我可以感觉到我的出现让她有所顾虑。最后,他们带我往厨房去。
晚餐时间快到了,尽管住在地底深坑,中国人对人际关系依然不含糊。走廊尽头的右边,一道厚重金属铁网门后便是车库。那里灯火通明、洁净无瑕,停著有钱老板的豪华名车,宾士、奥迪或保时捷。左边一道阴暗的水泥楼梯,B2的房客可以从这里走到位于B1的厨房。
狭小通道走到底,就是沿着停车场而建的四间厨房,名车的排气管以及排出的毒气取代通风系统。这些上了年纪的夫妇受雇于聚龙管委会,主要负责清洁维护,各自有个角落可放私人物品、准备三餐。当时正值中国黄历新年,吃的是传统菜色:饺子。这食物唯一的变化就是内馅,包猪肉、红萝卜或猪肉、菠菜。
“我们有客人啦!他可是法国很有名的大作家。”
老郑介绍道,他刻意营造出某种神秘感,一方面对我们有利,另方面也提升了他个人形象。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为何,中国人就吃这一套。
老郑每个月领一千八百元人民币,他也承认,其实他们可以住在原本的村子(在黄冈市,离武汉不远)继续种田养活自己,当然会拮据点,但日子还过得下去。只是加上两个儿子,一个二十六岁,一个二十七岁,可就没办法了。
实际上他们两个儿子都有工作且经济独立:一个在武汉做美发;另一个有机械工程学位,在云南工作,负责维修检测工地那些巨大的推土机。不过两个儿子都还未婚,于是这对老夫妇才会到北京来,每天劳碌为他们筹措聘金。
依照中国的传统,男方要送女方一栋房子、金银首饰以及聘金,或是一辆车。若不能提供足够的物质保障,是结不了婚的。
“在黄冈,我们得替女方买一栋房子加上聘金二十万人民币。”老郑咒骂着:“我们中国啊!根本不是娶老婆,是在买老婆。”
他们夫妻俩已经存了一点钱,但是还得再工作好长一段时间才能凑到四十万人民币,替兄弟俩各买一栋房子。老郑面容憔悴,有明显的黑眼圈,说到他其实受不了在城里过着像老鼠一样的生活,因为他在家乡有一栋大房子,乡下空气好得很。
“一开始,在这房间里我根本没法呼吸,而且闻着那股臭味老是让我头痛。我老婆也没好到哪里去。但是对她来说,打扫社区的工作比在田里干活来得轻松。”
他的太太尽力维持她的优雅。头发编成一根长长的辫子,白色开襟上衣外面罩着一件中式剪裁盘扣短外套。她的气色相当好,根本看不出她竟住在地底。老郑则是一头蓬松乱发,天天都穿着同一条破旧的裤子、军人迷彩衬衫。他们原本充满向往来到北京,现在面对着污染和悲惨的生活条件,早已失了心情、也没钱去参观“紫禁城”,遑论“长城”或“天坛”这些他们说好非去不可的地方。
“到哪儿都要门票,对我们来说太贵了,结果我们只去了天安门广场。北京不像我想的那么好,空气太糟了,因为有污染。而且北京人瞧不起我们这些乡下人,他们没啥教养,到处乱丢烟蒂、在公共场所吐痰。北京菜也不怎么样。老实说,我们村子里的人还比较文明。”老郑说。
郑元昭和刘舒真,他们两人在聚龙花园的月薪加起来是三千人民币,加上老郑的退休金一千八百元,一个月共有四千八百人民币,看来还要工作好多年才行。但是,他们都隐约觉得在聚龙的日子不多了。
“管委会很快就会把我们给遣散的。”
刘舒真对我们说,她有着纯朴之人才有的聪慧眼神,甘于命运的安排。
“他们雇用老人负责清洁维护,是因为这比雇用年轻人来得便宜,况且他们安排的住宿环境很差。要是我们不满意,他们就会叫我们滚蛋,因为他们很清楚退休的人很难找工作。不过我们年纪也不能太大,或是在这里待太久,因为他们担心我们要是生病或出什么意外,还得帮忙付医药费。”
这些民工通常没有健康保险,而雇主有道义责任帮他们付医药费。老郑夫妇打算被遣散后回到他们的村子,他太太可以继续种田,他则会试着到工厂找份差事。
“说起来,到时就算在我这个年纪很难找到工作,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事”。
老郑这么想着。
“因为在这儿,我们的自由都被他们剥夺了。”
中国能够带给他两个儿子更好的未来吗?
“这要看他们造化。”
他谨慎地回答。
“今天,在中国一切都有可能。中央的决策是好的,即便地方上有太多贪腐的公务员。但是政府应该更加保护穷人,因为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穷人越来越穷。”◇(节录完)
——节录自《低端人口》/ 联经出版公司
【作者简介】
派屈克‧圣保罗(Patrick Saint-Paul)
2013年起任法国《费加洛报》驻中国特派记者。曾前往狮子山共和国(相关报导获得2000年Jean Marin战地记者奖)、利比亚、苏丹、象牙海岸、伊拉克、阿富汗、德国、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低端人口:中国,是地下这帮鼠族撑起来的》是他的第一本书。
责任编辑: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