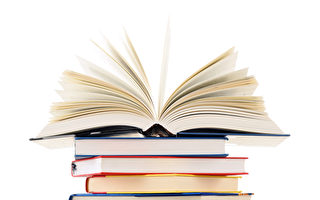(續前文)
腳下的悲慘世界
每一次,只要大家帶著那麼點幸災樂禍,跟聚龍花園內的非中國居民交頭接耳,說在他們舒適的公寓底下有個如痲瘋般的悲慘世界,懷疑效應便會再度被強化,而這讓我感到說不出的不自在。
「你說的『老鼠』在哪?我們怎麼從來沒見過?」
一個法國鄰居語帶嘲弄地發問。
「這些人從哪裡來的?他們在地底幹嘛?靠什麼過活?那裡有廚房、有浴室嗎?」
另一個人連珠炮似地追問。
另外有一個已經移民的法國女人,住在另一棟都是外國人的大樓裡,聲稱我正在籌備一場團體「奇幻」之旅,地點就是我社區的地下室,好讓大家見識隱藏版的北京。我大吃一驚,只好硬裝出幽默口吻,尷尬地笑著附議:
「沒錯,而且我會負責準備一袋袋花生好讓你們餵食,保證跟在動物園一樣好玩。」
一個單純的電梯按鈕,便將我們的平常世界與「活死人」的天地隔開來,我們在上頭重現西式享受,雖然有意無意混了點中國風。聚龍社區這條龍的光彩早已不復從前。
這裡是中國房仲業者所謂的「豪宅」,有著一九七○年代巴黎郊區社會住宅一切優雅特質。「老鼠」住所的入口在第七棟大樓,這一棟的三樓駐有綠色和平北京辦公室、一些外國媒體以及一個投資俱樂部。
電梯的按鈕帶著訪客向下,門開往一個廊廳,地面的白瓷磚髒到看不出原本的顏色,燈光慘澹,還不時能聽到「霹啪」的爆裂聲響,一頭斜放著一張布滿灰塵的老舊黑色沙發,上面堆滿紙箱。這裡乍看之下沒有任何異樣,感覺不到人的痕跡,不過再走幾步後,就可以發現隱蔽角落到處拉起繩子,上面曬著襪子、內褲、襯衫和長褲。便服裡夾雜著成套制服,有清潔阿姨的藍色或灰色制服、工人的藍工作服、服務生的,可說中國大城市裡廉價勞工的職業樣本幾乎一應俱全。
水泥地的陰暗宿舍擠了四十個工人,上下鋪鐵床一排接著一排。靠近牆壁另一側由工人體育館的一間夜店(裡面出入的都是北京富家子弟)承租,住了店裡十五個清潔女工,擺了床以後空間所剩無幾。走廊底,則是附近一家餐廳的十人員工宿舍。
市中心地面房子的租金昂貴,但只能住得靠近工作地點才能免於舟車勞頓、撐得住爆肝的工時,種種考量驅使他們接受這樣的生活條件。一股甜膩而令人作嘔的芳香劑氣味,隨著我們靠近盥洗室越來越濃。
公共衛浴區入口通道只有一個,全部的房客共用兩個洗手台,裡頭缺乏照明,中間僅隔著一片簡陋的板子;女生這一側有四間獨立的洗手間,男生則有四個小便斗和三個蹲式廁所,臭氣沖天。這裡沒有淋浴間也沒有熱水,洗澡得自己想辦法,這七十名房客每個人都有一只塑膠臉盆,裡面裝著廁所水龍頭接出來的水。
一轉彎,有人擋住了我們的去路。
「怎麼,你們迷路啦!我還是第一次在這兒碰到樓上的房客。」
鄭元昭驚呼。他是打雜的,負責撿紙屑、垃圾以及大樓出入口的清潔維護。
「這兒沒有任何中國住戶會來就算了……沒想到我遇到的還是個老外呢!」
這個來自湖北的老頭子相當有意思,只要在聚龍社區遇到老外,總是不忘熱情喊一聲你好。相較於北京人的作風,他顯得可愛許多。我們剛搬到北京那個月,還拿捏不準我們在此地大人稠的都會裡的定位,而他那親切的笑容在某種程度上像一股安慰的力量。我於是對他解釋起來。
「我正在寫一本書,要談住在北京地下室的人。」
我邊說邊祈禱他別被嚇跑。根據以往經驗,在中國若這麼直白說明來意,十之八九都會吃閉門羹。我接著說:
「我沒想到聚龍社區的地下室也有人住。我只是跑下來,就發現了這裡,簡直活像個迷宮。這個地方真的很神奇,你們的更衣室都在這裡嗎?」
老鄭對我豎起大拇指。
「好、好、好,這主題好。所有人一提起北京啊,都圍著它輝煌的歷史打轉,玻璃塔、財富、名車,可沒人關心我們在地底下怎麼生活。」
「所以您住在這兒嗎?方不方便帶我參觀一下?」
「等等, 這是我老婆。」老鄭轉頭向她介紹:
「這位先生是法國很有名的大作家。」
不管有意或無心,他並不在乎我的文學造詣大抵就是報章雜誌的文章等級而已。
「他要寫住在地下室的人的事,想知道我們是怎麼生活的。」
他的太太劉舒真,跟老鄭一起負責打掃我們大樓的出入口,聽了,臉色微微一變,我可以感覺到我的出現讓她有所顧慮。最後,他們帶我往廚房去。
晚餐時間快到了,儘管住在地底深坑,中國人對人際關係依然不含糊。走廊盡頭的右邊,一道厚重金屬鐵網門後便是車庫。那裡燈火通明、潔淨無瑕,停著有錢老闆的豪華名車,賓士、奧迪或保時捷。左邊一道陰暗的水泥樓梯,B2的房客可以從這裡走到位於B1的廚房。
狹小通道走到底,就是沿著停車場而建的四間廚房,名車的排氣管以及排出的毒氣取代通風系統。這些上了年紀的夫婦受雇於聚龍管委會,主要負責清潔維護,各自有個角落可放私人物品、準備三餐。當時正值中國黃曆新年,吃的是傳統菜色:餃子。這食物唯一的變化就是內餡,包豬肉、紅蘿蔔或豬肉、菠菜。
「我們有客人啦!他可是法國很有名的大作家。」
老鄭介紹道,他刻意營造出某種神祕感,一方面對我們有利,另方面也提升了他個人形象。不管他們的社會地位為何,中國人就吃這一套。
老鄭每個月領一千八百元人民幣,他也承認,其實他們可以住在原本的村子(在黃岡市,離武漢不遠)繼續種田養活自己,當然會拮据點,但日子還過得下去。只是加上兩個兒子,一個二十六歲,一個二十七歲,可就沒辦法了。
實際上他們兩個兒子都有工作且經濟獨立:一個在武漢做美髮;另一個有機械工程學位,在雲南工作,負責維修檢測工地那些巨大的推土機。不過兩個兒子都還未婚,於是這對老夫婦才會到北京來,每天勞碌為他們籌措聘金。
依照中國的傳統,男方要送女方一棟房子、金銀首飾以及聘金,或是一輛車。若不能提供足夠的物質保障,是結不了婚的。
「在黃岡,我們得替女方買一棟房子加上聘金二十萬人民幣。」老鄭咒罵著:「我們中國啊!根本不是娶老婆,是在買老婆。」
他們夫妻倆已經存了一點錢,但是還得再工作好長一段時間才能湊到四十萬人民幣,替兄弟倆各買一棟房子。老鄭面容憔悴,有明顯的黑眼圈,說到他其實受不了在城裡過著像老鼠一樣的生活,因為他在家鄉有一棟大房子,鄉下空氣好得很。
「一開始,在這房間裡我根本沒法呼吸,而且聞著那股臭味老是讓我頭痛。我老婆也沒好到哪裡去。但是對她來說,打掃社區的工作比在田裡幹活來得輕鬆。」
他的太太盡力維持她的優雅。頭髮編成一根長長的辮子,白色開襟上衣外面罩著一件中式剪裁盤扣短外套。她的氣色相當好,根本看不出她竟住在地底。老鄭則是一頭蓬鬆亂髮,天天都穿著同一條破舊的褲子、軍人迷彩襯衫。他們原本充滿嚮往來到北京,現在面對著汙染和悲慘的生活條件,早已失了心情、也沒錢去參觀「紫禁城」,遑論「長城」或「天壇」這些他們說好非去不可的地方。
「到哪兒都要門票,對我們來說太貴了,結果我們只去了天安門廣場。北京不像我想的那麼好,空氣太糟了,因為有汙染。而且北京人瞧不起我們這些鄉下人,他們沒啥教養,到處亂丟菸蒂、在公共場所吐痰。北京菜也不怎麼樣。老實說,我們村子裡的人還比較文明。」老鄭說。
鄭元昭和劉舒真,他們兩人在聚龍花園的月薪加起來是三千人民幣,加上老鄭的退休金一千八百元,一個月共有四千八百人民幣,看來還要工作好多年才行。但是,他們都隱約覺得在聚龍的日子不多了。
「管委會很快就會把我們給遣散的。」
劉舒真對我們說,她有著純樸之人才有的聰慧眼神,甘於命運的安排。
「他們雇用老人負責清潔維護,是因為這比雇用年輕人來得便宜,況且他們安排的住宿環境很差。要是我們不滿意,他們就會叫我們滾蛋,因為他們很清楚退休的人很難找工作。不過我們年紀也不能太大,或是在這裡待太久,因為他們擔心我們要是生病或出什麼意外,還得幫忙付醫藥費。」
這些民工通常沒有健康保險,而雇主有道義責任幫他們付醫藥費。老鄭夫婦打算被遣散後回到他們的村子,他太太可以繼續種田,他則會試著到工廠找份差事。
「說起來,到時就算在我這個年紀很難找到工作,好像也不是什麼壞事」。
老鄭這麼想著。
「因為在這兒,我們的自由都被他們剝奪了。」
中國能夠帶給他兩個兒子更好的未來嗎?
「這要看他們造化。」
他謹慎地回答。
「今天,在中國一切都有可能。中央的決策是好的,即便地方上有太多貪腐的公務員。但是政府應該更加保護窮人,因為有錢的人越來越有錢,窮人越來越窮。」◇(節錄完)
——節錄自《低端人口》/ 聯經出版公司
【作者簡介】
派屈克‧聖保羅(Patrick Saint-Paul)
2013年起任法國《費加洛報》駐中國特派記者。曾前往獅子山共和國(相關報導獲得2000年Jean Marin戰地記者獎)、利比亞、蘇丹、象牙海岸、伊拉克、阿富汗、德國、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低端人口:中國,是地下這幫鼠族撐起來的》是他的第一本書。
責任編輯: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