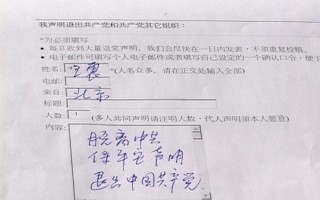【大纪元3月12日讯】我毕生难忘这一天:一九六八年八月十日。我也难忘这一天: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在这两个日子中间,整整六十四天,我失去自己的姓名和人格,仅仅剩下这副皮囊和呼吸,成为被关在笼子里的活物。
一辆吉普车把我送到西村监狱,一位中年军官把我带进一个办事间后就走了。办事间里有两张办公桌,靠墙一个大档案柜,一个军官给我办理‘入住’手续。和住医院或住宾馆不同,我没有行李,但必须取下随身带着的自来水笔、手表和穿在脚上皮鞋的鞋带。取下就取下罢,我倒无所谓,笔和表这时对我毫无用处,鞋带属于绳索一类,本来就是用来捆绑东西的。我不是东西,是人,也教人用绳索捆绑螃蟹似的,捆个结实,刚才在警备司令部才解开,现在把鞋带拿走,也好,解除束缚嘛。
只是,要我把裤子上的皮带也拿下来,哪可不行﹗我觉得受到侮辱,拿掉皮带,裤子还怎么穿,难道整天用手提着?那办事的军官看看我的登记表,微笑着向我解释道:‘你是个知识分子,道理应当可以明白。入狱的人,身上的所有绳带,都必须取下来放在这里保管。我们信任你,不会在监狱里乱来,但你无法保证,其他的人不会把你的皮带拿去干坏事﹗比如,用皮带自杀。’而且说这是历来就如此的‘狱规’。
取下皮带我勉强可以接受。又因为军官提到‘入狱’、‘监狱’及‘狱规’等词语十分刺耳,我不假思索即予回驳。是和你穿一样军装的张代表把我弄到这里来的,既无拘留证,又无逮捕证,更无法院判决书,我能算‘入狱’吗?
军官好像不屑与我辩论,一本正经地向我当面宣布三条纪律:一、不得告诉他人我原来的职务和工作单位;二、在囚室里不得与他人谈及自己的案情;三、不得把自己的真实姓名告诉任何犯人,只须记住自己的编号是一一O八。我真正感到忿恨和痛心,从这一刻开始,我连使用真实姓名的基本权利也被剥夺了﹗让我记住一个号码,岂不是要我的命。谁都知道我最大的弱点就是数学盲,两位数还好些,三位数重复多次勉强可以记住,三位数以上,毫无办法。直到现在,我可以记忆起从前许多人和事,甚至某些细节,就是记不住自己家的电话号码。心里一急,没想到却急出一点智慧来。一一O八,后面两位数,不是正巧与我的名字同音吗?当时一下子就记住了,到现在也没有忘记。
狱警带我走进一条阴暗的甬道,光线从甬道尽头高墙的小窗口投射进来,我的眼睛不能适应,勉强可以看到两旁是一式的矮门,一律上锁,我猜想是两排监仓。走到左边最后一个矮门,狱警开了锁,突然问我:‘有你认识的人吗?’我扫了一眼,监仓里已有四个人,一律背心内裤,席地而坐,脸无表情。我说:‘没有。’狱警又问监仓里那四个人:‘你们有人认识他吗?’四人同声答道:‘不认识。’然后,叫我进去,随手从外面上锁。我心里觉得好笑,都说不认识,住进来不就认识了吗?多此一举。
这间监仓不到十平方,靠后墙的一半是略高于膝盖的平台,另一半地板上垫了一块木板。后墙高处一个加了铁栅栏的小窗,天花板上一只二十瓦电灯泡,监仓门上端开一小圆孔,下端开一个大一点的方洞,每天两顿饭就从这个方洞送进来。门旁角落,放一只木马桶,大小两便都用它。每天傍晚轮流一人出去倒马桶,都有狱警监视。
随着外面上锁的声响,我的脑子突然空白了。我这副皮囊,呆呆地倚墙而立,如果不是还有三寸气在,俨然一条僵尸。大约有三十分钟,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只觉得有一股无名的情绪,似冰似火,似潮似涌,乱流一般,在周身乱窜。
正不知如何控制自己,忽然矮门外有点动静,又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同室中年纪最轻的那位‘红卫兵’说:‘开饭了﹗’果然,饭菜就从矮门下端的小方洞送进来。我最后一个接过饭菜,是一个两寸高的黑釉粗瓦盆,剩着米饭和水煮冬瓜。肚子实在饿了,靠墙坐下,埋头就吃,没几下便完事。什么味道倒也没有很深的印象,只觉得如果再来一份,完全有能力打发。二十分钟左右,粗瓦盆又从小方洞送了出去,自己不必麻烦。监狱里的第一顿饭,就这样平淡无奇地咽下去了。
不过,我还是注意到两个年轻人。一个是刚才说‘开饭’的那一位,十六七岁,开朗活泼,东北口音,我猜想他可能是中学红卫兵头头,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另一个瘦瘦高高,十九岁上下,一直靠在矮门边站着,愁眉苦脸,两眼闪着泪光,一份饭菜,只吃了不到一半。我有意在他身旁坐下,轻声问道:‘没胃口?’他低着头,轻轻用广东话回我一句:‘无胃口。’我又轻声劝他说:‘无胃口也要多吃一点。如果不吃饭,身体搞垮了,将来出去半条命,还怎么工作?’
忽然从监视孔传来一身警告:‘不许乱说乱动﹗’我回答道:‘我劝他吃饭没有什么不对罢?’监视孔外的人不再说话,我也给他一点面子,不再说什么了。我的判断大致不错:从踏入监狱的大铁门到吃完第一顿饭,没有见过一个警察,说明监狱已经被军管会接管了。我所在的监仓,连我在内一共五个人,都是‘新人’,没有一个‘老犯人’,说明监狱是临时为我这样一类人设置的。这位瘦瘦高高的青年慢慢也不再那么忧郁了,饭也吃好了。他悄悄告诉我,他是省体育工作队的跳高运动员,比赛得过奖牌。因为家庭出身是资本家,两派对立,他被打成‘狗崽子’,军代表把他抓到这里来,心里很委屈。一个月后,他就出去了。临走,还拉一拉我的手。
那位中学红卫兵头头,说话不多,该吃就吃,该拉就拉,一切都无所谓。我隐约感觉到,他有一种近乎习惯了的优越感,不自觉的流露出来。许多中、高级军官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不知不觉从父母的军衔、用小车接送,慢慢养成以‘爸爸官大为荣’的习性。小朋友之间有些小纠纷,开口就是‘我爸比你爸大’。红卫兵运动兴起不久,这种‘优越感’迅速膨胀,很快就发展成一种暴力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甚至还有封建色彩特浓的顺口溜:‘龙生龙子凤生凤,老鼠生仔会打洞’。一副军装,一条皮带,从学校打起,打遍全社会。只有他们最革命,别人都是牛鬼蛇神。
后来闹得太凶,打死很多人,内部又发生分裂,互相动武,又打死了不少。才不得不用军队这个正规的暴力集团,以暴镇暴,将红卫兵运动压了下去。与我同囚室的这位红卫兵头头,到我出狱的时候,仍然关着。我想,他的老子可能是高官,把他关在监狱里,保护多于惩罚。
小小囚室,不到十平方,却是相当标准的牢笼。两顿饭之外,规定的功课,是早晚各一次的革命仪式:早请安和晚请罪。所谓早请安,就是起床后的第一件事,集体立正唱《东方红》,然后是同声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接下来是朗读《毛语录》,两急实在忍不住了,可以临时通融,到角落的马桶去解决。不过,在小小的笼子里,庄严的仪式和见不得人的方便同时进,未免有点滑稽。晚请罪在临睡前进行,将《东方红》换成《大海航行靠舵手》,其他照旧,没那些杂七杂八的事,做起来就方便些。在外面做这两次仪式,必须高挂毛主席像,加上党旗国旗,布置一个‘三忠于’的庄严环境,大家面对毛主席像,唱歌跳舞读语录,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这里是监仓,总不能把毛主席也请进监狱罢。但没有毛主席像,又觉得失去目标,向谁早请安,向谁晚请罪,谁都说不清。
笼子里的人数有增有减,很快就有增无减,二十天后,竟然增加到十一个人。我估计,外面正大肆抓人,笼子里岂止‘人满为患’,简直是挤压如沙丁鱼。白天磕磕碰碰,已经十分难堪,排队蹲马桶,更是一大难题。晚上睡觉,侧身个挨个还是躺不下来。好在大家同一笼,共犯难,很快就互相同情,互相沟通,互相贴近,互相体谅。协商结果:让多数人睡得好些,三个人站着,每隔两小时左右轮换一次,总算解决了睡觉问题。
小笼子里关着十一个人,倒使我想起小学时一道‘鸡兔同笼’的算术题。当年的‘鸡兔同笼’,在于训练小学生加、减、乘、除的初级数学头脑,只是这种数学头脑,根本无法理解当代‘鸡兔同笼’的悲哀。同笼中一位河北汉子,首先揭开悲哀的序幕。
他在绝望的时候说:‘诸位战友,如果将来有谁能够出去,请记住我,把我的事也带出去!’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称呼我们为战友,我也把他视同战友,至於姓名,并不重要。
战友四十来岁,转业军人,广州沙河一家百货公司的副经理。两大派武斗期间,公司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推举他出来主持防御工作。他组织公司里同派的人,在大门口和临街二三楼窗下,堆起沙包,构筑起简单的防御工事,并通过他与原先部队的关系,弄来一些枪支弹药,使该地区对立一派的武斗队,不敢轻举妄动,这家公司自然成为本地区一个相当突出的‘据点’。战友作为这个防御据点的头头,就被他们单位的军代表关进笼子里来了。
进笼之初,战友非常乐观,劝大家吃好饭,睡好觉,耐心等待,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他常说:‘没打人,没杀人,怕什么!’有一天,战友被从笼子里提了出去,临走还笑着和大家摆摆手。我在心里为他能这么快出笼而高兴。
第二天傍晚,战友又突然回笼了。我发现他衣衫破损,脸颊瘀肿,神情十分疲惫,估计他可能‘受刑’了。他一言不发,倚墙站着,陷入沉思。我半夜醒来,见他依然站着,就让出一点地方,轻声说:‘你也躺一会儿罢。’他仍然站着,阴沉的说:‘我判断错误。’
过了两天,战友又从笼子里被提了出去。和上次一样,他临走时笑着向大家摆摆手。一连三天不见战友回笼,我估计,战友已被转移到别的笼子里去了。
第四天中午,战友又回笼了。不过,他的出现,使大家感到意外,还大吃一惊。他不仅衣衫被撕破撕碎,脸和脖子伤痕累累,皮下瘀血,肿胀得都变了形,几乎认不出来了。战友靠墙坐着,半天才用嘶哑的嗓音说:‘我不服﹗死也不服!’
随后,我渐渐了解:战友被他们单位的军代表提出笼子,交由群众批斗。罪名临时由批斗的人定,‘挑起武斗的坏头头’、‘抢劫粮食的土匪’、‘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份子’等等,都是当时的‘时髦罪’;批斗的方式也是当时的‘流行式’,挂牌、罚跪、殴打。一连批斗三天,一块十多公斤重的木牌,用细铁丝拴住,挂在战友的脖子上,铁丝都快吃进皮肉里去了。这还不算,有人还用特制的竹刀,砍他的头,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完了,又放回笼子里。什么时候需要,就和杀鸡宰兔一样,再从笼子里提出去。
我完全能够体会战友的感受。在这个意想不到的年代,人性是如此脆弱,兽性又是如此猖獗,只要手里有权,就可以堂而煌之地打出‘革命’的招牌,干尽伤天害理的勾当。我坚信自己不是鸡兔(禽兽),是普普通通有血有肉的一个人,即使无法对社会做出贡献,起码不能害人。如果连人性都丢掉了,还有什么本钱做人?
战友的遭遇,引导我作痛苦而不断的沉思。我意识到处境的险恶,应该向妻子做个交代,让她知道某些真相。因此,我找到一个当时最冠冕堂皇的理由,让妻子给我送《毛主席语录》。这一招果然灵验,我的信经监狱管理军官检查后顺利寄出,不久,妻子就找到监狱来了。
这是唯一的一次‘笼中会’。妻子在收到我的信之前,根本不知道我已被关在西村监狱,亲人生死未卜、下落不明的痛苦牵挂,是可以想象的。
一知道我的下落,她首先想到的是我的腰痛病,尤其时近中秋,天气渐凉,一定要注意保暖。她带来一个大包袱,棉被和秋天的衣物全有,面上还压着一套红塑胶皮烫金的《毛泽东选集》和一本小《语录》。
妻子来探监,完全按照‘监规’进行。我被狱警带出来时,妻子已经坐在长方形大桌子的一头,见我走近,妻子立即起身要过来,但被狱警轻声喝住了。我和妻子面对面坐在大桌子的两头,狱警就站在旁边。如果不是这种特殊的场景,我肯定会紧紧拥抱自己的妻子。见到坐在面前的妻子,还是那么善良,那么温柔,那么美丽,本来准备好一些很重要的话,都变得多余了。我定定地看着妻子两只非常漂亮的大眼睛,用平和的语调说:‘我住在这里还不错,能吃也能睡……’没等我说完,妻子就把话接过去说:‘我看到了,我明白,你放心。我会把孩子照料好,还需要什么,告诉我,一定给你带来。’
听了妻子这些话,看到妻子眼睛中流溢的光彩,我胸中的闸门顿时打开,爱的激流奔腾而出。见面只有短短十几分钟,但妻子给我的激励,使我走过坎坷的人生。夜深了,笼子里虽然拥挤,却也十分安静。我躺在墙角,辗转反侧,脑子里放着‘笼中会’电影,一遍又一遍,永远是那样动人。
我和妻子都是极平凡的人,就像两块不起眼的小磁铁,一次偶然的巧合,碰撞出爱的火花,就互相吸引住了。没有什么神秘的力量,仅仅是与生俱来的这副人的秉性。十多年来,我和妻子阅人极其有限,但能深切感受到人性的脆弱。尤其是由某种‘邪说’煽动的无端仇恨,把一批又一批怀有私心的人,变成凶恶的虎狼,残害一波又一波无辜的生命。我们惊慌,我们恐惧,我们试图躲避,我们在绝望中挣扎。我们口中也唱着那支歌:‘不靠神仙和皇帝,要靠自己救自己。’但我们不知道,最终能够战胜‘仇恨’的力量,不是天上的大救星,而是自己与生俱来的人性。
笼中无意听说今年有闰八月,就是说,我会在笼子里度过两个中秋节。只是笼中既无明月,又无月饼,月圆人不圆,徒增许多伤感。到了十月一日,吃晚饭的时候,水煮冬瓜忽然加了几粒猪油渣,才想起国庆节。两个星期之后,我被提了出去。仅仅由于结算伙食账,使我明白两件事:一,坐牢要交伙食费;二,伙食账结清了,大概不会再回笼了。
7/11/03(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