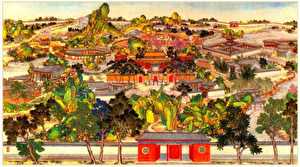1961年8月13日,天阴沉沉的,柏林人早上一觉醒来,发现城市变了样。分隔西柏林盟军管辖区和周围苏联占领区的街道被挖开了,苏军士兵和警察用挖出的砖石暂时阻隔了东西柏林间的交通往来,随后开挖处竖起了一块块两米多高的钢筋水泥板,构成一圈170多公里长的高墙,把整个西柏林围在中间。墙上还陆续安上了铁丝网,沿墙建了300个监视塔。

请你静下心来想一想。你发现我的亲身经历和你以前从电视上了解的法轮功是否是一样?大法在我身上发生的种种奇迹不但改变了我,也让许多人受了益。
流离失所期间,我在外面租房,暂住在成都市光荣西路市场公寓6楼22号。2002年12月9日,我又遭非法绑架。事情是这样的:下午2:30左右我从火车北站发货回暂住房,发现一位身背挎包、坐在车棚门口的小伙子有些面熟,我以为是修炼前在股市上见过面的熟人,也没在意。
近年来在社会上流行这么一句话:过去的土匪在深山,现在的土匪在公安。这个十恶毒世,实在是太糟糕了。由于同修发真象资料被抓,我也受到了牵连。2002年4月2日上午,户警魏大平把我骗到派出所,以我不打电话到派出所报到为由,叫我写保证要打电话来拖延时间。
回家后,所长冉XX规定我每天晚上9点钟必须用家里的座机给值班室打电话以监视我的行踪,有事离开成都必须请假。我当时想:为他人着想,打就打嘛!他们也被江氏集团害得挺可怜的。那年新年快到了,我几年没有回老家,想回去看一看。
每到节假日和4.25、7.20等所谓敏感日,派出所警察或居委会、610成员都会以各种理由骚扰大法弟子。
到了下午,魏大平又要把我往拘留所送,我坚决反对:“我不去,我没有错。连家都未回,你凭什么理由又把我送去,你们知法犯法,我要申诉。”魏大平说:“要申诉也只能到拘留所才行。”我又一次无辜的被魏大平送进了九茹村拘留所。
2001年7月,我和十位坚定修炼的学员被禁闭在一个小间里,长期被包夹守着,从不准出房门半步。从早上6点起床到晚上10时30分左右收监,一直坐军姿,两眼平视前方,直腰,双手必须放在膝盖上,不准闭眼,更不准说话,屁股不准离开凳子。
2000年6月8日,政府开始在四川省展览馆举办污蔑大法的图片展。为了让更多的世人不要再上当受骗,明辨是非,我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来,用复写纸复写几份。6月12日早上,我找到片警魏大平,对他说:“你看我写的这份真象材料,是我亲自到北京去交,还是交给你转交给中央领导。”
我又在驻京办的小房子里面被关了一星期后,由防暴大队的警察押回成都青羊区戒毒所,强行洗脑两天(因为每个上访的大法弟子送回成都后都要先到戒毒所“洗脑”两天)后,再被非法拘留半个月。我和其他拘留人员一样,一进门,便遭到脱光衣服非法搜身,他们对于大法弟子主要是搜经文和钱。
为了绕过警察的层层拦截,我便绕道坐大巴到重庆过武汉再转车到北京。一路上有惊无险;大巴车刚到重庆,我便听收音机里面说人大、政协会议于今天下午3点30分在北京召开,我的心跳加快了,我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北京信访办。
半个月后,已是2000年元旦节,成都市龙潭寺派出所的唐警察来接我,我以为要送我回家过节,结果又把我接到龙潭寺派出所,唐警察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没想到就因为这一个炼字,午饭后他就填写了一张刑事拘留通知书。又把我送进成都市第二看守所(莲花村)非法刑事拘留一个月。
我觉得我在大法中受益匪浅,一定是政府暂时不了解法轮功真象所致。我便开车与全家人和其他功友一起,依法到省政府上访,要求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抓捕的大法弟子,并向政府反映我们修炼法轮功后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真实情况。
于是,我带上法轮大法简介、老师在济南讲法的录音带、录像带和20本《转法轮》,与炼功点上的两名辅导员、一年轻男同修,再加上三个大法小弟子,由我亲自开车带上母亲一起前往简阳老家弘法。一路上,我止不住激动的心情:乡亲们啊,大法救你们来了!你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万古机缘啊!
3月8日,我早就约好儿子的老师蒙玉蓉和她台湾的朋友以及我的伯母一起到狮子山庄去玩。可这天早上一起床后,我感觉到脸紧绷着,还发着烧,很不舒服。便用镜子一照,我傻眼了,我的整张脸发肿,红得像关公,这可怎么办?
1998 年8月,开车的师姐(比我大一岁),开始炼起了法轮功,她说:“沙河堡一位男功友,原是秃头,炼功后都长出了头发;莲花村一位老太太炼功后白头发变成了黑头发,你也来炼法轮功嘛!”我说:“炼功是退休老人的事,我才不炼呢,该吃就吃,该穿就穿,死了算了。”她为我这个好友不炼功而感到惋惜。每周六晚上,我都要到师姐家,和她的丈夫,还有她丈夫的两位生意场上的朋友一起打麻将,有时甚至通宵;而师姐却独自一人看书,我为她这一大转变而感到不解。
与药为伴自从手术失败以后,我的精神压力更大了,知道自己能行走的时间不多了,随时都有瘫痪的危险,病情严重又不能跟亲人、朋友说,怕说后他们担心,只有晚上独自哭泣。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只要一激动或生气,大脑的血管就像琴弦一样绷紧,全身麻木失去知觉。从那以后,我手提包内除了化妆品,就是治脑血管的药:西比林、银杏叶片、眩晕停……,甚至有时走路都发飘,并伴有短暂失明。一次我开小车行驶到神仙树汽车运输公司五隧门口时,眼前突然发黑,我赶紧把车靠边停下,吞下随身携带的药物,趴在方向盘上,大约1小时左右才恢复过来。
失败的初恋十八岁那年,经人介绍,我和本队的小学同班同学恋爱了。他父亲承包修建房屋,他也是钢筋工还带了徒弟,在当地小有名气。那时他家也过上了小康生活,首先买上了黑白电视机,演霍元甲时很多村民都到他家去看坝坝电视。我们谈恋爱也有半年多,在热恋中,他突然向我提出分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无明的眼泪止不住的流……后来才知道,他听同学说我右下肢有病,会影响生育。还是这该死的腿,误了我的终身大事。不久,他又和我的中学同班同学恋爱上了,经常成双成对的从我家门前路过……我实在无法面对这一现实,便决定离开家乡,到成都去开创自己的事业,以后和他拼个高低,看谁比谁强。
编者按:日前,北京及当地七位律师为十一名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做辩护,并克服当局种种刁难于上周递交了上诉状。钟芳琼在这十一名法轮功学员中之一,她曾撰写《疾风劲草》一书,记述自己的故事。为感佩中国国内律师和法轮功学员不畏强权的道德勇气,也希望大家共同呼吁救援被非法关押、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大纪元将重新连载钟芳琼的故事《疾风劲草》。




 2009年9月1日 2:39 AM
2009年9月1日 2:39 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