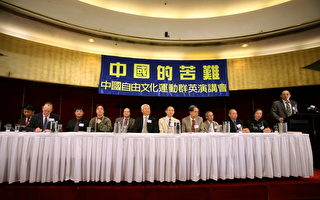在《利图马在安第斯山》中,略萨对秘鲁内战中的统治者和革命者两种权力结构,均有精彩描绘。革命者杀红了眼睛。平叛的秘鲁国民卫队也同样不分青红皂白施暴,除此以外没有任何控制局势的能力。
《旧约》中的恶人该隐杀了他兄弟亚伯之后,建了一座城。他的祭品并不被上帝悦纳。威廉.布莱克在〈亚伯的鬼魂〉中写道:“该隐之城是用人血建造的,不是牛羊的血。”
本届诺奖得主、秘鲁作家巴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的小说《利图马在安地斯山》的扉页题词,就是布莱克这句话。
略萨有句名言说:“作家是他们自身的魔鬼的驱魔者。”以佛家的观点来看,任何有心向善的人都要驱除内魔。青年略萨一度加入秘鲁共产党,六〇年代同情毛派革命,后来日渐转向右翼,投身民主政治。不以政治阵营的眼光来看,就不难发现,略萨的转变,正是他不断驱除内魔的过程和结果。
《利图马在安地斯山》出版于略萨的思想和艺术均已成熟的1993年,是他最重要作品之一。小说情节设置在八〇年代发起的秘鲁革命和内战时期,主人公利图马是政府军的军警,他和他的副手卡列诺被派遣到一个偏远的高地山镇,以寻找在筑路营失踪的三个人:一个哑巴,一个商人,还有一个是筑路工头。利图马开始接触他原本陌生的高地印第安人和印加文明。在茫然寻觅中,为了解闷,卡列诺每天夜里给利图马讲述他与一个妓女的罗曼史,他也在寻找这个得而复失的恋人,由此构成小说的一条缓冲紧张气氛的情节副线。
另一条更重要的副线是逼近山镇的“光辉道路”游击队,即从秘鲁共产党分裂出来的毛派分子的造反活动。在复杂的结构中,含有侦探小说、政治讽喻和爱情故事色彩的几条情节线索,平行交叉发展,最后融汇在一起。与之天人感应的自然景观,是小说开篇的黑云雷暴,笼罩头上的死气沉沉的蛊毒瘴气,以及后来的地震山崩。这一高地的黑白艺术画廊,实际上是那一恐怖时期整个秘鲁的缩图。
在革命与平叛的祭坛上有阅历的中国读者读《利图马在安第斯山》的原文或英译,有时也许难免产生这样的感觉:仿佛在读一部中国小说的外文译本。略萨笔下的那些革命场面,对于经历过文革的人太熟悉了:山地那些男男女女的“革命者”,甚至有十来岁的孩子。他们扛着机关枪、或手持刀枪棍棒,三、四个人一组,依照黑名单,半夜三更直闯“阶级敌人”的家门,上至市长,下至无辜的农场工人,妇女环保人士,一概从睡床上拖出来带走。……公审大会开始了,那些五花八门的“反革命”和“坏分子”,在卡夫卡式的“审判”中,不知道犯了什么罪,糊里糊涂被“革命群众”鞭笞,被枪毙,被棍棒、石头活活打死。酷刑拷问、强奸妇女成了家常便饭。从外国来游客也被当作“帝国主义的走狗”死于非命。
瑞典学院本诺奖颁发给略萨,“由于他对权力结构的描绘及其个人的抵抗、反叛和招致挫败的鲜明形象”。在《利图马在安第斯山》中,略萨对秘鲁内战中的统治者和革命者两种权力结构,均有精彩的描绘。革命者杀红了眼睛。平叛的秘鲁国民卫队也同样不分青红皂白地施暴,除此以外没有任何控制局势的能力。
后来,根据秘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调查,在多年内战中,政府军和游击队均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将近七万死难者,大多数是革命与平叛祭坛上的无辜牺牲品。
神话和祭祀山鬼的活人祭
在恐怖的屠杀风暴中,小说主人公利图马预感到难以从山镇活着出去,他疑惑地问道:“许多劳工都接受了现代生活方式,至少念过小学,见过城市,听过收音机,看过电影,穿着打扮跟文明人一样,可是,可他们的行为怎么像赤裸的吃人肉的野蛮人一样,这究竟是如何可能的呢?” 在略萨看来,把秘鲁毛派仅仅视为对中国的革命暴力的一种效法,那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是要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挖掘人性恶的内魔。
利图马发现,印加帝国的“失落之城”,今天的旅游胜地马丘比丘(Machu Picchu)城堡的墙石,就是那些山地人的祖先搬上山头的。在小说中,从这一城堡的建造到流产的筑路工程,都是以人血作水泥材料。
小说中一位前来考察的丹麦人类学家,比一般秘鲁人更了解印加文明宰杀活人祭祀神灵的历史,他使得利图马想起阿兹特克人的祭司站在金字塔顶部举行活人祭,撕裂牺牲品的胸口的惨状。甚至西班牙人征服秘鲁的殖民战争,也没有如此残暴。在今天的高地,关于山鬼吸人血吃人肉的神话仍然口耳相传。依照民俗,在建庙筑路之前,均要以活人祭和人肉筵席来安抚山鬼。高地仍有一个巫婆,很可能还在操办古老的祭礼――与古希腊的纵酒饕餮、歌舞狂欢的酒神节期间相类似的活人祭。
由此可见,“光辉道路”屠杀“阶级敌人”和“肃清”阶级队伍的举措,以及革命者欢庆胜利的盛典,均有其古老的活人祭、净化和狂欢的宗教仪式的渊源。青年略萨学习过的马列主义理论,其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已经成为一种准宗教。小说中的游击队许诺那些参加革命的人:鲜血不会白流,流一份血,就有一份报酬。可是,这种“血酬定律”和乌托邦的许诺,往往是一种历史的反讽。
与作者通过主人公的深层探究相呼应的,是难以彻查的那三个失踪者的来龙去脉。他们好像不是游击队绑架的。大致查明的那个哑巴的命运是富于象征意义的:他最初受到游击队的攻击,后来又遭到利图马的一个上司的拷打,最后成了巫婆操办的活人祭的牺牲品。
微弱的希望之光
在略萨笔下酷肖现实又扑朔迷离的故事中,在利图马和卡列诺的身上,可以发现一种微弱的希望之光。
尽管利图马隶属于国民卫队,但由于他是有西班牙血统的混血儿,性情温和,态度和善,他成了高地人眼里的外星人。在他身上有作者自身的影子,但他并不是完美的理想人物。他的探究,并不纯粹出于良知,更多地出于文化猎奇。不滥杀无辜,是他起码的道德操守。当他在比较爱情的狂热与革命狂热时,他告诉卡列诺说:“至少,当你爱得发狂时,除了你自己之外,你不会伤害任何人。”
卡列诺热恋的那个妓女,是他从一个毒枭手里救出来的。在他眼里,她虽然有点偷盗和撒谎的毛病,却富于典型的女性美。他把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寄托在她的身上。他的爱的失落,象征着他的爱国情感的失落。那个巫婆劝慰他说:“是一种爱给你带来不幸,使你受难,你的心每个晚上流血。但至少会帮助你继续活着。”
小说的警策意义,最后通过那个人类学家道出来:“秘鲁正在发生的,并不是埋葬暴力之后的万物复苏。暴力似乎隐藏在某处,突然之间会由于某种原因而重新抬头。”
活人祭与牺牲精神
活人祭蕴含的古老信念在于:人类的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安全或幸福,必须建立在少数人牺牲生命的基础上。针对少数人的暴力和人权侵犯,就这样合理化了。
从历史上来看,敬神的活人祭在古代社会恶性变异的着例,是宰杀活人为王侯陪葬,这在印加文明中是非常普遍的,在今天的秘鲁已有多处考古发现。此外,处死宗教异端的火刑,也是活人祭的遗风。但活人祭也有良性的发展:首先,是掌权者和祭司力戒屠杀无辜的奴隶,选择罪人作祭品。然后,在有些文明中,活人祭变为象征性的,例如古希腊一种净化仪式中的替罪人,有时并没有被真正处死,只是接受轻度鞭打石击。最后,取代活人祭的是动物祭或动物的血祭。
今天,活人祭虽然在世界上基本绝迹,但变相活人祭仍然见于专制国家维稳的祭坛上,在那里,其合理化的观念仍然是人心不容易驱除的内魔。
像英文词sacrifice 表明的那样,“献祭”与“牺牲”是同一个词。在宗教伦理和哲学中都有所谓“献祭或牺牲的悖论”(the paradox of sacrifice)。人类既要根绝残酷的被献祭,又可以从原始文明中吸取这样一种有益的精神: 自愿的牺牲――不是血肉生命而是个人利益的牺牲,例如,个人财富或时间的牺牲,义务献血,或死后捐献器官等有利他人或社会的自我牺牲精神,将永远是人类需要弘扬的高尚品格。这是恶中生出的善。对于那些为了某种高尚目标而甘愿牺牲生命的英雄,我们也应当理解、尊重,不能往他们的遗体上泼犬儒的脏水。
略萨尚未出版的最新作品,即他以爱尔兰诗人和革命英雄罗杰•凯塞门(Roger Casement )为主人公的小说《英雄梦》,就是弘扬这种牺牲精神的。2009年7月,略萨在接受一次访谈时表示:在1916年爱尔兰复活节起义中献身的凯塞门,“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谴责人的自私,谴责那些除了自我利益之外再也看不到别的价值的人。他非常慷慨,一生都围绕着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伟大目标,绝对准备着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他把所有的钱都用于人道组织和文化组织。”
活人祭和社会暴力的根源,及其相关的悖论,是值得深入探究的。继《利图马在安第斯山》之后的《英雄梦》,也许只是略萨继续探究这些问题的一个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