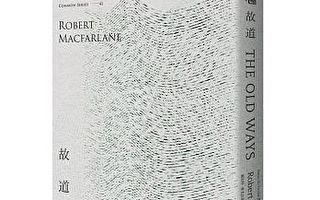我的大姐比我年长十岁,就读于复旦大学;她读书很用功,从不交男朋友。她有两个很要好的女同学,都有了男朋友。大姐经她们介绍,认识了浙江之江大学的高才生穆渭琴。他们认识后,交往密切,情书不断。大姐对他的学识,人品都很赏识。穆渭琴对大姐文静,敦厚的性格,也很欣赏。一有假期,他总是来上海找大姐长谈至深夜才离去。
我们都为大姐能找到这么一位男友而高兴。但好景不长,不知什么缘故,穆渭琴和大姐交往了几个月后就再也没有音讯,从此就消失了。后来才从她的好友处打听到,他嫌我家太富有了,他是一介穷学生,不想高攀。大姐绝不是那种嫌贫爱富的人,她爱的是他的德才和人品。大姐经过这一重大的打击,心都碎了,整天不思茶饭,魂不附体。
当时上海正流行一种叫“碟仙“的算命术,一张大黄纸上,由里圈到外圈,密密麻麻地印着字,纸的正中有一个圆形的阴阳符,用一个大小相同的碟子扣在符上,碟上画一个向下的箭头!三人用中指放在碟中,按照规定的符语,念念有词:碟仙,碟仙,请来相见,祸福有命,指点迷津。不一会儿,碟子就真的动起来了,旋转速度愈来愈快。三人轮流问碟仙自己想问的问题,碟子的速度也渐渐地慢了下来停留在某一个字,或两三个字上,这就是碟仙的回答。
我姐姐问:“穆渭琴为什么不来了?”碟子转了几圈箭头停在一个“贫”字上,又转了几圈停在一个富字上,这两个字正应验了姐姐的同学去了解的情况。我们其他人问的问题如:我今年大考会不会及格,我的咳嗽什么时候才好等等,碟仙都一一作了回答,有时也答非所问,或箭头停在“天”和“机”上,我们也就不敢再问了,因为天机不可泄漏啊!
由于碟仙的灵验,我家兄弟姐妹一放学回家,就像上了麻将瘾一样,凑上三个人就转将起来。按规定玩碟仙要三个人才能转起来,后来发展到姐姐自己买了一副碟仙,关在她房间里独自一人玩,碟仙居然破例也转起来了。大姐终日神魂颠倒,沉溺于碟仙中,弄得精神恍惚,憔悴不堪。父亲知道以后,决定收走了碟仙,并请神精科医生为大姐诊断治疗,才算结束了这场悲剧。
后来才听说穆渭琴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并且得到了提拔,正准备去延安“朝圣”,“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呢。阿弥陀佛!谢谢穆渭琴抛弃了我姐姐,否则姐姐必然会与资产阶级的家庭决裂,与情人双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说不定她现在也是个大贪官的太太或是别的不测结局呢。
……
我从小不喜欢数学,考试总是不及格。但和邻居小朋友在弄堂里(上海居民的住地,相当于北京的胡同)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我总是数一数二。我更愿意当强盗,躲躲藏藏,更富刺激性,我从未被官兵抓到过,堪称盗中之王也。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总喜欢去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荡一会儿秋千。孩子们自觉地排着队,顺序上前。
我大约排了二十分钟,当轮到我上架时,突然从远处来了一个媬姆样的妇女,手牵着一个碧眼金发的小男孩。我正要登上架,那妇女一手把我推开,一手将那外国男孩抱上秋千,嘴里还叨叨:“阿拉外国小囝先来”。我气极了,为什么外国小孩就有特权不排队?外国人又怎么的?但在那时,我只是个小孩子,敢怒而不敢言,只得忍气吞声地离开了秋千架。挨到那个外国小孩玩得不想玩了,我才上了架,但先前那种兴致勃勃想荡秋千的劲头,被彻底冲跨了。我兴味索然地荡了两下,就下来了。周围的孩子们,也都无心再玩,各自回家去了。
上海这个百年老城,十里洋场,表面繁荣,但各种公共设施,尤其是地下水道,陈旧而淤塞,只需一场大雨,下水道必然堵塞,街上积满了水,有的地方竟达一尺之深,普通人家不得不用一个圆的木盆当舟船,运送孩子们上学。孩子们放学回来,在水中互相泼水嬉戏,好像在游泳池里打水仗一样,丝毫也没有觉得水灾对每个家庭带来的麻烦和损失有多严重。住在高楼大厦的洋人们在阳台上,居高临下,观赏水景。他们将一把一把的铜板(相当于美国的一分钱PENNY)由空中撒向水中,穷孩子们钻进水里,你争我夺,在高楼阳台上的大人小孩们拍手哈哈大笑。此情此景,又加上公园里的秋千风波,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有了很大的阴影。
我们弄堂对面是英国人开的洋行(现在叫外企),每天都有汽车进进出出,将洋货由海外运来,卖给上海的市民,赚中国人的钱。那时所有的东西都冠以洋:洋火(火柴),洋车(人力车),洋油灯(煤油灯),洋人,洋房,洋娃娃……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暗中策划了一场向“帝国主义者”开火的复仇计划。放学了,我们四个人每人准备了一个弹弓,几颗子弹(小石头子),埋伏在弄堂的铁们后(上海弄堂,几户人家共享一个大铁们,作为运大件家具用,平时不开,进出走后门)一俟洋人的汽车进入射程,我们就同时出击。
不久,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停在对面的洋行,一个衣冠楚楚绅士模样的人,下车走进洋行。我们认为时机已到,一声令下,万箭齐发,打得那部黑轿车弹痕累累,玻璃也碎了好几块。命中目标,完成“复仇”任务,我们各自逃回了自己的家中,静观洋人的动静。那洋人出门后拿起车钥匙正准备开车门时,发现了车上的弹痕和破碎的玻璃,举起手高声大骂:GOD DAMM!SON OF BITCH!(该死的!狗娘养的!) 先前那副绅士风度已荡然无存,开着那残破不堪的汽车灰溜溜地远去了。
之后我们还想出些招儿,不定期地出手(复仇),以解我们心中的怨气。(待续)
点阅【黑与红】系列文章。
责任编辑:马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