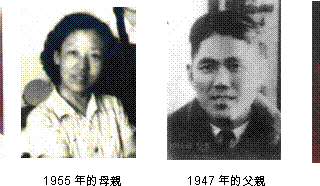第二节:我的少年(6)
(五)与父亲的最后一见
在山梁上,下面的人尽收眼底。我紧张地睁大眼搜寻。哨兵没有理会我们,他们正在聊天。我蹲在草丛中,拉着外婆和余妈妈叫她们蹲下,她们立刻会意的弯下了腰。拨开乱草,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
我看见他了——我的父亲!
他穿着灰色的劳改服,脚上套着脚镣,形容憔悴,步履艰难,头剃得光光的,脸却是黑沉沉的,好像很久都没有剃过胡须。
我心中一阵酸楚,眼泪涌了出来。回头看外婆,她布满皱纹的脸上,热泪纵横。
父亲埋着头一下一下地挥动着铁镐,此时他肯定不会想到,他日夜思念的亲人,正在山颠的草丛中用泪眼凝视着他。
我们的行踪终于被对面山崖上的哨兵看见了,他们向我们高声吼叫,使劲地挥手,要我们立即离去。
我们不得不拖着沉重的步子,在余妈妈的携领下沿原路慢慢退了回去。
这便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接下来一个星期天,外婆又在余妈妈的携扶下,来到了法院。法院的值班人索要单位的介绍信,余妈妈解释说不知道要开证明才能见到人。人虽没有见到,但在余妈妈好说歹说下,看守收下了外婆给父亲带来的那一联肥皂、一盒草纸和一块毛巾。
当外婆询问父亲究竟犯了什么罪时,那位看守不耐烦地说:“他的案子不能向你们家属说,你回去吧。”
母亲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终于向法院提出了“离婚”诉讼。我们都不理解,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她想,只有这样,才能释下沉重的精神枷锁吧。
半年以后,我们接到了父亲从狱中寄来的信,收信人竟是我的名字。信上的第一句话,就是他已同意和母亲离婚。他告诉我他已判了徒刑,现在正在西康的一个伐木场劳动改造。他说他一切都好,身体也很棒,相信我们一定还有相会的一天,只是需要争取了。
他在信的最后写着:“平儿,爸爸对不起你,没能使你成人便要洒手了。所幸的是你已经长大,已经懂事。今后一定要好好念书,照顾好外婆和妈妈,生活的重担就交给你了……”
我真傻!真的,我怎么就没有看出那洒满纸页的泪痕呢?我怎么就没有查觉到他暗藏着与世永别的绝望呢?我还真以为他会健健康康活在人间,并且终有一天和我们相聚。
我犯了与母亲完全相同的错误,我没有回他的信,轻率地认为,为了我自己今后的生存和前途,我不能公开地表示对他的眷恋之情!
倘如当时我就洞察了毛泽东的一切阳谋,断然地表示了对父亲的亲情,并且写信甚至千里迢迢去西康探望他,也许他会在亲情的抚慰下坚强地活下去。我们也许真的还会相逢。当时我幼稚的幻想,让我付出了终身悔恨的代价!
父亲已离开我半个世纪了,但他的慈父之爱始终没有离开过我,并且让我自责曾经对他的不敬不孝。
童真无奈的我,幼小的心灵却在知识的海洋中寻求着寄托。当我刚刚泅入其中,便被光怪陆离的科学现象所吸引,生命的、化学的、物理的、电磁的、宇宙的。
当一群人联合起来,打倒另一群人,杀戮、掠夺,产生出可怕的人吃人社会。一部分腐败、穷奢极欲,一部分受凌辱、被杀,这种无休止的人类自杀悲剧何时才能了结?人类为什么不能洗刷这种欺压同胞、欺压同类的污迹,而效仿那些向大自然讨索宇宙玄机的科学家?
我虽不可能像当时的一些年轻人,把毛泽东和共产党当成偶像和再生父母那么崇拜,但也还并不敌视它。既不敢,也不愿。我只是从自身的不幸经历中,产生出对政治敬若鬼神的距离和戒惧罢了。
后来,母亲常以父亲的悲剧告诫我远离政治,甚至不要再像他那样从事教育,他们体会到了教育者的失落和痛苦。我下定决心,不问政治、埋头苦读,立志成为一名自然科学家,或者成为设计师、工程师。(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