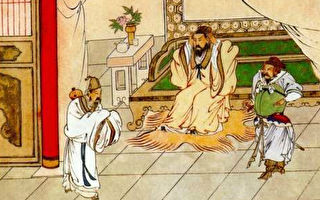* 引言
《水浒传》是中国“四大古典小说”之一,也是四部古典小说中最具争议性的一本,一些和《水浒传》有关的问题(例如它的作者问题、版本问题、历史背景问题)至今仍未有定论。不过,《水浒传》中引起争议的地方不仅在于上述这些形式上的问题,还在于它的思想的复杂性。本文尝试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水浒传》之所以具争议性,乃在于它的中心内容触及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造反,而且由于小说中的造反者 –梁山好汉造反不彻底(他们最后是接受“招安”–即向朝廷投降,而且还奉朝廷之命镇压其它造反者),这就更引起后世论者的争议,持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对《水浒传》可以有截然相反的评价。其实,各派论者不仅在评价这部小说的思想性方面存在分歧,他们对这本小说的情节和人物的诠释也如南辕北辙,例如对于小说中的主角–宋江究竟属于什么样的人,简直是众说纷纭,忠奸贤愚兼而有之。
《水浒传》还有另一方面的复杂性,即它存在大量“糟粕”(小说中一些残忍甚至有歪正道的情节)。这一点使《水浒传》跟《西游记》很不同,《西游记》在某程度上可以被当作童话,而《水浒传》则多的是“儿童不宜”的情节,离“童真”相去甚远。无怪乎坊间会出现一些略去“糟粕”、专供青少年阅读的《洁本水浒传》或《水浒少年版》。正因为有“洁本”和“少年版”的存在,才更见《水浒传》的复杂性。以下本文将分两部分讨论《水浒传》的上述两种复杂性。
*《水浒传》复杂性来源之一:对故事情节及主角的诠释及评价
造反主题
诚如笔者在“引言”中所言,《水浒传》的中心内容是关于造反。造反在古代社会固然是大逆不道的,即使在现代社会,造反也被视为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像。除非有十分充分的理据,否则难以得到社会大多数人的认同。事实上,在古今中外,造反始终难以与犯罪或其它反社会行为划清界线。可以这样说,《水浒传》的造反主题对一般读者心中的维护现有社会制度的理念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注1)。我们试拿《水浒传》跟《西游记》和《三国演义》作一比较。后两部小说的主题思想都是维护既有的社会秩序,《西游记》的开首虽然讲述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造反”行径,但最终孙悟空还是“回归正途”,保护师父取西经,还一路儆恶惩奸,最后得以“修成正果”;《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拥刘反曹”,就更加是维护封建正统。相比之下,《水浒传》的造反主题便显得非常大逆不道。虽然梁山好汉最终是“改邪归正”,接受朝廷招安,并且奉朝廷命讨伐其它造反者,但切勿忘记《水浒传》最为人熟知和津津乐道的部分还是它的前半部分–即讲述梁山聚义的部分(注2 )。梁山好汉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帮落草为寇的造反者,而非改邪归正的朝廷鹰犬。这一点正是梁山好汉区别于孙悟空之处。
正由于《水浒传》的造反主题对读者维护社会秩序的理念构成正面冲击,《水浒传》的读者在心理上须经历一个把梁山好汉的行径“合理化”的过程(除非该名读者是抱着仇视“梁山贼”的心态读这本小说),即同意《水浒传》所描写的时代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因而梁山好汉造反有理。而且请注意,这是一个有条件的合理化过程,即一般读者并非认同一切造反行为,而只是认同在“官逼”情况下的“民反”行为。因此一位《水浒传》的读者可以一方面赞同梁山好汉的造反行径,而另一方面却对发生在他周遭现实环境的反社会行为持否定态度。同样,一位热爱《水浒传》的家长或教师可以一方面鼓励他的孩子或学生读《水浒传》,却同时教导他们做个循规蹈矩的乖孩子,这就是《水浒传》复杂性之所在。相比之下,《西游记》和《三国演义》的读者在心理上无须经历上述合理化过程,因为尊师重道、儆恶惩奸、维护忠义之道在一般读者心目中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
虽然《水浒传》如上所述具有大逆不道的主题,可是历来它却又能为广大读者接受,甚至跻身于“中国四大古典小说”之林。其原因何在?除了因为它有很高的文学技巧外,笔者认为那是由于它的造反主题切合了广大读者的一种需要,就是对压迫的控诉。事实上,这种需要不仅在中国存在,在外国也存在,所以外国亦有关于“侠盗”的小说(如罗宾汉),只是其艺术性和影响力远远不及中国的《水浒传》而已。在古代社会,尤其是政治腐败或处于异族压迫的时期,封建剥削沉重,贪官污吏横行,广大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敢怒而不敢言,而《水浒传》正好为他们出了一口污气。在现代社会,由于几乎世界每个国家都曾经过革命的洗礼,人们对“造反/革命”等反政府行为有更大的理解和容忍度,因此即使生活在现今政治较为清明的国家里,也能认同古代造反者的行为。
事实上,在古代《水浒传》也确曾成为造反者的崇拜或模仿对象。例如明末和清代的造反者以至秘密帮会(如天地会)都曾模仿梁山的组织形式或梁山人物的名号。正由于《水浒传》是这么深入民心,而其造反思想又对封建秩序构成一定威胁,《水浒传》自它诞生之日起便屡遭统治者以“诲盗”为由被查禁毁版。据民间传说,施耐庵本人便因写作此书而遭明太祖下令辑捕,清朝的几代皇帝更曾下令将《水浒传》毁版。可是《水浒传》仍是禁而不绝,由此可见它的造反主题在旧社会中确有极大的认受性。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即使立场极端反动、极度仇视梁山泊的《水浒》续书《荡寇志》,也有官迫民反的情节。例如该书开场便讲述道人陈希真的女儿陈丽卿为高衙内垂涎,父女被迫落草猿臂寨,最后获朝廷招安。最有趣的是,该书不但没有为奸臣蔡京、高俅等辩护,而且还特地安排林冲烹杀高衙内和宋徽宗贬杀奸臣等情节。由此可见,即使是从统治阶级立场出发的文人,也不得不承认揭竿起义有时确是迫不得已的,而杀奸臣亦是大快人心的。它跟《水浒传》的分歧在于,《荡寇志》的作者其实是在宣扬一种起义者的“模范”,认为只有像陈希真那样不干绿林勾当、专心等待朝廷招安才算是值得原谅的造反者的应有行为。至于像梁山泊那样的造反者,则只是十恶不赦的盗贼,必须斩尽杀绝。
其实,界定某一反政府行为的性质(究竟是革命、起义、抗暴,还是叛逆、暴乱、盗贼行为)并不总是清晰判然的,很多时候是数者兼备,亦“正”亦“邪”。同样,《水浒传》所宣扬的意识也不能简单地划归“革命”或“诲盗”的范畴。正如历史上被定性为“革命”或“起义”的反政府队伍中少不免也会搀杂真正的盗匪黑帮( 例如在支持孙中山革命的组织中便有黑帮组织),同样,梁山一百○八人也包含诸色人等,既有饱受压迫、被迫落草的林冲和见义勇为、打抱不平的鲁智深,亦有专做鼠窃狗偷行径的时迁和开人肉作坊的孙二娘。这就为评价《水浒传》增加困难,所以笔者认为,《水浒传》的亦正亦邪双重性其实只是反映了历史上众多反政府行为的亦正亦邪双重性。因此,《水浒传》的复杂性乃在于其历史真实性。
* 受招安和征四寇情节
如果《水浒传》的故事止于梁山聚义(即最通行的“七十回本”),或者叙说梁山最后被官军荡平,或者违反历史事实,叙说梁山军最终推翻宋朝,那么它还不是那么具争议性,因为这样梁山好汉毕竟贯彻了他们的造反事业(不管是成是败)。可是《水浒传》的作者偏要安排梁山好汉归顺朝廷(即受招安),再进而征讨其它造反者( 注3),这就引起后世的无穷争议。这些争议主要是围绕对梁山泊的中心人物-宋江的评价,大致上可以归纳为五种意见,其中前两种是古代的观点,后三种则是现代的观点。
第一种意见认为宋江是“替天行道”的“忠义之士”。这里“替天行道”的意思不是要取天子的地位而代之,而是由于奸臣当道,天子遭受蒙蔽,导致天下大乱,梁山好汉的任务就是要帮助天子诛除奸佞,恢复朝纲。因此宋江的目的不是要推翻宋朝,而是本着一片忠义之心,矢志报效朝廷,并且还要镇压其它不忠于宋廷的造反者。概括言之,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种观点正反映了“一百二十回本”的精神,因为“一百二十回本”的后半部正是讲述梁山好汉如何在奸臣的百般阻挠外,仍然不负朝廷所托,讨平边患和叛匪。是故“一百二十回本”又称《忠义水浒全传》。
第二种意见认为宋江是“贼首”和奸恶之徒,删节《水浒传》的清代文人金圣叹是这种观点的代表。被删去的后五十回是叙述梁山好汉受招安和报效朝廷,正是显示宋江“忠义”的情节。因此金圣叹删去后五十回除了因为其情节、文字较前七十回拙劣外,其实还有一笔勾销宋江“忠义”性质的用意。除了删去原著后半部分外,金圣叹还窜改《水浒传》的内容。虽然他所窜改的地方一般只是一些细微部分,而非主要的故事情节,但其用意是要透过某些细节显出宋江的奸猾,以达到某种“微言大义”的效果。例如他对跟随晁盖前往攻打曾头市的头领名单作了某些更动,使名单中的头领尽是当初跟随晁盖上山或拥立晁盖的头领,以此暗示梁山已分裂为“亲晁盖派”和“亲宋江派”,而只有前者跟随晁盖出战。这样金圣叹便塑造了一个架空并篡夺晁盖领导权的宋江形象。
第三种意见认为宋江是农民起义军领袖,这主要是就前七十回而说的,因为前七十回的主要情节正是讲述梁山好汉(包括宋江)如何被迫上梁山,并进行反抗官军,乃至攻州夺府、杀害朝廷命官的活动。这种意见是中共建政初年内地的主流意见,这可能是由于当时一般人只知有“七十回本”,因而只着重看宋江造反的一面。虽然宋江的受招安意图在前七十回已略见端倪(注4),但由于“七十回本”是以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为结局,正是造反的巅峰期,因此造反主题非常突出,而受招安主题则被掩盖了。
第四种意见认为宋江是投降派,是农民起义的叛徒。这种观点最盛行于文革动乱时期,尤其是在“四人帮”发动“评水浒”运动之后。这种观点可以毛泽东对《水浒》的批示以及文革时期多篇批判宋江的文章或刊物(例如《宋江析》)作为代表。毛泽东的批示是这样的: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 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宋江析》则对宋江上梁山前的事迹一直到成为梁山泊主并受招安的过程详加分析,指出宋江根本就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上梁山只是权宜之计,他的最终目标还是向朝廷投降。该书还采纳了金圣叹批改《水浒》的很多观点,把宋江说成是处心积虑要架空晁盖,夺取梁山领导权以遂其投降意愿。此外,该书还指出梁山一伙曾围绕受招安一事分裂为投降派(以宋江、卢俊义为首)和反投降派(包括鲁智深、李逵等人),并且发生过激烈斗争,但最后还是投降派取得胜利,断送了梁山的起义事业,最后还成为朝廷的鹰犬,帮手镇压其它坚定不移的农民起义队伍。
除了上述四种观点外,近年内地电视台拍摄的《水浒传》剧集其实代表了又一种新观点。该电视剧把宋江塑造成一个带有两面性的人物。一方面他是愚忠的,他的最大志向是为国家出力,因此竭力主张受招安,但另一方面,该剧集中的宋江形象也并不算太坏。例如它没有把宋江塑造成一个假忠假义、玩弄权术的人物,也没有把他塑造成篡夺梁山领导权并出卖梁山事业的叛徒,他接受朝廷招安的出发点除了“忠心报答赵官家”外,也是为弟兄的出路设想。在奉派征讨方腊的过程中,电视剧也没有把宋江塑造成穷凶极恶的朝廷鹰犬,而是特地加插了一段宋江劝方腊投降以避免生灵涂炭的片段。最后,当宋江看到朝廷滥杀被俘的造反士兵时,他还是痛心疾首地为这些战俘求情。
笔者认为,出现上述多种宋江形象,一方面是由于《水浒传》本来是来自话本和杂剧,而这些话本和杂剧又是集体创作的结果;另一方面亦由于原著中的宋江其实是一个颇为矛盾的人物,他没有帝王思想(而且还有忠君爱国的思想),不可能把梁山建设成真正的造反队伍,但是他的“愚忠”又未至于令他甘愿作一个贴贴服服的顺民,否则他便不会在何涛前往捉拿晁盖之际“担着血海的干系”向晁盖通风报信,也不会在成为梁山一员后多次领兵攻打州县。因此可以说,宋江是一个既“忠”且“奸”的角色(不论是从朝廷的角度还是从造反者的角度出发),任何对宋江的简单化评价,把他定性为忠义之士、奸恶之徒、坚定不移的农民起义领袖或处心积虑的投降派,都会失诸偏颇。其实历史事实又何尝不是如此?对历史上的很多事件和人物,同样都不能作简单化评价。因此,笔者认为,《水浒传》的复杂性其实反映了现实历史的复杂性。
《水浒传》的矛盾不仅表现在对宋江的评价上,亦表现在对梁山好汉的出路问题的意见上。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宋江根本没有帝王思想。在中国古代,志在推翻朝廷或割据一方的造反者(如陈胜、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乃至《水浒传》也有描述的方腊),无一例外都有帝王思想,我们无法设想这些造反者会建立一套“共和制度”,或者《桃花源记》所描述的那种“乌托邦”式社会,这是时代的局限性。既然宋江根本没有帝王思想,梁山事业的发展空间便非常有限,因为他们不可能建立一个与宋朝分庭抗礼的新政权。要么在较佳的条件下接受招安,要么继续啸聚于梁山,但时常有朝廷派军前来围剿之虞。结果宋江选择了前者。
即使撇除宋江的因素,单单讨论什么才是梁山好汉的最佳出路,这仍然是充满矛盾的问题。接受招安似乎不是最佳的出路,因为正如《水浒全传》所描述的,接受招安的大多数梁山好汉最终只是落得狡兔死,走狗烹的悲惨结局。唯一能全身而退的方法似乎只有像公孙胜那样遁迹江湖,或者像李俊那样远走他方,另觅干净土,可是这样做似乎埋没了梁山好汉的一身本事,某些希望有所作为的梁山头领似乎也不甘心选择走这条路。而按照“革命火红”年代的说法,这是放弃现实生活中的斗争,因而也是不可取的。若果不接受招安,便只有反抗到底。过去在火红年代,一面倒认为这是唯一“政治正确”的出路。可是正如上段所述,中国古代的“彻底”造反者无一例外都具有帝王思想,一旦造反成功只会建立另一个封建王朝,按照火红年代的标准说法,这是地主阶级篡夺了农民起义的成果,因此梁山英雄似乎只有奋战失败才是最“政治正确”的出路!或许这正反映了中国古代农民造反的局限性和悲剧性。
《水浒传》的上述矛盾为后世续写或改写《水浒传》的作者提供了无穷的发挥空间,因而出现了多种续书或改编的《水浒传》,这些作品所描绘的宋江形象和安排的梁山结局各有不同,代表了各种不同的评价(注5)。在描绘宋江形象方面,主要有正面和反面两种,其中反面的形象又分两种类型,有的把宋江描绘为假忠假义的奸恶之徒(如《荡寇志》、《新水浒传》、《残水浒》),而有的则把他描绘为断送梁山事业的叛徒(如褚同庆的《水浒新传》)。而正面的描绘则更为多种多样,有的把宋江描绘为忠君爱国之士(如《征四寇》、《水浒中传》),有的把他描绘为爱国但不一定忠君的人物,其爱国表现为领导众好汉参加抗辽(如《水浒别传》)或抗金战争(如张恨水的《水浒新传》)。有的则把他描绘为成功的起义领袖,深得众头领拥护(如《水泊梁山》),甚至深受百姓爱戴(如《古本水浒传》)。
在梁山好汉的结局方面,有的续书或改编根本不提众好汉受招安的情节,而是以梁山大聚义结局(如《古本水浒传》、《水泊梁山》);有的只轻轻带过梁山受招安的情节便告结束(如《新水浒传》)。有的则详细描述梁山好汉在受招安问题上分裂为投降派和反投降派,不过即使主题相同,角色安排却可以迥异,例如褚同庆的《水浒新传》以宋江为投降派的首领;而《残水浒》却以宋江为反投降派的首领(但宋江最后还是为张叔夜所擒) 。《荡寇志》则讲述宋江曾试图向朝廷投降,但终究未能成事,最后以张叔夜讨平梁山,杀尽梁山众头领结束。上述诸书都是以梁山事业失败而结束的,其它书则继续讲述梁山好汉在受招安后的发展。最经典的莫如《征四寇》和《水浒中传》讲述梁山好汉讨伐其它造反者,最后损兵折将,宋江还落得狡兔死,走狗烹的收场。其它书虽亦有受招安情节,但没有讲述梁山好汉讨伐其它造反者,而是讲述他们参加抗辽或抗金战争。其中有讲述他们胜利的(如《水浒别传》),亦有讲述他们失败殉国的(如张恨水的《水浒新传》)。除此以外,还有一些续书说得更远,它们或是述说梁山余部或后人起义抗金的事迹(如《水浒后传》、《水浒别传》),或是述说宋江、卢俊义等人托世转生为杨么、王摩,在洞庭湖再度造反,最后为岳飞剿平(《后水浒传》)。由以上所述可见,一部《水浒》竟然派生出这么多续书和改编,其中有些书的立场更是截然相反,这种现象在世界文学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而这亦正正反映了《水浒传》思想的复杂性。
* 《水浒传》复杂性来源之二:糟粕
造成《水浒传》思想复杂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存在大量糟粕,《水浒传》的糟粕大致上可归为以下几类:
(一)残忍行为
《水浒传》所记载的某些杀人行为是相当残忍的(本文不拟抄录《水浒传》中有关残忍行为的文字,请读者自行查阅原著),例如李逵杀黄文炳、石秀杀潘巧云,都使用极之残忍的方法。如果陷害宋江的黄文炳还算是死有余辜的话,那么背夫偷汉和以馋言迫走石秀的潘巧云却是罪不至死,更加不至于要用那么残忍的手段治死她。事实上,后世对石秀的评论,多有认为他的手段过于狠毒。如果上述两个例子只属“个别事例”,那么剖腹剜心却是绿林上的惯常刑罚,例如射杀晁盖的史文恭便遭受这种极刑。如果绿林中人用这些残酷刑罚来对待敌人或仇家还算情有可原,那么十字坡孙二娘和揭阳岭李立迷晕过路客商并拿来作人肉馒头,以及清风山强人捉拿过路人剖心制“醒酒汤”,这些行径便实在难教人认同了。事实上,正由于孙二娘、李立和清风山强人的行径,他们几乎曾害死武松、鲁智深和宋江。
(二)滥杀无辜
假如有些人认为不能用现代人的标准来衡量古代人的行为,那么以下所述的滥杀无辜、盗贼行径和有违正理就不是古今尺度差异的问题。梁山泊作为一伙造反者,少不免是要杀人的,而攻城略地时也难免会殃及无辜百姓。可是《水浒传》中描写的很多杀人行为却大大超出上述的“容许范围”,而是属于滥杀无辜,其中尤以黑旋风李逵为甚。李逵在上阵时奋勇杀敌,这是人所称道的,可是李逵在杀得性起时,往往敌友不分,连己方的兵士也错杀。如果李逵在战场上错杀战友还可以解释为混乱的环境使他判断错误,那么以下四宗杀人事件便实在难以再作辩解了。第一宗是为了迫朱仝上梁山而杀害沧州的小衙内,杀害无辜幼童无疑是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更何况那名幼童又是朱仝所爱,所以当一向敦品仁厚的朱仝在梁山遇见李逵时,他几乎要和李逵拚命。第二宗是为了迫公孙胜回梁山而企图杀害其师傅罗真人。虽然结果李逵还是杀不了懂得法术的罗真人(而且还被其戏弄),但是李逵的行径实在有违朋友之道。第三宗是在三打祝家庄战事即将完结之际,把已与梁山达成和议,并且正要把祝家三少爷擒献梁山以示友好的扈家庄阖庄老小全部杀害。此一行径不仅残忍,而且违反了梁山与扈家庄的协议,实在有损梁山信誉。第四宗则是杀害有意投奔梁山的韩伯龙。假如上述三宗杀人事件还勉强算是杀害“异己分子”,那么杀害韩伯龙就真是莫名其妙。虽然原著解释韩伯龙之死是由于他不在一百○八人数内,但撇开这些迷信说法,我们不得不说李逵的杀人行径已到了嗜杀成性的病态地步。
其实除了李逵外,梁山其它头领也有滥杀无辜的行为,例如前述的孙二娘、李立、清风山强人,以及以下会次第提到的杀人越货盗贼行径、为迫人落草而不惜杀人并嫁祸他人的行径等。这些都留待各部分详细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三)盗贼和恶霸行为
历来歌颂《水浒传》的人都把梁山人物说成是锄强扶弱、劫富济贫或者为世所迫,起而反抗的好汉。诚然,在梁山众多头领中,确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真英雄,如鲁智深、石秀等是,尤其是鲁智深,为了帮助素未谋面的金老头父女和好友林冲,竟致两次被迫流亡。此外,也有本性善良,但为奸人所害不得不迫上梁山的好汉,如林冲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人物。不过,如果细心考究,我们亦不难发现,在梁山众头领中,亦不乏绿林(或江洋)大盗,他们有些人(虽非全部)的行径实难以称得上是“好汉”。事实上,梁山便是由多个山寨的人马汇合而成的。虽说这些人可能都是为世所迫而落草为寇,但是他们之中有些人的行径却接近恶匪多于“侠盗”,这方面的例子包括:梁山早年规定,新入伙者须在山下杀一个人,取其首级送上山作为“投名状”;张横在浔阳江上当水贼,在劫人财物后还迫人跳船,宋江便差点被他迫得淹死于浔阳江中;周通在桃花庄强娶刘太公女儿作压寨夫人,其行径跟某些贪官恶霸强抢民女没有太大分别。
即使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智取生辰纲”事件,本质上也是一种“黑吃黑”的强盗行径,而非某些人所说的“劫富济贫”。虽然吴用等人曾以生辰纲为“不义之财,取之何碍”作为他们劫夺生辰纲的“合理化解释”,不过根据《水浒传》的记载,他们劫夺生辰纲却完全没有劫富济贫的意思,而是准备私分,这从公孙胜对晁盖所说“此一套富贵,不可错过”便可清楚看出。因此严格地说,他们只是劫“不义之财”以遂其私心。虽然后来宋江在攻州夺府后确有开仓赈济穷民之举,不过这不能说明梁山从来都是以劫富济贫为宗旨的。而这一点也进一步证明梁山泊是一群品流复杂,亦正亦邪的人物。
除了盗匪外,梁山头领中也有一些人本来是土豪恶霸或甚至恶吏。例如浔阳镇上的穆弘、穆春兄弟便是典型的恶霸,当薛永在镇上卖艺而宋江给他赏银时,穆氏兄弟竟以薛永未拜见他们而追打薛永和宋江(其实这里应有勒索“保护费”的用意)。而曾经担任江州两院押牢节级的戴宗,虽说不上是贪官,但也是一名恶吏。当宋江被押解至江州牢城时,戴宗便首先向宋江勒索赏银,这种行为其实跟林冲在沧州牢城营遇到的那名差拨没有多大差异。
有些人或许不同意笔者在上面的评论,认为笔者是在“苛责”梁山好汉,毕竟他们不是完人。问题的关键正在于此,以往某些歌颂《水浒传》的评论实在过于美化梁山人物,把他们说成是“怪盗一枝梅”式的侠盗。其实梁山好汉既然大多出身于绿林或市井,难免会沾染江湖习气,干一些强盗勾当或恃强凌弱的事。本文无意抹黑或看扁梁山人物,但也反对过于美化原著中的梁山人物(惟《水浒传》的改编或续书中的人物则另作别论,因为那已不是原著作者的意思)。本文只希望还《水浒传》以本来面目。
(四)有歪正理或侠义之道的行为
《水浒传》中最受人非议的是一些有歪正理或侠义之道的行为,这主要表现在梁山人物为了迫其它人落草为寇,有时竟不择手段,做一些有违侠义之道的事,甚至嫁祸当事人,令他走投无路,唯有落草为寇。这一方面的例子除了上述李逵杀害小衙内迫朱仝上梁山外,手段最肮脏的当推宋江迫秦明落草清风山的手法。为断绝秦明归路,宋江竟派人假扮秦明,在青州外围屠杀了数百家平民,害得秦明一家为官府所杀,无处容身,唯有落草为寇。常言道“盗亦有道”,宋江在这件事上实在是完全违反正道。后世某些评论家把宋江定性为奸恶之徒,“秦明事件”相信是其中一个重要论据。
除了上述例子外,《水浒传》还记载了其它以不正当手段迫人上梁山的事件。举其要者如为迫徐宁上山,派遣时迁前往盗取其家传之宝雁翎甲,引徐宁追捕时迁,然后设法迷晕徐宁,将其挟持上山,并派人假扮徐宁为盗劫夺客商,以断其归路。此外,萧让、金大坚也是在非自愿情况下被哄骗上山的。
梁山部分头领的行为也非好汉所为。除了前述周通强娶民女外,最为人诟病的当推身居五虎上将之一,自号“风流万户侯”的董平。董平之所以上梁山除了因为被梁山军生擒被迫投降外,主要还是为了抢夺东平府太守程万里的女儿。为此,他竟在东平府城破之时径自杀害程万里全家,夺其女儿。由此可见,董平实在难以称得上是英雄,他所做的比起垂涎林冲妻子美色的高衙内来说,真是有过之无不及。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作出以下的设想,假如《水浒传》的作者不是把程万里说成是东平府太守,而是某名梁山头领的亲属,那么董平便自然成为梁山的敌人,而且是死有余辜的敌人。因此这里带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读者对小说中人物的好恶,很大程度上视乎作者是“站在谁的一边” 。同样是夺人妻女,淫辱良家妇女的绿林强人,周通、董平可以成为梁山“好”汉;而瓦罐寺的崔道成和邱小乙、蜈蚣岭的王道人、牛头山的王江和董海等却成为反面人物,为梁山英雄所杀。同样是劫夺客商、迫人跳江的水贼,浔阳江的张横可以成为梁山头领,而扬子江的张旺和孙五却要做梁山头领张顺的刀下鬼,其分别只在于前者是张顺的哥哥,而后者却“有眼不识泰山”,竟然打劫张顺。
(五)不合情理/不近人情的情节
历来评论《水浒传》的人都有指出《水浒传》某些不合情理的地方,例如地理上的错误,不过这些都只是无伤大雅的错误。较严重的还是一些不近人情的情节,令某些梁山英雄成了无感情或没心肝的人。其中最为人诟病者当推扈三娘在全家为李逵所杀的情况下,竟然还应允下嫁一个“五短身材,一双光眼”的矮脚虎王英。后世评论《水浒传》作者安排以一丈青嫁王矮虎,多有认为这是对一丈青的戏谑(假如说不上是“委屈”),其实这里何止戏谑?而《水浒传》作者对此的解释只是扈三娘“见宋江义气深重,推却不得”,试问灭门之仇在前,义将安在?这不能不说是《水浒传》的一大败笔。反倒是朱仝在上梁山后,一见杀害小衙内的李逵便要和他伙拼,这才显得朱仝是有血有肉、大仁大义的真英雄。
其它不近人情的情节还有秦明在被宋江害得家破人亡返回清风山后,外号“霹雳火”的他不但没有追究宋江等人的行为,而且还接受宋江作媒,娶了花荣的妹子作继室,这样描写秦明实在太不近人情了。另外又如梁山大军在活捉高俅后,宋江要将之释放,而与高俅有血海深仇的林冲竟然不发一言。《水浒全传》只是描写林冲对高俅“怒目而视”,这样未免把林冲描写得太窝囊了。
正如《水浒传》的造反和招安情节给后世的续书和改编者以无穷的发挥空间,同样《水浒传》的糟粕也成为某些续书或改编针对的对象。对于原著的糟粕,大致可分为三种处理手法。第一种是索性删去这些糟粕,例如《洁本水浒传》和《水浒少年版》便是采取这种处理手法。第二种是竭力改善梁山好汉的形象。在这一方面,改编和续书的具体处理手法又各有不同。由于续书无法对原著作任何改动,因此它们只能通过描述梁山好汉的义举突出梁山人物的正面形象,藉以掩盖原著糟粕中的负面形象。由于《水浒传》的历史背景正是北宋末年内忧外患交煎之际,有几部续书便选择描述梁山好汉参加抗辽或抗金战争,藉以突出他们的爱国形象(包括《水浒后传》、《水浒外传》和张恨水的《水浒新传》;此外,《征四寇》和褚同庆的《水浒新传》也有梁山好汉抗辽的情节)。其中张恨水的《水浒新传》更是一部“借古讽今”之作,该书创作于日本侵华时期,其主旨便是借描述梁山英雄的抗金事迹以激发同胞的抗日斗志。因此对梁山人物作了非常正面的描述,例如原著中两个备受争议的人物董平和宋江,在该书中都成了抗金烈士。其中有关宋江之死的情节,更大大改善宋江的形象。该书借用《水浒全传》中宋江被朝廷鸩杀的情节,描述宋江为金人所挟持,因不肯屈服金人而饮鸩自杀。这样一招“移花接木”,便把宋江原来的愚忠形象改为爱国烈士的形象。另一部续书《古本水浒传》则使用另一种手法。该书突出梁山好汉的锄强扶弱和劫富济贫形象,以五十回的篇幅大书特书梁山好汉在大聚义后的各种英雄事迹,从而掩盖了前七十回的某些负面形象。
如果续书所用的手法还只是补救,无法抹去原著的污点,那么《水浒传》的改编小说则是索性对原著中的糟粕进行改写。《水泊梁山》可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该书基本上沿袭原著的故事,但对原著的糟粕作大幅修改,尤其是对宋江形象的改善。例如在有关秦明落草的情节中,该书删去了宋江陷害秦明的情节,改为青州太守慕容彦达陷害秦明并杀其全家。此外,该书还特地加上宋江开导启迪清风山、浔阳江、揭阳岭强人的情节,劝他们放弃杀人不义勾当,这样既突出了宋江的正面领袖形象,亦显示梁山好汉虽出自绿林市井,但终能接受教化,改邪归“正”(成为不滥杀无辜的绿林豪杰)。
其实有很多民间传说都美化了梁山人物的形象,这可能是由于梁山人物已深入民心,老百姓希望他们的偶像真正是锄强扶弱、劫富济贫的英雄,因而产生了一些美化梁山人物的传说。例如,《水泊梁山的传说》一书便收集了山东一带有关梁山人物的传说,其中便有时迁、孙二娘劫富济贫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不见于原著的。除了民间传说外,历来有关《水浒》故事的电影或电视剧集都有美化梁山人物的倾向,它们或者略去原著的糟粕,或者索性改编原著的某些情节,使梁山人物的行为“合理化”。例如多年前香港某电视台拍摄的《迫上梁山》剧集便刻意改善浔阳江水贼张横的形象。原著本来述说张横假扮艄公载运客商渡江,在船到达江心时抢夺客商财物,并且还迫人跳船,不理他人死活。而该剧集则把这段情节改为张横把船划到近岸处才迫人跳船涉水上岸,这样便大大改善了张横的形象。其实这些美化正正反映了原著糟粕的不合理性。正是由于编剧觉得依照原著把这些糟粕拍摄出来,势必影响观众对梁山人物的观感,所以才选择“不忠”于原著。
上述两种手法的共同点是力求保持梁山英雄的正面形象,而第三种手法则是保留原著糟粕所突显的负面形象,并且加以发挥,描述梁山部分人物最后得到的“报应”,《荡寇志》和《残水浒》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诚如前述,《荡寇志》是一部由统治阶级立场出发的“反水浒传”,该书作者对梁山人物深恶痛绝,尤其对其首领宋江更极力描写其奸恶和虚伪面貌。该书还塑造了一众忠臣角色,以影照出宋江的假忠假义。最后该书以梁山被官军荡平结束,还特地加插宋江在逃亡时为渔民贾忠、贾义所捉的情节,以暗喻宋江终为假忠假义所误。《残水浒》则针对原著的糟粕而大加发挥。对于前述某些遭梁山头领灭门的女性人物,该书描述了她们的复仇过程。例如分别遭李逵和董平灭门的扈三娘和程小姐均亲手除灭仇人,其中作者更安排程小姐在毒杀董平后自杀身亡,这简直是塑造了一个烈女形象。对于宋江,该书同样塑造了一个假忠假义的形象,并且把宋江说成是用毒箭射杀晁天王的真凶,最后以宋江众叛亲离,其所作所为被众头领揭穿而结束。
以上笔者概述了《水浒传》的糟粕,目的是要说明《水浒传》是一部非常复杂的小说,任何简单化评价都会失诸偏颇。以往歌颂《水浒传》的评论都对这些糟粕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这不能准确反映《水浒传》的真貌。必须承认,《水浒传》的糟粕所反映的意识的确是不值得宣扬的不良意识,也确曾对社会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例如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便指出
“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
可是我们也不必因这此而全盘否定《水浒传》,把它斥为坏人心术的“晦盗”之书,因为《水浒传》除了这些糟粕外,也确曾记载梁山好汉的某些英雄事迹。而梁山人物的形象除了是绿林强盗外,也是不畏强权的造反者和重情重义的好汉。
笔者认为《水浒传》其实反映了中国古代农民造反者的真实一面,他们往往带有两面性,亦侠亦盗。诚如前述,在古代造反者往往难以跟盗贼或其它犯罪分子划清界线。因此《水浒传》的糟粕其实只是反映以下这一事实,历代的造反者往往是品流复杂的队伍,当中既有为势所迫,铤而走险的善良百姓;亦有生性强悍,愤世嫉俗的好汉;更有怙恶不悛,凶残成性的恶匪。除了品流复杂这一因素外,造反活动性质的改变也可能造成造反者的两面性。梁山泊便曾经历这种改变,从最初啸聚山林,打劫村坊的山贼,发展到后来以“替天行道”为旗帜的反政府军,实在经历了巨大转变。而经历这种转变的梁山头领,其性格行为亦多少会受到影响。就以开设人肉作坊的孙二娘为例,她在上二龙山后便已停止这种伤天害理的行为。到上梁山后进一步成为参与“替天行道”事业的一员,便更不会干这种有辱梁山名声的勾当。因此孙二娘的形象也从一个女魔头演变为女中豪杰。正由于梁山很多头领都曾经历这种变化,他们便具有两种形象。
其实,对江湖人物亦侠亦魔的描写并非《水浒传》所独有,当代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在其脍炙人口的小说《倚天屠龙记》中也有描写明教中人的各种乖戾乃至残忍行为(注6)。其实既然被称为“魔教”,我们便很难期望明教中人一个个都是正襟危坐的卫道之士。可是在《倚天屠龙记》中明教中人又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尤其是在张无忌成为教主之后),事实上,作者更把明教说成是领导汉人推翻蒙古外族统治的民族英雄,朱元璋便是明教的一分子。其实这里也有一个作者站在谁的一边的问题。假如《倚天屠龙记》的作者不是把主角张无忌安排为殷素素的儿子,而是龙门镖局当家都大锦的儿子,那么殷素素在小说中便成了女魔头和张无忌的复仇对象,即使作者丝毫没有改变对殷素素所作所为的描述。而更有趣的是,正如以《水浒传》为蓝本的电视剧集竭力美化梁山人物形象,几年前某台湾电视台拍摄的《倚天屠龙记》也竭力美化殷素素的形象。例如该剧集把殷素素滥杀龙门镖局八十多人的情节改为殷素素在混乱的情况下错杀龙门镖局中人,这样便大大减少殷素素的凶残形象。作为不同时代作家的两部作品,《水浒传》和《倚天屠龙记》竟然有这些相同之处,或许这就是描述亦正亦邪人物的小说的共通点。
* 结语
最后要提的是,《水浒传》的复杂性其实还表现在我们向青少年推介这部小说的态度上。究竟我们如何向青少年推介《水浒传》?毫无保留地推介这部小说?可是我们如何向他们解释书中的糟粕?假如青少年模仿梁山人物的反社会行为,我们作何反应?仅向青少年推介《洁本水浒传》或《少年版水浒传》?可是这样做只是隐恶扬善,令他们不能准确了解《水浒传》真实的一面。把《水浒传》视为洪水猛兽,不鼓励青少年阅读?这样做不啻是因噎废食。《水浒传》作为中国四大古典小说之一,在外国也享有崇高地位,纵然有一些糟粕,也不应全盘否定它的文学价值,亦不应抹杀梁山人物的正面形象。而且,历史已多次证明,把《水浒传》打为“禁书”只能产生反效果。
那么在推介《水浒传》时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笔者认为就让青少年自己去判断吧。笔者自七岁那年接触《水浒》故事起,便经历过从一面倒认为梁山头领全是正面人物到逐渐认清梁山人物的亦正亦邪性质的过程。其实,这不就是一个思想逐渐成熟的过程吗?在孩提时代,我们总认为这个世界非黑即白,所有故事、剧集中的人物非正即邪。但其实这个复杂世界可以存在亦正亦邪的事物,而这种认识只有在我们思想较为成熟后才能达到,正是基于这一点,笔者认为《水浒传》是一部思想性复杂的文学作品。
注1:请注意这里只是就“一般读者”而言。对于那些本身正从事反对现有社会制度行为或持有这种思想的人( 例如犯罪份子、黑帮人物、愤世嫉俗的人、革命份子、造反者等),或者正处于“革命火红”年代或“打砸抢”已成为家常便饭的社会来说,《水浒传》的造反主题当然并不构成冲击。
注2:清代文人金圣叹把《水浒传》的后半部分删去后,世上流传最广的《水浒传》版本便是这个删节本(世称“七十回本”)。七十回以后的故事已鲜为人知,笔者在幼年时便曾千辛万苦才觅得“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又称《水浒全传》),得以读到七十回以后的故事。只是直至近年,“一百二十回本”才重新为人所认识,不过即使如此,“七十回本”仍是当前最通行的《水浒传》版本。
注3:一般所称的“征四寇”中的“四寇”是指梁山归顺朝廷后奉命前往征讨的北方外患辽国以及三个造反者 –田虎、王庆、方腊。其中征辽的情节自然是虚构的,田虎、王庆更加史无记载,只有方腊真有其人。不过根据历史所载,讨平方腊的并非宋江。
注4:例如当宋江向被俘朝廷将领韩滔、呼延灼、关胜等劝降时,便告诉他们落草梁山只是权宜之计,“等朝廷见用,受了招安,那时尽忠报国,未为晚也”。同样,在宋江攻打华州向太尉宿元景借金铃吊挂时,对宿元景礼待有加,生怕得罪这位太尉,其目的也是要为他日受招安铺路。
注5:本文提到的《水浒传》续书和改编共有十一种,其中包括八种续书,即陈忱的《水浒后传》、青莲室主人的《后水浒传》、俞万春的《荡寇志》、姜鸿飞的《水浒中传》、王中文的《水浒别传》、程善之的《残水浒》、张恨水的《水浒新传》和《古本水浒传》(作者不知名),以及三种改编,即褚同庆的《水浒新传》、散发生的《新水浒传》和刘操南的《水泊梁山》。此外,还有一部《征四寇》(据传作者为罗贯中),即“一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传》的后五十回。不过《征四寇》究竟算是续书,还是原著的一部分,历来众说纷纭。
注6:例如“青翼蝠王”韦一笑需喝人血续命,“金毛狮王”谢逊曾滥杀无辜,与武林正派结下莫大仇怨;殷素素曾屠杀龙门镖局上下八十多人。(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