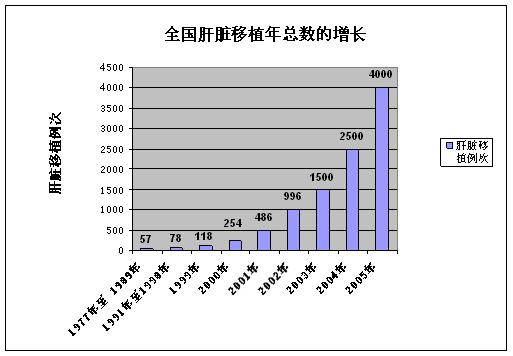陈云甫是星期四中午走的,直到星期一下午才回到农场。汤达凌客套地问过了病情,便拿出自己亲笔誊写的报告交给他审阅。陈云甫粗粗地看了一下,取出钢笔准备签名:反正事情只能是这么一个结局。这当儿,汤达凌无意中说了两句多余的话:
“报告写得不坏吧?这还是马伟章代劳的。”
陈云甫握笔的手轻微地抖嗦了一下。他放下钢笔,摸出烟斗,一边吸烟,一边把报告从头到尾认真地再审查一遍。说实在的,他最近在心里面对马伟章这个人已经有了新的看法。但他难以启口,因为全凭自己两只眼睛的直觉,还没有抓到什么真凭实据。而且,汤达凌的浅薄无知,再加上他那种狂妄的性格,进一步阻止了陈云甫把心里话掏出来。他希望从这份报告里发现什么明显的漏洞,可惜没有找到。于是他重新握紧了钢笔,无可奈何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汤达凌看到了陈云甫的心理反应,马上便为自己编造了一个理论:
“我想,我们应该更多地采用分化的政策,以右治右,这比我们自己直接管理更易奏效。”
汤达凌说过后,立即为自己发明了一个“以右治右”的理论感到几分的得意。这是在新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创造性的发展和运用,他想。
陈云甫一面向烟斗里添装香喷喷的烟丝,一面淡然地微笑。
“不错,马伟章这小伙子有几分才气,干劲也不小,说不定将来是个有所作为的人物。”
按照陈云甫真正的意思,这几句话应该正确地翻译成为:
“小心啊,同志!说不定你将来会败在马伟章手里。他也许才是历史上真正的胜利者,有一天回过头来把我们大大地嘲弄一番。”
“我也是这么想的。”汤达凌说,一面在陈云甫的名字下面洒脱地签划上了自己的名字。“像他这样在改造上有不少成绩的右派,又能帮助组织做些工作,就该第一批回校,起个带头作用。”
“大夫约我后天去洗肠。看来这次要比上回轻些。”陈云甫从嘴上取下烟斗,故意再一次提起自己的病,郁郁不乐地说。“我老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以后工作主要靠你一个人了,我在这里最多起个辅助配合的作用。”
“哪儿的话,离老还有十万八千里呢!再说,我一个人哪里挑得动这副担子啊!这些右派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人物。你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这里的工作非你领导不可。”汤达凌稍微停了一下,吸过一口烟以后继续侃侃地说:“我相信现代科学一定能医治好你的肠胃病。而且,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本身就是战胜一切疾病最有力的武器。史达林同志说过,共产党员都是特殊材料铸成的。”
“但愿果真如此。”陈云甫说,向汤达凌抛去一个和蔼宽厚的微笑。“我心里也很想为党多工作几年,只是身体不争气,老是和我过不去。”
陈云甫昨天晚上从一个朋友嘴里听说,汤达凌曾经多次在组织部长面前弹劾自己,说他革命意志衰退,借口有病,消极怠工,而且对党通过劳动改造右派的政策有严重的抵触情绪。他听了不但不生气,倒反而有几分高兴:他正希望组织部长把自己从这儿调走呢!现在他望着汤达凌,心里想道:
“我会给你让位的,孩子;也许我给你让位正好符合历史的要求。”
他这样想着,心里不免有点凄然黯然。就在今天早晨,他的妻子(她在一个重点中学担任校长兼党总支书记)因为工作不顺心,在家里唉声叹气。他对她说:
“我们这一代人挨过皮鞭、警棍和水龙头,为了夺取政权还曾坐过监狱,出色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现在可以无愧地交班了。但愿他们不要玷污了马克思的名字,但愿他们对得起千千万万壮烈地献出了自己生命的革命先烈。”
当时,他说过之后就后悔了,因为他的妻子,一个从事过多年地下工作的老党员,听到这些话竟然伤心地哭了。可是现在这个思想又慢慢地爬上了他的脑子。
汤达凌一点也没有觉察到陈云甫的心里。他很仔细地把报告折叠好,装在一个大信封里,悠然自得地点燃了一支烟,说道:
“现在到处都是拖拖拉拉,光说不干。我想今天就把这份请示报告送上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批下来呢!”
陈云甫突然控制不住自己地顶他道:
“什么时候批下来都一样啊!反正他又跑不了。”
“可不是。”汤达凌随口附和道,对着陈云甫笑了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里,他往哪儿跑呀!”
汤达凌转过身看看日历:他心里面还是希望愈快批下来愈好。
一个多月以后,大学党委办公室来了电话:同意将要求翻案的右派分子张恒直送去劳动教养;但是考虑到他本人的历史,可以酌情给予他最后一个认识错误的机会。
汤达凌接到这个电话自然很高兴:赏罚分明,这无疑会增加他个人在全体右派心目中的威信。
陈云甫也很满意:党委的决定留下了一个可以回旋的余地。他决定亲自出马,尽他的最大努力来挽救张恒直的命运。当天下午,趁着汤达凌下到北区队去发布指示的机会,他把张恒直叫来个别谈话。
“你写给市委的信我们已经看过了。”陈云甫说,轻轻地咳嗽了一声。“王本湘也写出了他个人对你的看法。党委慎重地研究了你的问题,认为原来的结论不能更改。”
张恒直好像被当头浇了一桶冰水。多少个不眠的夜晚!多少滴脑汁酿成的希望!在这一刹那间全部化为乌有了!他默默地坐在陈云甫的对面,感到浑身发冷。
陈云甫心不在焉地翻阅着王本湘的“作品”,停顿了很长时间,估计对方的头脑该稍微清醒过来了,这才继续说下去:
“你愿意回校念书,完成大学的学业吗?”
张恒直抬起头,困惑地望着陈云甫的脸好久好久,最后十分肯定地点点头。
“你想回校学习,就得好好改造。”陈云甫说,心理感到有了一线希望。“可是你直到今天还想翻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改造又从何谈起呢?”
张恒直的心头涌上种种痛苦复杂的感情。他似乎忽然获得了灵感,口才变得流利了。他说:
“我知道自己很需要改造,但这是人民内部思想意识的改造。我不是右派。我没有存心向党进攻。我给周善福写信的时候,心里根本就没有这种想法。我当时也不知道他就是右派。我的心像玻璃一样纯洁,但被人歪曲了。”
取暖用的炉子上放着一个水壶,此刻正在吱吱地响。陈云甫对着水壶看了很久,突然打破了沉默,换了一个话题。
“你哪一年入党的?”
“四七年一月,在苏北批准的。”
“你受过党多年的培养和教育了,自然应该懂得随时随地维护党的威信和荣誉,对不对?”
“我知道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天职。”
“你有没有想到过,你来农场以后的种种表现,——我指的主要是翻案——给党的威信带来了一定的损失?你知不知道,那些心怀不满的右派分子,都想从你身上捞到一根稻草,来达到攻击党、攻击反右斗争的目的?你是不自觉地在为他们服务了,做了他们想做而又不敢做的事。”
这席话像一根鞭子,狠很地抽打在张恒直的心坎上。他羞愧地低下了头,痛苦地说:
“我知道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我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损失。我对不起党。我请求组织处分我。不管多么重的处分,我都愿意接受。”
“现在组织上并不想处分你。只要你承认错误,就可以继续留在这儿改造,将来和大家一起回校念书。你们是一起来的,我希望也能一起回去。”
水壶里的闹声更响了,从壶口和壶盖的缝隙里冒出了大量热气。陈云甫懒洋洋地站起来,走过去把水壶提放在一边,盖上炉盖。他慢腾腾地走回自己的座位,一边走一边说:
“考虑到你参加革命很早,个性又特别强,所以方式方法也就不必拘泥了。如果你不愿意在大会上公开承认,找组织个别谈也可以。再有,写一份像样的书面检讨。”
“可是我应该写什么样的检讨呢?”
张恒直的声音是悲哀的,迷茫的,这声音进一步唤起了陈云甫心中的怜悯感情。他认为面前这个人虽然掉在水里,但还没有完全沉溺,他已经向自己发出了呼救的信号,自己有责任冒着风浪去营救。他实在不是敌人,他是同志啊!陈云甫再也顾不得思前虑后了,他决心把自己的底牌完全亮给对方。
“我想你一定学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吧?”陈云甫说得很慢,他疲倦的眼睛正透过窗子的玻璃凝视着户外十米远的一棵白蜡树,这棵白蜡树的叶子一个星期以前就已经全部脱落了,光秃秃的枝条正在大风中不住地颤抖。“你还记得那上面怎样说的吗?‘一个党员,他也可能有最高的自尊心、自爱心,而在为了党与革命利益的前提之下,也最能宽大、容忍与委曲求全,以至在必要时忍受各种屈辱虐待而无怨恨之心。’我希望你在写检讨之前,应当反复想一想刘少奇同志的教导。”
陈云甫严肃地等待着张恒直的回答。在他看来,自己这个暗示再明白不过了,等于告诉对方:
“我知道你不是右派。但,既然事已如今,为了照顾党的威信和利益,也为了你自己的前途,只好委屈承认了吧。——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法子啊!”
张恒直皱着眉头,似乎正在很吃力地思索着。这是一个老实人,陈云甫深信他不会抓住自己的一两句话大做文章。他现在倒是担心这颗死心眼儿能不能很好地领会自己的意思。看来张恒直多少还是明白了几分。长期单调、沉闷的劳改生活确实磨蚀了他不少的意志和精力,但他毕竟还保存着自己心灵里最纯洁的那一部分:诚实的品质。他想了一会儿,如痴如呆地瞠视着陈云甫的脸,坚决地摇了摇头。
“我知道我给党造成了损失,我应该接受组织的处分。无论什么处分,就是把我关在监牢里,我也愿意。只是,别把我当成右派。要我签字画押承认自己是右派,这比枪毙我还要难受。”
陈云甫完全相信最后那句话。个别谈话失败了。他十分同情张恒直的处境,但是他再也没法帮助他了。他发现自己处在一种无能为力的境地。他再一次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倒真像是一颗螺丝钉,被紧紧地拧在一个不断转动着的庞大的机器里,只要偏离轨道一点儿,立刻就会被碾得粉碎。
“好的,你回去吧。”陈云甫怏怏不乐地说,额头上两道竖纹变得更粗更深更严峻了。“我们再研究研究你的问题。”
张恒直艰难地离开椅子站起来,拖着沉重的步子,刚刚走到门口,又被叫住了。陈云甫走过来温柔地拍拍他的肩膀说:
“我希望你回去后冷静地想一想,别激动。过于感情用事实在没有好处。生活并不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简单。你年纪不轻了,应该更理智一些。如果你今天想不通,过几天也行;什么时候想通了,就直接来找我谈。但是……”说到这个“但是”,陈云甫有意停顿了一下,意味深长地看着对方的眼睛,“你要知道,时间是不等人的,愈快愈好。”
张恒直轻轻地“嗯”了一声,头也不回地走了。陈云甫望着他孤单的背影,心里感到一阵绞痛。他的脑子里又一次浮上了那个念头。他要给党委写一个报告,再附上医院的诊断证明,说明自己身体不支,请求党委调换工作。当然,真正的原因不在这儿。他已经带病在农场干了十个月。这十个月的观察、感受和体验,使他渐渐地认识到他现在所从事的工作。从字面上来说,他是受党的委派,监督那些对党对人民犯有罪行的右派分子,即年轻的大学生们,转变他们的反动立场,把他们从坏人改造成好人。可是实际上的情况怎么样呢?他的心头荡漾着疑惑和痛苦……
(待续)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