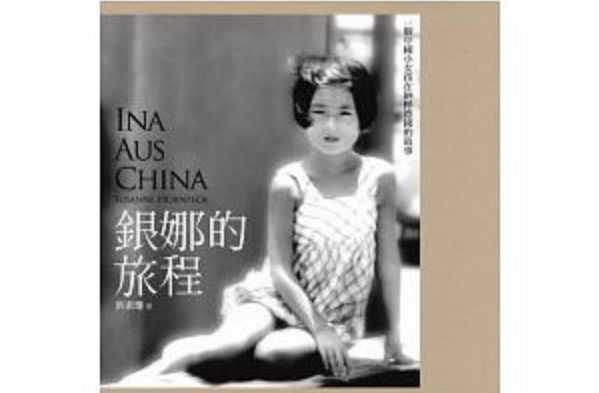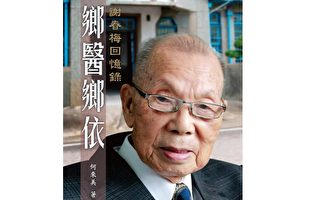这是一段改编自真人实事的故事。
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
战云密布、人心惶惶,
七岁的陈银娜从上海飘洋过海,来到德国,
寄养在冯·史坦尼茨太太家。
她踏上的每一片土地,都将成为远方……
而远方,有那盼着与她团聚的至亲……
*〈新家〉
*1937年10月|布兰登堡
从此,伊娜有了非常规律的生活:每天早上七点在大教堂的钟声中醒来,吃完早饭就和冯.史坦尼茨太太一起进城买东西,伊娜因此走遍了布兰登堡不少地方。
在伊娜眼中,布兰登堡根本算不上一座城市,没有繁忙交通,没有拥挤人潮,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巨型邮轮。贯穿城中的几条运河里,充其量也只有些许小拖船、渔舟和小游艇在上面行驶。
一切安详自在,井然有序:行人走在宽阔的人行道上,寥寥可数的汽车行驶在马路中间,电车在轨道上滑行,船只则徜徉在运河上。警察在这儿似乎显得有点儿多余。
路上的行人互相招呼、问候,熟识的则停下脚步,亲切地交谈几句;还有一些穿着褐色制服的人,以简短的方式互相打招呼:右手向前方高举,招呼声听起来像喉咙不舒服在清嗓子似的。
在这儿真像人人都彼此认识,当然每个人也很快就认识了伊娜。这小城不像上海街头,除了她没有别的外国人。布兰登堡没有人缠着富有异国情调的头巾,没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陌生面孔,也没有深浅不一的各种肤色。人人只说一种语言:德文。
市场是一条规划得整整齐齐的摊贩街,一星期只开放一次,所以又叫做“星期市场”。虽然百科全书上写着,星期市场就像上海的市场一样热闹,但伊娜可一点儿也看不出来,这儿的市场跟刘妈偶尔会带她去逛的中国传统菜场有任何相同之处!
刘妈每天下锅的菜,都是早上从市场新鲜买回来的:先到种类不胜枚举的蔬菜摊,叶菜类、豆荚类、根茎类,多不胜数。然后再去卖鱼的摊位,看鳝鱼在大木桶里翻跳,看小虾在水中不停伸着触须……
还有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的水果摊,摊子上有着形形色色的甜瓜,翠绿诱人的释迦,晶亮橘黄的小金桔,还有臭气冲天、满身是刺的巨大榴梿。刘妈挑水果一定每个都摸一摸,确定是否完好,再狠狠的跟老板杀价。
市场中混杂着种种气味,香的、臭的、好闻的、不好闻的,到处都充满讨价还价的声音,喧哗叫嚷,此起彼落,人们只能靠手不停的比画,确认要买的斤两和价钱。
最后,她们还会到卖酸梅的摊子,酸梅是永远也吃不腻的零嘴,梅核在嘴里吸吮半天,依然甘甜可口。通常刘妈会“赏”给银娜一小包酸梅,或是一块包在油纸中的现煎葱油饼。
***
要形容上海的市场,只有两个字:“热、闹”!
热闹对中国人来说,没别的意思,就是代表高兴,代表生意好。
在德国则全然不同,这儿只能用“冷”和“静”来形容,和中国的市场恰恰相反。所有活动都在秩序、平静和礼貌中进行。水果和蔬菜堆放得整整齐齐,动物都是死的。
“早安,冯·史坦尼茨太太,今天想买点儿什么?”
听起来好像有不少东西可以挑选似的:大葱、白菜、马铃薯,也许再来一些不好看也不好吃的小紫萝卜和大白萝卜。
伊娜喜欢这两种萝卜,只是因为它们的德国名字特别好玩儿罢了。顾客不准碰东西,只能用手指指着想要买的蔬果,然后老板会秤好斤两,客人二话没有,接过东西,付钱走人。
所以对伊娜来说,冯·史坦尼茨太太从德国厨房里端出来的东西,就跟德国市场给她的感觉一样,色、香、味全无!但她也知道这么说并不公平,因为她亲眼看到德国市场的东西多么乏善可陈。不过伊娜也发现了好几道自己爱吃的菜:洋芋煎饼、鸡蛋煎饼加苹果泥、小麦羹和煎肉饼。
伊娜常常帮忙准备午饭。吃过午饭,冯·史坦尼茨太太会睡个午觉,那段时间,谁也不准打扰。相对的,小伊娜也不会受到干扰,她可以自己玩儿,或是一个人想想心事。
通常她会躺在床上,在脑海里整理今天新接触到的事物:新名字、新面孔、新气味和新口味。但饱饱的肚子和暖暖的床,常常让思绪一不小心又溜进了刘妈的厨房。在午后阵雨的轰隆声、唧唧的蝉鸣和爸爸亲切的哼唱中,伊娜也昏昏沉沉进入了梦乡。
骤然回到现实,阿特曼老师两点半准时按铃造访。接着伊娜和老师两人就会坐在客厅的桌子前面,开始两小时的学习。首先,他们一起看《图画百科》中的一张图,每天小伊娜都可以自由选择一个学习主题。难道这整个陌生的世界,就在这本书的封面和封底之间吗?要从哪一页来开启呢?最好还是从身边的事物开始吧!
譬如说客厅。《图画百科》里的客厅,虽然和他们现在坐在其中的客厅不太一样,但有许多词汇,马上派得上用场:比如饭桌、沙发、餐具柜、收音机、书柜等等,只有一个叫“橡树”的东西,伊娜在冯·史坦尼茨太太的客厅找不到。
图上画着一株盆栽里的瘦小植物,但在上海,这种植物种在院子里,不仅长得很茂盛,而且可以长得比人还高!不过在冯·史坦尼茨太太的客厅里有一种东西,书上称为“收音机”,阿特曼老师却叫它“人民收音机”。这个东西对冯·史坦尼茨太太来说,十分重要,尤其在吃过晚饭以后。
第二个小时轮到写字练习。伊娜有一本德国小学生用的课本,她从课本中学习字母和生词,而且是德式的手写体。伊娜觉得手写的德文和口语的德文一样,都带刺带钩,有棱有角,但是非常实用。
譬如今天轮到“i”上场:“往上往下再往上,最后点一点在头上”,阿特曼老师教笔顺的时候,同时教了一个顺口溜帮助记忆。就这么容易,一个字母又解决了。
而这些构造简单的字母一共不过二十六个,这对在中国必须和几千个复杂的中文字奋战的小孩来说,简直就是小事一桩!德国小孩根本不知道他们有多幸福啊!
当伊娜明白用字母拼音有多方便后,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如果这二十六个字母,就可以让人知道所有的生词该怎么说,那么不久的将来,她就可以独自将百科全书里所有的字汇说出来,不用再去麻烦谁了。那扇通往新语言世界的大门,不就又打开了一些嘛!
吃完晚饭,伊娜重新坐回客厅。这次是和冯·史坦尼茨太太一起,两人不再是傍着桌子坐,而是肩并肩坐在沙发上。她们先将白天学的生词复习一遍,然后冯·史坦尼茨太太会逐一考问,看看伊娜学习的成果如何。当小家伙的回答还算差强人意时,冯·史坦尼茨太太就会把那个叫做“人民收音机”的东西打开。
在那个时段,有个节目叫做“德国之音”,内容伊娜几乎一个字也听不懂。总有一个急促、粗重、气喘吁吁的男人声音,情绪激昂的说着:人民异议分子、人民没有空间、“一人民、一帝国、一元首”、人民同志……
想必是因为“人民”这个词,总是不断传出来,所以收音机又叫做“人民收音机”吧!伊娜比较喜欢听音乐节目,收音机里也总是有播。当然,大多又是“人民的音乐”!
伊娜很快就发现了,音乐其实很实用。住进圣裴堤路的第一天,那架客厅里黑得发亮的直立式钢琴就吸引了伊娜的注意,以前她从未见过这样的乐器。幼稚园里只有一台风琴,每天早晨,大家一起唱赞美诗时,修女就会踩着踏板用风琴伴奏。
那台风琴总是可怜兮兮的喘着气,不断发出咻咻声。只有一次在上海跟爸爸去作客,在室内看到一架平台演奏钢琴,由一位女士弹奏出极美妙的音符。那位钢琴家对上海潮湿闷热的气候相当不满,认为会对钢琴造成很大的伤害。
现在,这么一架气派非凡的乐器就摆在眼前,触手可及。它不会喘气──伊娜已经偷偷试验过了──显然也不会受到气候之苦。
冯·史坦尼茨太太很快就发现,伊娜会不时抚摸着钢琴,并小心翼翼的打开琴盖,用手指试探的按着黑白琴键。
“你想学钢琴吗,伊娜?我可以帮你请一位老师,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会写信告诉你爸爸的。”
“老师”、“爸爸”,听懂了这两个词汇,其他的,伊娜再自己拼凑一下,剩下的就是拚命点头了。
于是,毕德曼(Biedermann)小姐出现了,她每星期六都会来家里教琴。虽然伊娜始终搞不懂,为什么在一位女士的名字当中,会出现“男人”这样的字!但是她非常喜欢这位新来的钢琴老师。
她觉得毕德曼小姐不但人年轻,而且一头金发真是漂亮极了!尤其她那十只修长纤细的手指,飞快的在琴键上滑行时,真是太迷人了!她的手指总是能按到正确的琴键,从不失误。
虽然毕德曼小姐为了想教她一首简单曲子,在第一堂课时竟弹出了《小汉斯向前行》那首歌,伊娜也早就原谅她了。
不要,不要再来一遍!她恨死了这首歌和所有相关的记忆。伊娜因为控制不住心中的愤怒和失望,激动的直踱脚,把年轻的毕德曼小姐着实吓了一跳。
后来两人达成协议,学习弹奏《雅格兄弟》这首歌,因为这个旋律在中国也有,只不过在中国歌词里,没有“叮当叮当”的钟声,而是有两只跑得很快的老虎。这正是音乐的美妙之处,人人有自己的想像空间,歌词到后来,其实无关紧要。
于是钢琴课也顺利进行着。伊娜注意听、仔细看,然后模仿着弹。在每天与阿特曼老师共度冗长、无聊的下午时光后,钢琴课正是她最佳的休息与调剂。不知不觉间,伊娜的右手已经可以在琴键上任意滑行,而左手可也一刻都没闲着。
但钢琴还是无法取代所有伊娜想念的事物:像跟同年龄的孩子一起嬉闹,和宝宝之间的亲密友情,听刘妈讲好听的鬼故事,和厨房里爱吃甜食的灶王爷。这些全都不会出现在她目前清楚规划好的日常生活表中。
冯·史坦尼茨太太闪闪发亮、纤尘不染的厨房里,冒不出灶王爷来,就算有吧,厨房主人也不需要用甜食贿赂他,因为所有的锅子都光可鉴人,米袋里也没有生虫长虱,灶王爷根本就没有状可告。而在帮忙削马铃薯皮的时候,也不可能随意蹲坐在小凳子上,而是必须规规矩矩坐在椅背又高又硬的座椅上。
只有到了晚上,当冯.史坦尼茨太太不需要缝补衣物的时候,她才会问伊娜:“怎么样,想不想一起玩点儿什么?”这时小伊娜就可以从两种游戏中选一样来玩:一种是她从上海带来的骨牌,另一种是冯·史坦尼茨太太柜子里原有的“不要生气”。
伊娜虽然觉得“不要生气”的名字有点儿奇怪,但游戏确实很好玩。每当有一颗棋子——最好是她的红色棋子——被踢回家了,必须重头再走一次时,有什么好生气的呢!
那就是运气不好嘛!赶快再掷骰子就是了,掷到“六”就又可以从家里走出来。而且只要有棋子被踢回家,游戏就可以一直玩下去,那么原本规定八点整要去睡觉的,就可以往后延一下了!
***
在闻起来始终有一点地板蜡和咖啡香的屋子里,小伊娜每天的日程表可是排得满满的:早餐、购物、家庭作业、午餐、德文课、练钢琴……但日子中就是少了点儿什么。
每当有孩子笑闹着从街上跑过去,伊娜总是满心渴望的望向窗外,看着他们一边玩着抓人游戏,一边带着球追打着穿过砖砌的大门,消失在城堡大院之后。
在这儿,环绕着大教堂,由高大菩提树和古老旧房子围成的内院,被称为“城堡大院”。伊娜还记得,她最后一次和同伴一起疯狂的笑闹追逐,是在前来欧洲的船上。从那之后,世界就像被箍进了一件紧身衣里一样,束缚在无法表达的语言、层层规矩和必须严格遵守的时间表之中。
伊娜动着脑筋:要如何才能到楼下去,跟那些孩子一起玩呢?虽然冯·史坦尼茨太太在午睡的时候,几乎不可能察觉到什么,但她总不能一声不吭的溜出去吧!
在“困境”中,伊娜打开那本翻阅得破破旧旧的《图画百科》。这本书在她之前,已经帮助过三个年轻人解决许多问题。
在书中,她发现有个主题叫做〈在公园里〉,当中有张图片“游戏草场”,图上画着许多孩子在草原上玩球。嗯,这张图看起来正合适!
于是有一天,在吃完中饭,洗好碗盘,伊娜照例擦干餐具之后,她取过《图画百科》递到冯·史坦尼茨太太的面前,翻到“游戏草场”那一页,并用手指着那张孩子正在游戏的图片。
冯·史坦尼茨太太特意把眼镜戴上,仔细看了看那张图,然后越过眼镜上缘,用审慎的眼光看着伊娜。
“好吧,但是两点整要回来,听到了吗?当教堂钟塔敲两下的时候。”
冯·史坦尼茨太太严正的举高了两根手指对伊娜说。
“你得先休息一下,喘口气,才能开始上课。还有,不要在街上乱跑,而且只准在城堡大院里玩。”
对于那些提醒和警告,伊娜没有听懂多少,但讯息够明确了!伊娜雀跃不已,她兴奋地穿上从上海带来的红外套,第一次一个人从屋子里走到外面,再关上那扇厚重的木制大门。
有好一会儿,她站在原地不能动,惊讶于自己的勇气。好不容易暂时没人监管,非要好好把握时光不可!
她飞快冲下那打蜡打得光可鉴人的楼梯,一步三阶的往下跳。在楼梯转弯处,她借助在栏杆扶手顶端的大圆球,来个大幅度的回旋,加速往楼下冲的速度。
冲到门外的人行道上,她首先左右张望了一下。向右是进城的磨坊路,和冯·史坦尼茨太太一起去买东西的时候,总是顺着这条路走。另一个方向不用几步路,就到了城堡大院入口。
伊娜转身向左奔去,就在要穿过砖砌大门的时候,她回头望了一眼三楼客厅,有一扇窗的窗帘微微掀动了一下。
老远,伊娜就听到了孩子嬉闹的声音。有一个棕发的女孩,年纪大概跟她差不多,另一个金发的,年纪稍小,绑着两条辫子,还有两个男孩,正轮流对着石墙丢球。
没有人发现伊娜,于是她靠着一棵菩提树,远远瞧着他们。那个大一点的女孩正在丢着球,她口中一边大声数着数,一边拍着手。
她先把球丢出去,在球弹回来之前,她要完成一连串动作,而那些动作愈来愈难:首先只要拍一次手,然后得拍好几次,再来必须将腿抬高,让球从胯下扔过,最后还要在原地自转一圈。
在她玩球的时候,两个男孩一直在旁边干扰她,试图让她接不到球。
“喂,站在那边的那个,想干嘛啊?”一个男孩突然用手指着伊娜喊道。
“嘿,你们看,她眯着眼睛哪!”另一个男孩也接着喊道。
“又没有出太阳,她干嘛把眼睛眯成那样啊?”
“你们别惹她!她住在冯·史坦尼茨太太那儿。我看过她们一起去买东西。”
年纪比较大的女孩打断了他们的嘲弄,小金发则站在旁边一声不吭。
伊娜不需要听懂就了解。男孩们用食指将两眼向外拉成一条线,这个动作她再熟悉不过。多谢指教,我知道自己在这儿是个外国人!伊娜生气的想着。
“我叫伊娜!”她毫不示弱冲着男孩说。想吓唬我,可没那么容易!
“哈哈哈,中国来的小伊娜,中国来的小伊娜!”比较大的男孩开始怪声怪调叫嚷起来。
噢,还好嘛!伊娜想,至少在这儿我不是日本鬼子!这个开头算不错了。
“你来的地方,一般人都怎么说话?磬─锵─琼,还是怎么样?”
“我是中国人!”
伊娜先用中文回敬了一句,骄傲的抬起下巴。
“我是中国人,我来自上海,我今年七岁,我住在圣裴堤路二号。”
伊娜一口气讲完了她能用德文讲的话,这招奏效了。
“嘿,你也会讲德文啊,”男孩儿赞许的说:“那你先前讲的那句话是中文啰!对吧?”
伊娜点点头。
“我叫珞特。”
褐色头发的女孩这时候插了话。她个子很壮,至少比伊娜高了一个头。
“这是英格。我们正在玩‘挑战球技’,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玩?”
伊娜再次点点头。德文课本里也有一个珞特。
“我教你。”
珞特拿起球对着墙扔过去,在球弹回来还没有落地之前,她拍了一下手。
“好,现在轮你。”
珞特把球递给伊娜。这个简单!
接下来必须拍两下手,然后是三下。这也都不难。但再来就必须把球一次从右腿胯下,一次从左腿胯下扔过去,而且还要来得及拍手,最后还必须在原地自转一圈才能接球,那可真的需要动作很快才行。
两个男孩早就放弃干扰接球的差事,张大了嘴,等着看新来的玩伴怎么搞定这个游戏。
“到后来动作比较难的时候,你最好把球扔高一点。像这样,你看。”
这时英格也插进来了,示范给伊娜看。
“这样你就会有比较多时间。”
“时间”、“钟”、“两点钟”,唉呀,糟糕了!
伊娜突然想起了阿特曼老师和冯·史坦尼茨太太的警告。她迅速抬头望向钟塔,大钟的指针正极具威胁的朝两点钟迈进。
“上课!”
伊娜因为不停丢球、拍手、转圈,一下子还喘不过气来,她吃力的吐出两个字并指着塔楼上的钟。
“你明天还会来吗?”珞特问。
“来!”
伊娜坚定的回答,虽然她一点也不确定女孩问的意思,但至少她心中渴望对方这么问自己。
“我会来!”
为了保险起见,伊娜一边往回跑,一边又对珞特喊了一次。
“而且我会教你们玩剪刀、石头、布!”
最后这一句话,伊娜没有真正说出口,就算她说了,其他人也听不懂,因为她只会用中文说。
***
“星期六,玛尔塔要来看我们。”
早餐时,冯·史坦尼茨太太对伊娜说。
对于好消息,伊娜总是很快就能明白。她正喝着大麦咖啡,差点儿呛到。有太多事她想要问玛尔塔,堂姊一回来,语言也就回来了。
这些日子,伊娜总觉得自己像个牙牙学语的小娃娃,结结巴巴讲不清一句话,真是讨厌极了。有太多的问题和想法积压在她的脑袋瓜里,等着堂姊替她清仓。
“她从柏林寄来了一张明信片,写明了抵达时间,到时候我们可以去火车站接她。”
“好耶!”伊娜高兴的欢呼起来。
冯·史坦尼茨太太将玛尔塔那张没有图片的明信片递给伊娜,她仔细研读起来。堂姊的德文字十分工整,容易辨认。这些日子以来,伊娜跟着阿特曼老师学完了字母,她开始大声的,一个字一个字的拼出来:
“亲─爱─的冯.史坦尼茨太太!”第一行这么写着。
“我已─经─找─到─了一间─房,一切也都安─顿─好了。”
哇!有够难。伊娜不认得她读的那些字,但罗马拼音的好处,就是不知道字义,照样念得出来,这在中文里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想─来─探─望─您和伊娜;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星─期─六,三十点来。”
“是十三点!”冯·史坦尼茨太太纠正她。
我永远搞不懂为什么德国人要把数字倒过来念!伊娜心中嘀咕着。好了,不管了,继续念:“有一─封─我叔叔写─给伊娜的信也在─我这。”
“爸爸的信!”
伊娜高声喊着,因为太过激动,明信片从她手中落了下来。
明信片上还写了什么,都不重要了。现在,伊娜更殷切期盼着星期六的到来。
但是,为什么爸爸不把信直接寄过来呢?欸,无所谓了,重要的是她马上就可以拿到信了。
星期六终于到了。
她们搭乘电车经过圣安娜街抵达火车站,买了月台票。从柏林来的快车驶进车站时,伊娜伸长了脖子。玛尔塔是唯一的中国人,在成群的旅客当中,远远就能认出。
伊娜拔腿就向她冲过去。
“嗨!阿肥……真高兴你能来接我。”
终于又听到那熟悉、抑扬顿挫的中文!
“冯·史坦尼茨太太也来了吗?啊,她在那后边站着呢!”
“我的信你带来了吗?”
伊娜才刚提出问题,玛尔塔口里的语言又换成了德文。
她跟冯·史坦尼茨太太打过招呼后,就热络的向她报告别后情况。房间、柏林、翰理、大学……玛尔塔从车站回家的路上,就这样说个不停。就算伊娜一路上不断扯她的衣袖,也无济于事。
“大人讲话不可以打断!”是玛尔塔在船上时就再三叮嘱的金科玉律之一。现在她是大学生了,当然算是大人了,所以对纠缠不休的小堂妹,自然名正言顺的不予理会。
伊娜快要忍不住了。玛尔塔一定要现在讲那些无聊的事吗?难道她就不能想想,我有多希望看到爸爸的信吗?伊娜心里生着闷气。
冯·史坦尼茨太太似乎也没有察觉到什么,她一面兴趣盎然,听着玛尔塔滔滔不绝叙述着,一面从容不迫打开了大门。
终于,玛尔塔把大衣挂好在衣帽间里,开始在包包里翻找起来,取出了信,并交给伊娜,然后就和冯·史坦尼茨太太一起消失在厨房里。
伊娜站在走廊上,肃穆的看着手中的信封:信封上花花绿绿的邮票,盖满了邮戳,粗纸制成的直式信封,还有用中文写成的寄信人姓名,这些看起来都那么熟悉。
这封信和她及玛尔塔一样,是经过了千山万水才来到这里。当她屏息凝神的从信封中抽出信纸,鼻尖因为心情激动而不自禁的一酸。信纸先包折,然后在上方约三分之一处,又往下折了一折。整张信纸从上至下,是用毛笔写的,工工整整的蝇头小楷写满了一张。
伊娜一下子愣住了。刹那间她意识到,自己和爸爸的距离不单是远隔重洋,还包括了语言和文字。她认不得爸爸写的汉字,爸爸也看不懂她写的德文。想到这里,泪水一下子涌进眼眶,一滴滴落在信纸上。幸亏中国的墨汁要比西方的墨水防水一些,伊娜迅速将信又折了起来。
“要我念给你听吗?”玛尔塔问。
她手里端着装满东西的托盘,踏出厨房,正要往客厅走去。在昏暗的走廊上,她没有察觉到伊娜哭了。
难怪爸爸把信寄给玛尔塔,他知道若没有堂姊帮忙,我是看不懂信的,可玛尔塔满脑子只想着自己的事。但,抱怨委屈无济于事,现在只能靠堂姊了。
“是的,谢谢!”伊娜轻声回答。
“还是进客厅来吧!走廊上太黑了,我什么也看不见。咦……怎么了?你干嘛哭啊?难道不高兴收到信吗?”
这个玛尔塔,怎么就是什么都不懂!
“好,听着,你爸爸的信是这样写的……”
我亲爱的女儿银娜:
你好吗?冬天快要到了,你去德国也有好一阵子了。我希望你已经适应那边的气候,也习惯了冯·史坦尼茨太太家里的生活。很遗憾的,我个人并不认识冯·史坦尼茨太太,不过我们两家一直有着深厚的情谊。
我很高兴你能在德国受到妥善的照顾,因为这儿的情况已有了很大的改变。你是知道的,刘妈回了乡下老家,而我也必须跟着银行迁到重庆。
一个人在重庆生活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身边少了你,少了刘妈,少了厨房里乒乒乓乓的声音,屋子里变得好安静。我们现在必须耐心等待,看政治的情势将会如何发展。希望战争不要持续太久,你能尽快回到中国来。
答应我,要不时跟美华练习中文,不要完全忘记你的母语。
做个乖女儿,好好用功读书。爸爸非常想念你。
爱你的父亲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于重庆 ◇(节录完)
【作者简介】
洪素珊(Susanne Hornfeck)
德国慕尼黑大学文学博士,汉学家,现居德国南部慕尼黑市近郊。从事专业著述及书籍翻译,曾译介多位中文名家作品至德语世界,是中、德文学交流的重要推手。
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四年受德国学术交流总署(DAAD)派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担任客座讲师。在台任教期间,结识本书主人翁陈银娜(化名),得知银娜的人生故事,于是起了念头,开始撰写这个中国小女孩在二战期间的奇妙经历。
她以十年工夫写就的“认同三部曲”,地理上跨越了欧亚大陆,时间上从二十世纪上半叶来到二十一世纪初,主题涵盖战争、流亡、离散、融合,透过三位女主人翁银娜、英格和木兰的人生故事。
——节录自《银娜的旅程》/ 左岸文化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余心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