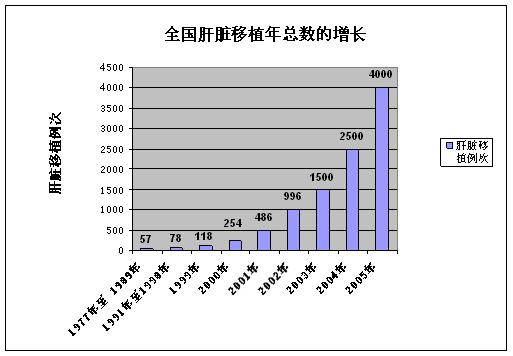八
生活还是像原来那样进行着,并没有因为一个年轻生命的毁灭而有一丝一毫的变化。
冬天来到了。这是一九五八年的冬天。辽阔的国土上升起了举世闻名的“三面红旗”,在她们璀璨夺目的光辉照耀下,全国男女老幼几乎都动员起来了:挑灯夜战,砸铁炼钢,挖渠开河。各行各业都在争着放“卫星”。“卫星”一个更比一个大。一时间,只见中国的天空“卫星”满天飞。
张恒直头上戴着一顶帽子,是人民的敌人,自然没有资格和人民共用这种盛况空前热烈的喜悦。但是他也没有闲着。在全国一片凯歌声中,两木农场匆匆地建立起了一座化肥厂,按照规划,将年产数万吨硫酸,规模可说不小。这是现代化的生产,得找些有文化科学知识的人来操作才好。农场里放着这么多的大学生,为什么不用一用呢?场长主意一定,便找陈云甫和汤达凌商量。三个人坐在一起研究了几分钟,就决定将南区队的右派分子全部调到化肥厂劳动,因为这个区队的右派几乎有一半是学化学的,既对上了口径,可以发挥他们的专长,又不致拆散原来对右派的管理体制,两头都照顾到了,双方皆很满意。于是张恒直他们奉命放下了农具,卷起了铺盖来到了农场总部(厂址建在这儿),开始当化学工人了。
工厂投资早已突破二十万元大关,机器设备也都安装好了,不晓得是什么毛病,就是生产不出一滴硫酸来。但凭着场长来头大,矿石还是照样一车一车地往里运,堆成了两座石山。张恒直现在每天都在砸矿石,把一块块黑乌乌硬邦邦的大石头砸成许多小碎块,以便工厂技术过关后立即就可投入生产。他不但白天砸,晚上还得对着月亮和星星“夜战”三、四个小时。他没有棉鞋,单鞋也早已破烂不堪了,而砸矿石又不需要两只脚出力气,老是蹲坐在地上保持着同一种姿势,砸了不到一个礼拜的矿石,他的脚生了好几个冻疮:早晚天冷要发痛,正午太阳当头的时候又变得奇痒难熬。这个滋味真不好受。他咬着牙默默地忍受着,不向任何人吐露一个字,连“小上海”也不告诉。
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了,终于盼到了一个难得的礼拜天,农场总部宣布让大家休整一天,以迎接今后更大的“战斗”任务。人们喜出望外,纷纷到市里去洗澡,看电影,惟有张恒直一瘸一拐地来到了附近的一个小集镇。他看见一个老头儿面前放着一堆高帮草鞋,式样虽然笨重,倒很结实。他向老头儿打了个招呼,便拿了一只试穿了一下,果然觉得十分温暖、舒适。再一问价钱,要二元五角。他对着草鞋轻轻地叹息了一声,把它放回到原处,然后绕着老头儿慢慢地徘徊,两道眉毛皱得很紧。那老头儿看透了他的心思,便引诱他说;
“来一双吧?穿了这鞋包你的脚冻不着。”
“钱不够啊!”张恒直向老头儿笑了一笑,接着又叹了一口气。
“你给两元吧。”老头儿说,他看出来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实人。“咱是认人不认钱,一文也不赚你的了。”
张恒直一边付钱,一边道谢。老头儿也很高兴,亲自为他挑选了一双比较结实的。张恒直穿上新草鞋,顿时觉得脚痛减轻了不少,走起路来不像以前那么艰难沉重了。但他走了十多步又把它们换了下来:他得完好无损地拿回去先让“小上海”欣赏一下。他对“小上海”的感情依然是那么浓,只不过更多地放在心里更少地表露罢了。他希望听到“小上海”赞美一声。如果“小上海”确实喜欢这双鞋,他愿意送给他穿。他现在身边还剩下两角七分钱。烧饼三分钱一个,他买了五个吞进肚子里。手上捧着两只草鞋一瘸一拐地走回到农场。“小上海”还没有回来。他一直等到晚上九点仍不见“小上海”的踪影,只好失望地铺上被褥准备就寝。
张恒直又困又累,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在睡梦中,他依稀觉得自己穿上了新买的高帮草鞋去参加考试;通过这场考试,他将进入人生的转捩点。他走进了考场,立时感到里面的气氛十分庄重、严肃。他惶恐地环顾四周,发现考场辽阔、空旷,好像是无边无际的原野,又好像是寂静窒息的墓地。可是,你瞧,远处那边主席台上坐着三个人,似乎正在等着他。
张恒直迈开穿着高帮草鞋的两只脚,勇敢地向主席台大步走去。主席台的桌子上铺着洁净的白布,上面摆着两瓶鲜花,另外还放着许多卷好的小纸条,每一张纸条大概就是一道考题吧?张恒直蓦地一怔,觉得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这样的场面。他努力追忆,忽然想起自己踏进大学门槛不久,听过一个刚从苏联讲学回来的教授演讲,介绍莫斯科大学的考试,那情景和眼前这张桌子上的布置差不多。
张恒直离主席台愈来愈近了。他现在清楚地看见,在那只摆着鲜花的桌子正中就座的原来是一尊镀着金粉的菩萨。在菩萨的右边坐着陈云甫,正皱着眉头在沉思,额上两道竖纹又粗又深又严峻;左侧则是汤达凌,两只手捧着一本厚厚的佛经,嘴里喃喃地祈祷着什么。张恒直向他们走去,深深地鞠了一躬。这时在他后面传来了他十分厌恶的江涛的声音:
“报告!右派分子张恒直到。”
张恒直吃惊地扭过头去——啊,原来是江涛押送他来的!江涛穿着国民党青年军的军装,手里还握着一支手枪。张恒直愤怒地回过头来,又吃惊地看到桌子正中原来那尊菩萨的位置上,此刻正坐着一位身穿袈裟的法师,六十光景的年纪,两只手搁在桌面的白布上,脸上好一派神圣、威严的表情。这位法师用严厉的目光审视着张恒直,突然干咳了一声,然后半闭着眼睛,用习惯于念经的声音问道:
“你就是右派分子张恒直吗?”
“冤枉哪!冤枉哪!”张恒直声色俱悲地号啕大哭。“我不是右派分子,我是真心实意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啊!”
“别嚷!”汤达凌把手上的佛经朝桌子上一拍,厉声喝道。“马上就要考试,你是不是右派分子,一考就考出来了。”
“真金不怕火来烧。”张恒直对自己说,立刻化忧为喜。“当年我把脑袋拴在裤腰带的手枪上,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进出出,不就是为了打下今天的江山吗?把我的骨头烧成灰也休想找到反党反社会的思想。这回我可以得救了。”
“这儿是你的考题。”
法师伸出食指向一张纸条点了一下,汤达凌就把这张纸条拿过来交给张恒直。张恒直打开纸条一看,见上面印着几个仿宋体的大字:
“黑猫和白猫,哪一个好?”
“黑猫好!”张恒直几乎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不对,黑猫是魔鬼的化身。”法师摇晃着秃脑袋,得意洋洋地说。“尘世上的一切罪恶,诸如:贪婪、自私、淫乱、盗窃、诈骗、虚荣、嫉妒,等等,等等,都是从这只黑猫身上衍生出来的,黑猫是万恶之源。”
“那么——白猫好!”张恒直讷讷地说,纠正了自己刚才的答案。
法师向汤达凌斜视了一眼。汤达凌赶紧打开那本厚厚的佛经,紧张地翻寻了一番,然后把嘴凑到法师的耳边,说道:
“法师大人!我刚才已经查过了佛经。据佛经记载,白猫像征资产阶级。”
“两个都不好!”张恒直惶惑地补充了一句,他对自己的回答已经失去了信心。
“你把一切都否定了。”陈云甫轻轻地摇着头,满怀忧虑地叹息道。“按照你的答案,这个世界还剩下什么呢?”
“完啦——我完蛋啦!”张恒直的心头立时袭上一阵绝望的痛苦,身子像触电似地抽搐了一下:他惊醒过来了。这时正在响着急促的电铃声。屋子里的电灯亮了。他周围的人们都在忙着起床。啊,这不过是一场梦!张恒直惊喜地扔下梦境从被窝里钻出来。他简单地漱洗了一下,就抱着草鞋匆匆地去吃早饭,又抱着草鞋匆匆地去上工。天还没有大亮,他们已经开始劳动了。
张恒直今天似乎情绪特别好。他凑到“小上海”身边,把那双高帮草鞋捧到人家的眼睛前面。
“你看这鞋好不好?穿起来可舒服哩!”
“小上海”正在害着思家病。他满肚子的烦恼,连看也不愿看一眼,就把那双鞋扔到地上,足足有十多尺远,一边嘟嘟哝哝地说:
“一双草鞋有什么好不好的。你就是喜欢缠人家,没话找话,真讨厌!”
张恒直一瘸一拐地走过去拾草鞋。“小上海”的态度刺痛了他的心。他觉得自己的感情受到了蔑视。他知道,“小上海”并不真心喜欢自己,只是因为有些可怜他,有时才和他搭理几句。是的,这儿没有一个人了解他,连他——“小上海”,也不愿意和他多亲近。于是他想起了那个蓝布褂子上打补丁的女同学。她是农民的女儿,她会了解他的。他将来要穿着这双高帮草鞋走到她的面前,对她说一句话。她不会嘲笑他的。是的,她一定不会嘲笑他的……
(待续)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