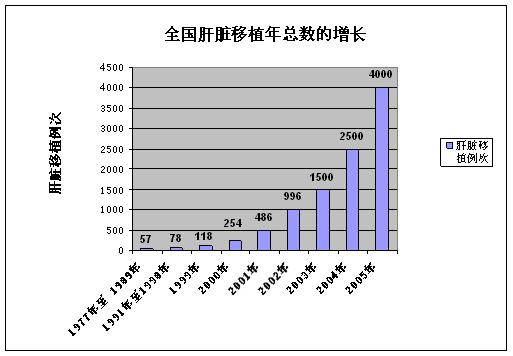八
生活還是像原來那樣進行著,並沒有因為一個年輕生命的毀滅而有一絲一毫的變化。
冬天來到了。這是一九五八年的冬天。遼闊的國土上升起了舉世聞名的「三面紅旗」,在她們璀璨奪目的光輝照耀下,全國男女老幼幾乎都動員起來了:挑燈夜戰,砸鐵煉鋼,挖渠開河。各行各業都在爭著放「衛星」。「衛星」一個更比一個大。一時間,只見中國的天空「衛星」滿天飛。
張恒直頭上戴著一頂帽子,是人民的敵人,自然沒有資格和人民共用這種盛況空前熱烈的喜悅。但是他也沒有閑著。在全國一片凱歌聲中,兩木農場匆匆地建立起了一座化肥廠,按照規劃,將年產數萬噸硫酸,規模可說不小。這是現代化的生產,得找些有文化科學知識的人來操作才好。農場裏放著這麼多的大學生,為什麼不用一用呢?場長主意一定,便找陳雲甫和湯達淩商量。三個人坐在一起研究了幾分鐘,就決定將南區隊的右派分子全部調到化肥廠勞動,因為這個區隊的右派幾乎有一半是學化學的,既對上了口徑,可以發揮他們的專長,又不致拆散原來對右派的管理體制,兩頭都照顧到了,雙方皆很滿意。於是張恒直他們奉命放下了農具,捲起了鋪蓋來到了農場總部(廠址建在這兒),開始當化學工人了。
工廠投資早已突破二十萬元大關,機器設備也都安裝好了,不曉得是什麼毛病,就是生產不出一滴硫酸來。但憑著場長來頭大,礦石還是照樣一車一車地往裏運,堆成了兩座石山。張恒直現在每天都在砸礦石,把一塊塊黑烏烏硬邦邦的大石頭砸成許多小碎塊,以便工廠技術過關後立即就可投入生產。他不但白天砸,晚上還得對著月亮和星星「夜戰」三、四個小時。他沒有棉鞋,單鞋也早已破爛不堪了,而砸礦石又不需要兩隻腳出力氣,老是蹲坐在地上保持著同一種姿勢,砸了不到一個禮拜的礦石,他的腳生了好幾個凍瘡:早晚天冷要發痛,正午太陽當頭的時候又變得奇癢難熬。這個滋味真不好受。他咬著牙默默地忍受著,不向任何人吐露一個字,連「小上海」也不告訴。
一天又一天地過去了,終於盼到了一個難得的禮拜天,農場總部宣佈讓大家休整一天,以迎接今後更大的「戰鬥」任務。人們喜出望外,紛紛到市裡去洗澡,看電影,惟有張恒直一瘸一拐地來到了附近的一個小集鎮。他看見一個老頭兒面前放著一堆高幫草鞋,式樣雖然笨重,倒很結實。他向老頭兒打了個招呼,便拿了一隻試穿了一下,果然覺得十分溫暖、舒適。再一問價錢,要二元五角。他對著草鞋輕輕地歎息了一聲,把它放回到原處,然後繞著老頭兒慢慢地徘徊,兩道眉毛皺得很緊。那老頭兒看透了他的心思,便引誘他說;
「來一雙吧?穿了這鞋包你的腳凍不著。」
「錢不夠啊!」張恒直向老頭兒笑了一笑,接著又歎了一口氣。
「你給兩元吧。」老頭兒說,他看出來這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老實人。「咱是認人不認錢,一文也不賺你的了。」
張恒直一邊付錢,一邊道謝。老頭兒也很高興,親自為他挑選了一雙比較結實的。張恒直穿上新草鞋,頓時覺得腳痛減輕了不少,走起路來不像以前那麼艱難沉重了。但他走了十多步又把它們換了下來:他得完好無損地拿回去先讓「小上海」欣賞一下。他對「小上海」的感情依然是那麼濃,只不過更多地放在心裏更少地表露罷了。他希望聽到「小上海」讚美一聲。如果「小上海」確實喜歡這雙鞋,他願意送給他穿。他現在身邊還剩下兩角七分錢。燒餅三分錢一個,他買了五個吞進肚子裏。手上捧著兩隻草鞋一瘸一拐地走回到農場。「小上海」還沒有回來。他一直等到晚上九點仍不見「小上海」的蹤影,只好失望地鋪上被褥準備就寢。
張恒直又睏又累,不一會兒就睡著了。在睡夢中,他依稀覺得自己穿上了新買的高幫草鞋去參加考試;通過這場考試,他將進入人生的轉捩點。他走進了考場,立時感到裏面的氣氛十分莊重、嚴肅。他惶恐地環顧四周,發現考場遼闊、空曠,好像是無邊無際的原野,又好像是寂靜窒息的墓地。可是,你瞧,遠處那邊主席臺上坐著三個人,似乎正在等著他。
張恒直邁開穿著高幫草鞋的兩隻腳,勇敢地向主席臺大步走去。主席臺的桌子上鋪著潔淨的白布,上面擺著兩瓶鮮花,另外還放著許多卷好的小紙條,每一張紙條大概就是一道考題吧?張恒直驀地一怔,覺得似乎在什麼地方見過這樣的場面。他努力追憶,忽然想起自己踏進大學門檻不久,聽過一個剛從蘇聯講學回來的教授演講,介紹莫斯科大學的考試,那情景和眼前這張桌子上的佈置差不多。
張恒直離主席臺愈來愈近了。他現在清楚地看見,在那只擺著鮮花的桌子正中就座的原來是一尊鍍著金粉的菩薩。在菩薩的右邊坐著陳雲甫,正皺著眉頭在沉思,額上兩道豎紋又粗又深又嚴峻;左側則是湯達淩,兩隻手捧著一本厚厚的佛經,嘴裏喃喃地祈禱著什麼。張恒直向他們走去,深深地鞠了一躬。這時在他後面傳來了他十分厭惡的江濤的聲音:
「報告!右派分子張恒直到。」
張恒直吃驚地扭過頭去——啊,原來是江濤押送他來的!江濤穿著國民黨青年軍的軍裝,手裏還握著一支手槍。張恒直憤怒地回過頭來,又吃驚地看到桌子正中原來那尊菩薩的位置上,此刻正坐著一位身穿袈裟的法師,六十光景的年紀,兩隻手擱在桌面的白布上,臉上好一派神聖、威嚴的表情。這位法師用嚴厲的目光審視著張恒直,突然乾咳了一聲,然後半閉著眼睛,用習慣於念經的聲音問道:
「你就是右派分子張恒直嗎?」
「冤枉哪!冤枉哪!」張恒直聲色俱悲地號啕大哭。「我不是右派分子,我是真心實意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的啊!」
「別嚷!」湯達淩把手上的佛經朝桌子上一拍,厲聲喝道。「馬上就要考試,你是不是右派分子,一考就考出來了。」
「真金不怕火來燒。」張恒直對自己說,立刻化憂為喜。「當年我把腦袋拴在褲腰帶的手槍上,在國(民黨)統(治)區進進出出,不就是為了打下今天的江山嗎?把我的骨頭燒成灰也休想找到反黨反社會的思想。這回我可以得救了。」
「這兒是你的考題。」
法師伸出食指向一張紙條點了一下,湯達淩就把這張紙條拿過來交給張恒直。張恒直打開紙條一看,見上面印著幾個仿宋體的大字:
「黑貓和白貓,哪一個好?」
「黑貓好!」張恒直幾乎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不對,黑貓是魔鬼的化身。」法師搖晃著禿腦袋,得意洋洋地說。「塵世上的一切罪惡,諸如:貪婪、自私、淫亂、盜竊、詐騙、虛榮、嫉妒,等等,等等,都是從這只黑貓身上衍生出來的,黑貓是萬惡之源。」
「那麼——白貓好!」張恒直訥訥地說,糾正了自己剛才的答案。
法師向湯達淩斜視了一眼。湯達淩趕緊打開那本厚厚的佛經,緊張地翻尋了一番,然後把嘴湊到法師的耳邊,說道:
「法師大人!我剛才已經查過了佛經。據佛經記載,白貓像徵資產階級。」
「兩個都不好!」張恒直惶惑地補充了一句,他對自己的回答已經失去了信心。
「你把一切都否定了。」陳雲甫輕輕地搖著頭,滿懷憂慮地歎息道。「按照你的答案,這個世界還剩下什麼呢?」
「完啦——我完蛋啦!」張恒直的心頭立時襲上一陣絕望的痛苦,身子像觸電似地抽搐了一下:他驚醒過來了。這時正在響著急促的電鈴聲。屋子裏的電燈亮了。他周圍的人們都在忙著起床。啊,這不過是一場夢!張恒直驚喜地扔下夢境從被窩裏鑽出來。他簡單地漱洗了一下,就抱著草鞋匆匆地去吃早飯,又抱著草鞋匆匆地去上工。天還沒有大亮,他們已經開始勞動了。
張恒直今天似乎情緒特別好。他湊到「小上海」身邊,把那雙高幫草鞋捧到人家的眼睛前面。
「你看這鞋好不好?穿起來可舒服哩!」
「小上海」正在害著思家病。他滿肚子的煩惱,連看也不願看一眼,就把那雙鞋扔到地上,足足有十多尺遠,一邊嘟嘟噥噥地說:
「一雙草鞋有什麼好不好的。你就是喜歡纏人家,沒話找話,真討厭!」
張恒直一瘸一拐地走過去拾草鞋。「小上海」的態度刺痛了他的心。他覺得自己的感情受到了蔑視。他知道,「小上海」並不真心喜歡自己,只是因為有些可憐他,有時才和他搭理幾句。是的,這兒沒有一個人瞭解他,連他——「小上海」,也不願意和他多親近。於是他想起了那個藍布褂子上打補丁的女同學。她是農民的女兒,她會瞭解他的。他將來要穿著這雙高幫草鞋走到她的面前,對她說一句話。她不會嘲笑他的。是的,她一定不會嘲笑他的……
(待續)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