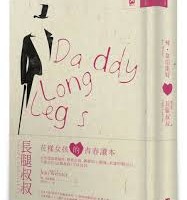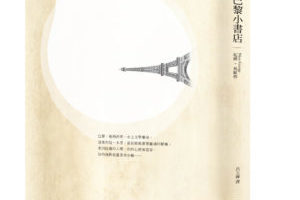蘇東坡的詩:「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
這座人潮似海的巍巍大城,真能藏住所有不為人知的另一面?
還是就像籠罩城頂的霧霾一樣,人們只能避它防它,束手無策?
該做好人還是壞人?霧霾深罩的北京城,上演著不見天的罪與罰。
──《王城如海》
這幾天余松坡的胃口欠佳,最愛吃的煎土雞蛋早餐也只是切了蛋白的三分之一。祁好擬的食譜:蛋黃不吃,膽固醇高。羅冬雨吃掉了蛋黃和剩下的蛋白。牛奶(脫脂的),麥片粥(降血脂),烤全麥麵包片,西紅柿。
據說奧馬巴早餐也是這些。余松坡多一樣,辣椒醬「老乾媽」。這是漂泊海外的後遺症。
羅冬雨剛來的時候,余松坡在飯桌上講過,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念戲劇專業的研究生時,有段時間忙論文,顧不上到餐館裡洗盤子搞創收,窮得揭不開鍋了,見到彩票信息就兩眼發綠。
有一天在校園的海報欄裡看到條消息,紐約華人留學生協會搞了一個問卷活動,既像腦筋急轉彎又像有獎競猜,回答精妙者有獎。他拿了頭獎,三個月的生活費一下子解決了。
有道題他答得讓所有評委都擊節。
問:華人留學生心目中最慰鄉愁的女神是誰?
他答:陶華碧。
陶華碧是「老乾媽」的創始人,這一款辣醬不僅解決了所有留學生的吃飯問題,還撫慰了背井離鄉的悲愁。不管能不能吃辣的,老乾媽都讓他們嘗到了祖國的滋味。
羅冬雨把余家的早餐食譜推薦給父母、弟弟和男朋友,沒一個當回事。
父母在蘇北農村,早飯一年到頭只有兩款:春秋冬三季是稀飯、饅頭或餅,外加一碟鹹菜,來客人了就多炒個雞蛋;夏天是白開水、饅頭或餅,外加鹹菜。
弟弟畢業後留在北京,每天工作到後半夜,早上起來就該吃午飯了。
男朋友送快遞,作息倒是規律,作為前廚師,余家的早餐他唯一感興趣的是編外的「老乾媽」。較起真來,韓山用鼻子哼一聲,這不是營養和飲食習慣的差異,是城鄉差別、中西差別,是階級的問題。
余松坡兩口子都是紐約來的海歸。
儘管沒耽誤余松坡的早餐,羅冬雨知道自己還是起遲了。
晚了半小時。
照她的習慣,若無特殊情況,余松坡和祁好早晨看見她的第一眼,必是一個洗漱完畢、清清爽爽的羅冬雨,而不是早上這樣,蓬頭垢面、睡袍一放鬆就露出兩條光腿。的確遇到了意外,半夜余松坡發病了。
過了子夜她沒來由地進入了眠淺的狀態,薄薄地浮在睡眠的表層,空氣淨化器微弱的聲響她都聽得分明。余松坡臥室門咯噔一聲打開時,她精確地醒來,隔著她和余果的房門以及空曠的客廳,她判斷著余松坡棉拖鞋與大理石地板摩擦的方向。
當她發現他不是朝向衛生間也不是朝向廚房,而是在客廳裡轉了一圈時,果斷地穿上睡袍打開門。借著窗外北京夜空含混的霓虹燈光,以及客廳裡另一台空氣淨化器上藍色和橘黃色的指示燈,她看見余松坡睡衣褲整齊地貼著客廳墻角在走,眼神安詳但表情緊張,五官之間在相互較勁。
以她的經驗,余松坡會越走越快,擺臂幅度漸大,直到失控,最終會喊出聲來,對家具大打出手。這個過程只需要五到八分鐘。
來得及。她在悄悄走向客廳東南角的留聲機時,覺得自己後半夜的眠淺就是為這一刻準備的。她預感到了這個四十六歲的男人今夜要出問題?她打開留聲機,調到合適的音量,當唱針落到黑漆膠片上時,〈二泉映月〉的二胡聲像憂傷的月光落滿了客廳。
余松坡的速度慢下來,手臂的擺動也跟著緩慢而抒情。他閉上眼又睜開,五官逐一放棄了戒備,回到它們原來的位置。一張平和帥氣的中年男人的臉。
羅冬雨站在留聲機旁不出聲,看著這個只比自己父親小五歲的男人,這個著名的話劇導演,他有千般好,但她在敬仰之外也生出了憐惜和悲哀。
他的行動越來越輕柔,彷彿擔心打斷了這深潭般的音樂。他在認真聽,但他不知道他在聽,他不知道正是這一曲子,唯有這一曲子才能平復他身心裡的焦慮、恐懼和躁動,然後他按照音樂的節奏起伏著右手,轉身往臥室裡走。
當他關上門,又過一分半鐘,羅冬雨關掉了留聲機。
可以了。他返回到先前的睡眠裡,彷彿不曾起來過。
早上出門,余松坡甚至都沒有看那台德國造的留聲機一眼。如果看了一眼,肯定沒有看第二眼。彷彿他不曾起來過。他當然知道那台留聲機對他的意義。
這個家唯一不能動的就是留聲機,電源永遠都通著,黑膠片從來都不換,從最外圍往裡數,第二十一圈開始是閔慧芬演奏的〈二泉映月〉。哪怕一年用不上一次。要聽音樂有音響、功放,古典音樂、現代音樂、中國民樂、世界各國民歌,包括〈二泉映月〉,但留聲機裡的〈二泉映月〉必須隨時待命。
四年前,羅冬雨站在這個家的門檻外面,祁好只問了她一個問題:能否嚴守祕密?她說能。祁好說,那就好,請進;這祕密比他們家保險箱密碼都重大。然後祁好把她帶到留聲機前,花了一個小時教會她如何在五秒鐘之內讓閔慧芬拉起〈二泉映月〉。
祁好小心翼翼地拍著留聲機黃銅做的大喇叭,那簡直就是一朵冷傲的巨型牽牛花。祁好說:
「保險箱可以動,這個不能動。著火了,保險箱可以扔,這個不能扔。」
但祁好沒告訴她為什麼。主家不說她就不能問,這是規矩。
來余家的第六個月,秋天的後半夜,她起來給余果沖奶粉,那時候祁好正和她、余果睡在一個房間,祁好不餵母乳,夜裡也很少起來照看孩子,只是偶爾過來陪他們睡著。祁好突然坐起來,說:「冬雨,快,〈二泉映月〉。」
她的緊張把羅冬雨嚇了一跳,羅冬雨放下奶瓶就往客廳跑。她看見一個人影正張牙舞爪地朝留聲機衝過去,她甚至都沒看清那人是余松坡就搶到了他前面,哢,哢,哢,哢,她頭腦裡的秒針走動了四下,〈二泉映月〉響起來。
稍稍不那麼完美的是,閔慧芬是從第二十二圈拉起的,然後她看見余松坡停在原地,狂躁和恐懼緩慢地從四肢和幽藍的臉上褪去,那些劍拔弩張的力量隨著絲弦飄曳走了,一個陌生的余松坡轉瞬即逝,他像過去一樣沉默、平和,轉過身,在剩下的二胡聲裡回了自己房間。
夢遊。祁好的說法。
她說遇到重大刺激或情緒動蕩,余松坡會在後半夜夢遊。放心,我們家老余不傷人,要傷也只會傷自己。〈二泉映月〉能治,所以,這就是留聲機的祕密。
羅冬雨不完全相信這種解釋,但也挑不出毛病;當年她在衛校裡學的是護理,老師沒講這些。她也沒往深處想,只在餵余果奶粉時腦子裡轉了兩個念頭:一是,如果她沒有及時趕到,余老師會砸了那留聲機嗎?二是,有錢人真任性,治病聽的〈二泉映月〉也得用進口的老骨董放。
再後來,祁好無意中說起,他們回國時,三隻行李箱裝下了他們在海外二十年的家當:幾身衣服,二、三十本書,十幾張面具,一台留聲機,和八百九十五美元。羅冬雨在心裡哦了一聲。如果是夢遊,那也由來已久。
四年多余松坡夢遊過三次。也可能更多,只是羅冬雨不知道。原因當然也不便問。她沒學過家政,但護理課上老師教過,護理過程中,有時要裝成是個瞎子、聾子和啞巴。她是護理專業那一屆最優秀的畢業生。
七點一刻,羅冬雨叫醒余果。余果照例要賴上幾分鐘的床。三分鐘後,小傢伙已經完全清醒,但讓他穿衣服下床依然要大費周章。
羅冬雨有辦法,昨天泡進浴缸裡的恐龍蛋裂開了,一隻粉色的小恐龍探出了腦袋。余果來了精神,自己穿好衣服。刷牙,洗臉,喝一杯溫開水,從家裡走到小區門口的幼兒園,通常距早飯上桌還剩下五分鐘,正好讓他坐定了出口涼氣。
全北京最好的私立幼兒園之一,一日三餐都由幼兒園營養師親自搭配。祁好看重科學。
為了免受冷風和霧霾之苦,羅冬雨把洗漱的傢伙拿到了樓上的衛生間。余果咳嗽著從樓下跑上來,後腦勺上和老鼠尾巴一樣粗細的長壽小辮子也跟著蹦。他把剛露頭的小恐龍從蛋殼裡揪出來了。
「冬雨阿姨,恐龍怎麼這麼小?」
「剛破殼出來,當然小,放回去它才能繼續長大。」
「我剛生出來也這麼小嗎?」
「比它大。」
這個比較羅冬雨自己都笑了。恐龍蛋是她在超市採購時順手買的玩具,每顆拇指大小,放水裡泡二十四小時,小恐龍破殼而出;再泡二十四小時,小恐龍會長大兩到三倍。這麼微小的變化已經讓余果驚奇不己了。
「那我生下來時有多大?」
「這麼大,」羅冬雨比畫了一下,覺得現有的尺寸不夠樂觀,又把兩隻手的距離拉開了一點。「咱們果果生下來是個胖嘟嘟的洋娃娃。」
「像它一樣胖嗎?」余果指著牆上他貼的加菲貓圖片。
「你把小恐龍送回去阿姨就告訴你。」
余果生下來比一隻貓大不了多少,還是瘦貓。
分娩時祁好三十八歲,大齡產婦。為了保住余果,她搭上了半條命,從頭一次找不到胎音開始,出血,胎位不正,臍帶繞頸,羊水不夠,孕期高血壓、高血糖,就沒有連著三天消停過的。
懷孕九個月,祁好在婦幼保健醫院待了不下四個月。余果生下來就被送進了保育箱。祁好看見醫生手裡倒頭拎著一個紫不溜秋的小玩意兒,哪是個孩子,就是只病貓嘛,她放聲大哭的力氣都沒了。
這一眼毀了她做母親的自信。背地裡她一直抱怨余松坡,為什麼非得要個孩子,二人世界不是挺好嗎!差點得了產後抑鬱症。也是為此,她決定把羅冬雨帶回家。
在醫院的幾個月裡,羅冬雨是她的私人護理,她想到和沒想到的,羅冬雨都做得很好。
羅冬雨是她請的第三個護理,跟前兩個相比,羅冬雨不僅悟性高、技術好,還懂得尊重別人的隱私;生活中的隱私,生理上的隱私,哪怕女人之於女人的。有羅冬雨在跟前,做女人、做母親,祁好心裡都有了底。
再從樓下跑上來,余果已經忘了他生下來有多大的問題,他鄭重地跟羅冬雨說:「阿姨,衛生間的玻璃碎了。」
「天太冷,凍的。」
「多冷?」余果也比畫起來,一個籃球大小的圓,「有這麼冷嗎?」
羅冬雨重複了他的大小,「有。不過果果刷完牙洗完臉,冷就變小了。」
出門她給余果戴上最新款的防霾口罩。網上售價四百多,防霾率據說高達百分之九十六,當然早就賣斷了貨。◇(節錄完)
——節錄自《王城如海》/ 九歌出版社
責任編輯:李梅